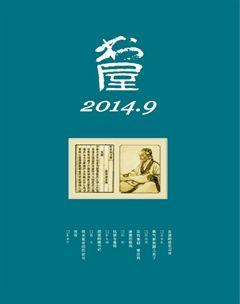有關狙擊的歷史與傳奇
朱亞寧
年齡稍長的影迷應該還記得2001年上映過一部名叫《兵臨城下》的電影。這部改編自同名紀實小說,投資高達九千五百萬美元,由法國人讓-雅克·阿諾執導的片子以二戰最殘酷的戰役之一——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德、蘇雙方傷亡約二百萬人)為背景,講述了兩位狙擊手:牧羊人出身的蘇軍準尉瓦西里·扎依采夫(俄語“扎依采夫”意為“野兔”)與柏林狙擊學校校長、神槍手考寧斯少校生死決斗的故事。
影片的主角瓦西里·扎依采夫確有其人,他1915年出生于俄羅斯的車里雅賓斯克州,1936年在蘇軍第六十二集團軍第二百八十四師一千零四十七團服役。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扎依采夫先以一支普通毛瑟槍射殺了三十二名德國人,之后三個月內用狙擊步槍擊斃二百二十五名德國及其他軸心國部隊官兵,包括十一名狙擊手。1943年2月他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按狙殺人數在二戰狙擊手中列第十位。1991年12月15日逝世于基輔,享年七十六歲。不過據考證,扎伊采夫和考寧斯的對決并無其事,乃是蘇聯宣傳機器制造的神話,德國也并沒有考寧斯少校教學的那樣一所狙擊學校。
狙擊手(Sniper),一個毫不惹眼的詞,其前身Snipe1832年才首次出現,據考源自英國殖民官員在印度鄉間的游獵活動。Snipe(鸻形目鷸屬之鷸鳥,亦名沙錐鳥)是一種靈活的小鳥,極難獵捕,這種需要高超射擊加潛行技術的運動于是以snipe名之。狙擊手(Sniper)一詞即由“獵鷸者”轉化而來,高精密度的步槍也因之被稱為“狙擊槍”(Sniper rifle)。一戰期間,Sniper取代Sharp-shooter成為狙擊手的專稱,除了強調射擊的精準,還包括隱藏自己行蹤的能力。
“狙”,漢語本義就有“窺伺/覬覦”(狙伺)、“詭詐”(狙詐)、“偷襲/突襲”(狙擊)等意思,所以以“狙擊手”譯Sniper,差不多可稱絕佳。
神射手(Sharp shooter)一詞明顯褒義,聽起來感覺較正面,而“狙擊手”則有點復雜曖昧。從專業角度講,后者不止要有超凡的射擊技術,還需經過嚴苛的偽裝、潛行、偵察等特種訓練,其綜合素質遠超一般的“神射手”。不過在大眾印象中,“狙擊手”就是行蹤詭秘的謀殺暗算者(約等于“特務”、“間諜”一類),因不夠光明正大而近于反派。大概是緣于“神射手”之名的中性,連國外治安單位對轄下射手都稱“神射手”而非“狙擊手”。
雖同為殺手,戰時服務于軍隊和平時任職治安單位的“狙擊手”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以下所述,主要以戰爭中的軍人“狙擊手”為對象。
如果不以發射子彈的火器為限定標準,那么可以說冷兵器時代同樣存在“狙擊手”或“狙擊”行為。再如果“狙擊”以暗中隱匿射擊為定義的話,史上最早有記載的狙擊應該發生在特洛伊:當天下無敵的阿喀琉斯在特洛伊城門前耀武揚威之際,赫克托耳的弟弟、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經太陽神阿波羅指點,自城樓上發暗箭擊中其腳踝命門,刀槍不入的希臘第一勇士因此殞命沙場。
現代意義上的狙擊則離不開槍械的發展。近代火槍設計制造的兩大發明一是膛線,一是瞄準裝置。據記載,螺旋式膛線的使用開始于十六世紀初的德國紐倫堡地區,而最早的一支有膛線的槍則是1544年在瑞士制造(此槍現存蘇黎世博物館)。瞄準裝置的發明大致也在同時,當然只是最基本的準星、照門而已。有了膛線和瞄準裝置以后,射擊準確度大大提高,距離可達二百公尺之外。傳說大畫家兼發明家達·芬奇曾攜自制來復槍登上佛羅倫薩城墻,向圍城敵軍射擊,竟然一舉命中三百公尺外的目標。
盡管前膛來復槍已在中歐大量使用,但由于其裝彈太過困難耗時(因彈頭與膛線緊密咬合),各國部隊的配備仍然以滑膛槍為主。問題是滑膛槍的殺傷力極為有限,以二百多年后美國獨立戰爭中的英軍標配——著名的Brown Bess滑膛燧石槍為例,其有效射程僅八十碼(一說五十碼),超距離被打中的人只能說是運氣極背。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北軍的柏丹上校于1861年招募了兩團神射手(大名鼎鼎的“柏丹射手”),不過主要是充任主力部隊的前衛,遇特殊情況才派作狙擊手用場。由于資源短缺,南軍沒有龐大的狙擊手編制,然而戰果卻堪稱輝煌——四年戰爭期間,至少有三名北軍將領成為狙擊手的槍下之鬼,中下級軍官更是傷亡者眾,連林肯在視察前線時也差點被獵獲。
當時南方狙擊手配備的是帶三倍瞄準鏡的英國魏渥斯步槍(Whitworth rifle),據說曾創下八百碼的遠距離狙殺紀錄。
1914年一戰爆發,德軍針對“塹壕戰”緊急訓練狙擊手(多選有狩獵經驗者進行特訓),并訂購大量狙擊步槍和瞄準鏡,分配到前線每個步兵連。這使得德軍狙擊手一度主宰了戰場,英法聯軍陷入被動挨打態勢。
面對威脅,聯軍自然要進行反制,但由于英國上個世紀對民用槍支進行嚴格管制,一般老百姓都甚少射擊/狩獵經驗,因此發往前線的狙擊槍十有六支被誤用。英軍的狙擊手速成班也因僵化守舊,設備教材兩缺,徒費人力物力效果不彰。直到1916年赫斯·克皮理查少校主持的第一軍團狙擊學校成立,英軍才逐漸組織起有效的反擊。
在西方傳統的戰爭觀念中,兩軍對陣應光明磊落,狙擊放冷槍的行為雖屬必要之惡,卻只在戰時臨場搭建應用。故而狙擊戰術在一戰后再遭雪藏,并未繼續被各國軍方重視。
二戰初,歐洲戰場多為大兵團作戰,勢如破竹的德軍無暇顧及狙擊小道。倒是蘇軍為遲滯對方攻勢使盡渾身解數,訓練狙擊手消耗德軍有生力量即其中之一。1942年,紅軍被鼓勵參加一個名叫“狙擊手運動”的射殺法西斯競賽,創造四十次擊殺紀錄的士兵即獲得勇敢勛章和“卓越狙擊手”稱號——這大約是“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戰時延伸。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紅軍于圍城內設狙擊學校,現炒現賣,德軍第六軍團被大批速成狙擊手吸入街巷戰的泥沼——《兵臨城下》所述蘇軍準尉扎依采夫與德軍科尼格少校極富戲劇性的狙擊對抗,就是發生在上述背景下。
英國軍方對狙擊重視有限,1943年秋才設置第一所狙擊學校。美國陸軍則任由各部隊長自行決定狙擊戰術的運用。結果在意大利/諾曼底戰場,德軍狙擊手一度讓盟軍寸步難行。endprint
值得一提的是德、美對夜間狙擊裝備的開發:德軍用于突擊步槍的“吸血鬼”紅外線夜視鏡于1945年初試用,曾在德西黑森林把英軍一個排的巡邏隊干掉大半。美軍則為M3卡賓槍裝上紅外線照明燈及瞄準鏡,據稱琉球登陸戰首周內,有百分之三十的傷亡日軍跟這些帶夜視鏡的槍械有關。
二戰凸顯了狙擊手的重要性,可一當戰爭結束,狙擊又被束之高閣。進入部隊正式編制的只有蘇軍狙擊手;英國海軍陸戰隊與傘兵也保持了狙擊手的訓練與編制。
越戰在美軍的狙擊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對付行蹤不定的北越小部隊,使用同具機動性的狙擊手再合適不過。美國海軍陸戰隊將雷明頓M700-40用作正式狙擊槍,同時開發了各類夜視裝備。陸軍第九師的Adelbert F.Waldron與海軍陸戰隊的Charles B.Mawhunny是越戰最高狙擊紀錄的保持者。
二十世紀后半葉至今,在一些低度沖突地區使用狙擊手的需求日益凸顯。隨著國際恐怖主義行為的增多,反恐部隊對精確狙擊提出了更高要求,從貝魯特、巴拿馬、索馬里一直到阿富汗、車臣、科索沃、波斯灣……狙擊手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作用在較大規模戰爭里也不可小覷。以俄軍同車臣武裝在格羅茲尼市進行的兩次大規模巷戰為例——作為當初按要塞設計建造的格市,城內堡壘星羅棋布,易守難攻,車臣狙擊手依憑熟悉地形,自隱匿處逐一射殺俄軍。1995年第一次巷戰結束時,據說突入市區的一個俄軍團僅余十一名官兵活著離開,二十六輛坦克有二十輛被擊毀,一百二十輛裝甲車只剩下十八輛,車臣武裝將俄軍死尸堆成“人體街壘”以遮擋子彈。在1999到2000年間爆發的第二次巷戰中,俄軍更是尸橫遍野,多達一千一百七十三名士兵陣亡,連俄集團軍副司令員馬洛費耶夫少將也被擊斃。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普京無奈下令轟平了格羅茲尼,然這座小城已成為俄軍永遠的傷心地,兩次巷戰亦因“越戰后最殘酷最血腥的巷戰”之謚而名聞遐邇。
作為一種專業的狙擊及作為一種職業的狙擊手,在常人眼里無疑籠罩著神秘與傳奇色彩——對此,一些以狙擊手及狙擊生涯為題材的書籍/電影提供了再好不過的證明。然而任何對象,一旦被納入文學藝術范疇,其真實性與可信度就難免大打折扣。
“漫長的孤獨、忍耐和等待”,這個簡單的描述大約比較接近真實的狙擊手生活了。無論在山間野地還是城鎮街巷,狙擊手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選擇合適隱蔽場所,徹底偽裝、藏匿自己,在對手的視覺、嗅覺甚至第六感里隱形消失,然后靜靜地觀察,等待。保存自己,發現目標而盡可能不被目標發現,這是一個成熟狙擊手所需達成的第一要務。
等待并非意味著悠閑——觀察、追蹤、地圖判讀、細節的關注分析、進入與撤退、戰術計劃的擬定等,都需反復謀劃斟酌,最困難之點在于,你無法確知獵物會在何時出現(亦即難以預測機會與危險何時降臨),多數情況下機遇都如電光石火般瞬時即逝,你必須以兔起鶻落般的迅捷去躲閃或者擊殺。對狙擊手而言,等待中的分分秒秒都足夠緊張,足夠驚魂,因而,堅韌神經與超強的心理素質比技術更為重要。
不能不提到的一位狙擊手:芬蘭人西蒙·海耶(Simo hayha)。
西蒙·海耶,專業獵人出身,世界最高獵殺記錄保持者,有“白色死神”之稱的狙擊之王。在1939-1940年的蘇、芬戰爭中,海耶以不到四個月的時間,用芬蘭版莫辛納甘步槍狙殺了五百四十二名蘇軍(一說五百零五人),平均每天殺敵超過五人。
腳蹬滑雪板,身著白色偽裝服,冒著攝氏零下二十到四十度的嚴寒,率狙擊小組在皚皚雪地中悄無聲息來去自如,而身穿棕褐色制服,在大雪泥濘中掙扎的蘇聯紅軍則成了芬蘭狙擊手射殺的活靶子——這就是當年以“Motti戰術”重創入侵者的芬蘭士兵的日常戰斗場景。
據說西蒙是一位不用瞄準鏡的“神人”,他認為狙擊槍的準星是上帝賜予的最好瞄準工具,因為在雪地里,瞄準鏡有可能被日光反射,這容易暴露自己,給對方可乘之機。
1940年3月6日,海耶在近戰中被蘇軍狙擊手擊中下顎,子彈向上貫穿左腦。可他成功退出了戰斗,在進行面部再造手術后奇跡般復原,一直活到2002年去世,成為世界著名狙擊手中享壽最高的人。
網上流布有一個不那么靠譜的“世界狙擊手排行榜”,在這份四十余人的榜單上,筆者驚訝地發現了三位女性(均為前蘇聯軍人),其中排位最靠前一位的狙殺紀錄是三百零九人。
這位名叫柳德米拉·米哈伊爾洛夫娜·帕夫利琴科的狙擊手,1916年出生于烏克蘭的貝里亞·特沙科夫,1941年參加蘇聯紅軍。蘇方稱她在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共擊斃三百零九名德軍,1943年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1945-1953年晉升為海軍少將,1974年10月10日病逝。在位于莫斯科的一座公墓的墓碑上,鐫刻著柳德米拉生前最喜歡的詩句:“痛苦如此持久,像蝸牛充滿耐心地移動;快樂如此短暫,像兔尾掠過秋天的草原。”
掐指計算,此人只活了五十八歲。生命如此短暫,除了戰爭給一位女性的身體帶來的創痛外(1942年6月,她曾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中被德軍的迫擊炮彈炸傷),還有沒有更復雜的原因?從那座公墓墓碑上的詩句里,人們是否能讀出一些信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