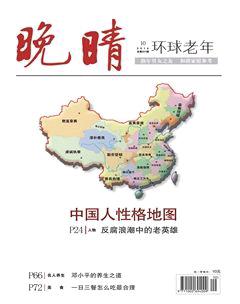“中國性格”和“中國夢”
張頤武
什么是“中國性格”?今天我們所不斷試圖努力去發現和展現的中國人的性格究竟是怎樣的?中國人的形象究竟如何?這些問題在今天中國崛起,一個“新新中國”開始吸引世界的關注之后,變得異常地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這里,其實我們強烈地期望通過對于“中國性格”的關切,讓世界對于中國人的新的形象有更多的了解,期望中國人的形象從過去的刻板的印象中脫離出來,讓世界重新感受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魅力和活力。
這種期望其實是今天我們探討“中國性格”前提和條件。這其實是我們超越現代以來對于“中國性格”的舊的觀念和意識,在一個新的中國崛起,“新新中國”開始為世界所認識的時代中去尋求新的可能性的歷史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展現。
其實,“中國性格”在現代以來其實一直是我們感到困擾的問題,也是我們在現代面前的焦慮的根源。由于中國在近代以來積弱和貧窮,使得中國人對于自身的文化產生了巨大的不安和困惑。據許壽裳回憶,魯迅先生早年在東京弘文書院學習的時候“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的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這可見當時他的思想已經超出于常人。”這里魯迅先生的三個問題,其實就是現代中國一直貫穿的“國民性”批判的話語的核心,其實也是現代中國對于我們自己的反思意識的最為關鍵的部分。這三個問題其實是從負面理解中國性格的局限和問題的,并通過這樣的追問來達到對于“國民性”的改造的目標的。這三個命題可以說是“現代”中國改變自身命運的核心的意識。
“民族精神”的歸依
因此,“國民性”批判是現代的“中國性格”的具體的起點。魯迅先生的小說所尖刻批評的麻木、茍活等等“性格”弱點,和時時被我們自己詬病的諸如隨地吐痰、大聲喧嘩這樣的生活細節都變成了需要改造的“國民性”的一部分。當時人們認為,正是這種“國民性”從“內部”導致了中國的積弱和落后,也導致了中國的貧窮和屈辱。“中國性格”其實在五四時代通過“國民性‘的反思,在“具體”的層面上受到了尖銳的批判和否定,這種批判和否定其實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中仍然主導著我們對于自身的認識。許多人都曾經指出,魯迅先生的“國民性”批判深深地受到了當年西方傳教士對于中國人性格的諸多評說的影響。魯迅先生其實是通過西方人的外部的觀察來確認這個“具體”的自我的形象的。
與此相伴,中國的“現代性”在對于“具體”的“中國性格”以“國民性批判”方式加以否定的同時,也通過對于“民族精神”的召喚和肯定來樹立“中國性格”在“抽象”方面的力量。如最深切地批判中國的“國民性”的魯迅先生本人就對于“中國的脊梁”加以肯定,對于中國的精神加以弘揚。在“否定”“國民性”的種種表現的同時,卻異常堅定地肯定中國人的抽象的力量。而這種“抽象”的肯定其實也是中國民族在現代的世界上存在的理由和依據,這種精神也是中國人從遠古生存到今天的價值所在,也是中國走向富強和繁榮的歷史和現實的依據,也是中國必然崛起的歷史的要求。
正是由于我們知道自己的存在和價值有一種必然的歷史的意義,我們的“民族精神”依然是我們的認同的來源和精神的歸依,于是,我們才會認識到改造“國民性”的意義和價值,才會有讓中華民族再度崛起的歷史的宏愿。因此,我們對于“中國性格的認識在整個中國的現代歷史上就有兩個方面,我們在“抽象”地肯定自己的“民族精神的同時,“具體”地否定我們需要改造的“國民性”。這樣的“抽象”和“具體”的兩面性正是我們對“中國性格”思考的關鍵。沒有“抽象”的肯定,我們無法建構自己在世界上生存和發展的理由,而沒有“具體”的否定,我們又沒有對于“落后”的認識和覺醒的依據。這種“抽象”肯定和“具體”否定其實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地銘刻在我們的身上,如陳凱歌的《黃土地》里的兩個群體性的場景正好是這種“肯定”和“否定”的結合。讓人感動的“腰鼓則是中國人的“抽象”的生存力量和精神的展現,而“求雨”則是“具體”的愚昧和落后的表現。其實《我的團長我的團》中的散兵游勇是“具體”的中國的“國民性”的表現,而龍文章的勇氣則是“抽象的民族精神的表現。這說明現代以來為先輩們為我們標定的關于“中國性格”的界限對于我們有如此深刻的影響。
“新新中國”的崛起
在今天,“新新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告別貧困和積弱的過程正是和中國的全球化的進程相聯系的。現實已經在在要求我們超越這種對于“中國性格”的“抽象”肯定和“具體否定,而是尋找我們自己的新的形象。
在這里,一方面,我們需要超越“國民性”話語對于我們的具體的否定,而是尋找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對于我們的具體的文化身份的建構有用的符號和表征。我們會驚異地發現,正是由于現代以來的“具體”否定,我們丟掉了如此多的具體的文化的傳承。而這些文化對于我們的文化身份來說是異常重要的。我們開始認識到,許許多多我們認為是中國“國民性”弱點的問題,其實是人性本身的局限,也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條件相關聯。而不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的問題。因此,我們通過許許多多具體的文化的尋找來發現和充實“中國性格”的具體性。今天無論是讀經、祭祀還是恢復傳統節日等等,都是我們對于具體的“中國性格”尋找的一部分。我們發現,正是這些具體的事物才賦予了我們“性格”。如奧運會開幕式的那些具體而微的中國符號都是中國的文化自信的表現。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再僅僅對于“民族精神”進行抽象的肯定,而是以更加開闊的歷史視野和更加全球化的意識,來對于我們自己加以自覺的審視。因為,今天的中國已經具有了更多的力量,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新的全球化中的關鍵性的“位置”,有更多的自覺性來賦予自己新的開放的性格。也就是說,在“具體”的方面,我們更多地找回傳統的符號和價值,獲得更多的自信。在“抽象”的方面,我們對于自身有更多的自覺,把我們的“具體”的事物融入到人類的普遍性之中。
“中國性格”的這些新的發展,其實就是三十年來我們對于“中國夢”的追求超越了我們的“國民性”的限定的結果,是中國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開始重新建構的巨大的可能性。
“新新中國”的中國夢的偉大的旅程為我們正在為我們創造新的“中國性格”。這個“中國性格”正像魯迅先生在1908年時所期望的那樣:“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
“新新中國”需要新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需要新的“中國性格”。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