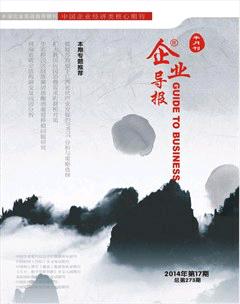打開一扇長篇小說文體研究之窗
陳進武
摘 要:晏杰雄《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研究》是國內對新世紀長篇小說進行專題考察的少數專著之一。該書顯著的亮點是跳出了既定的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有意識地理清了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的相關問題,提出了一系列較富原創性的觀點,從而確立了考察長篇小說文體的理論模式與研究范式。
關鍵詞: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專題性;原創性
一
上世紀80年代,小說文體的變革一度成為了學術界集中談論的重要話題。有關小說文體的研究,或宏觀考察小說文體的問題,或微觀探討小說的語言功能與風格、敘事觀念與技巧、結構方式與形態,以及具體小說的文體特征,等等。然而,盡管已有研究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反映了小說文體功能的某些問題,但在理論層面上并未取得多少實質性的突破或獲得可資借鑒的學術成果。究其實,一來,近些年來的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是龐大的研究對象,包括文體在內的任何角度的切入都是繁重而又巨大的挑戰;二來,小說中的文體并不是簡單的技巧問題,而小說的發展演進必然會出現小說文體的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界定“文體”尤其是長篇小說文體的基本范疇,歸納出小說文體的演進脈絡與總體趨勢。如何突破既有的研究模式,找尋到進入小說文體闡發的研究支點,從而把握小說美學規律以及提供小說文體研究的有效學術范式等。這些無不是在顯示著系統性、整體性與學理性的研究小說文體問題是一大難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晏杰雄的新著《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研究》(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3年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
12月版)恰是從新世紀文學研究的這一難題出發,積極回應了被學術界忽略或有意回避的重大命題。這部著作呈現出了著者敢于挑戰學術難題的勇氣與智慧,更為重要的是,該書對于“新世紀長篇小說創作如何健康發展,如何建立屬于本土的現代小說詩學和走向世界,具有不菲參考作用。”[1]
如今,當代文學已經進入到了長篇小說的時代,面對龐大的文學實體,學術界進行新世紀長篇小說研究的契機真正出現了,而文體研究無疑是最為可行的切入視角。正如著者在“導論”中所說的:“本書將從文體的角度對新世紀長篇小說進行整體考察,致力于揭示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的內在規律和美學品格,為長篇小說詩學的良性發展提供一個理論參照體系,為提升民族文學自信力提供證明材料,并以某一具體文體的專門研究,豐富和深化新世紀文學的理論體系建設。”[2]27著者立足于本土語境,去發掘新世紀長篇小說的審美特征,從而確立起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文學坐標。該書的不少觀點不僅見人之所未見,發人之所未發,而且也充分地體現了著者不凡思辨的能力。
該書由導論、結語與六章構成。一開篇著者便對新世紀以來長篇小說這一文學文體的盛大化與經典化以及審美元素的內化整合現象進行了有意義的探尋。接下來,著者用三章的篇幅,宏觀地剖析了新世紀長篇小說的基本問題、歷史脈絡與整體特征。其中,第一章界定了“文體”的本質是“人造物”,從文體的人造性出發,確立了敘述、結構與話語等三個因素為長篇小說文體的基本范疇,并分析了長篇小說為何成為“時代第一文體”的原因。第二章考察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長篇小說文體的演進過程,描繪了文體在一個時代之內從“萌發”到“揚厲”再到“沉淀”的自然生長過程,從文體自身運行規律的角度,揭示了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的轉變及其新的美學觀念。第三章重點闡述了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的內在化、本土化與混沌化等三大整體特征與美學風貌。然后,著者從第四章到第六章轉入微觀研究和個案分析,結合新世紀長篇小說文本,分別從敘述、結構與話語三個方面詳細分析了新世紀長篇小說的文體特征,勾勒出了新世紀長篇小說的文體全貌與總體趨向。這又與前面三章形成了某種呼應與互動。結語則指明長篇小說文體逐步進入成熟,而我們期待的長篇小說的黃金時代也即將到來。
二
談到小說文體的研究,評論家汪政和曉華一再表明,“討論長篇小說的文體實際上是一樁相當困難的事情,因為長篇小說的文體“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既在逐步開放著自己的疆域和越來越多的吸納別樣的文體因素,又在外觀上依然呈現著敘述的體式和相當的敘述規模;它的主觀傾向日漸明顯,但還仍然保持著強大的客觀姿態;因為閱讀和傳媒的關系,它似乎有趨于簡單的跡象,但構筑龐大的敘事結構甚至重金裝飾,也還是一大批作家的喜好;究竟是走向世俗,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知識分子敘事,它似乎也搖擺不定。”雷達對著者的寫作難度也有這樣的估量:“一是閱讀的困難。二是概括的困難。三是資源的困難。”也就是說,新世紀文學累積有五六萬部長篇小說,如何選擇最具代表性的小說是很棘手的事情。同時,要從新世紀“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文學現象中概括出清晰的文體特征也是難度很大的。加之,作為“當代之當代”的新世紀文學可利用的理論資源相當匱乏,要找尋到闡釋和整合的資源難度也不小。顯見的是,這一著作最顯著的亮點并不是在于克服了研究的中所有難題,而是跳出了既定的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有意識地理清了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的相關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原創性的觀點,從而確立了考察長篇小說文體的理論模式與研究范式。
一是該書在梳理新時期以來的長篇小說文體發展歷程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向內轉”的觀點。著者認為,新世紀以來,長篇小說的文體革新由絢爛歸于平淡,并且出現了盡可能妥帖的與內容相結合的狀況,“長篇小說文體開始‘向下降和‘向內轉,越來越成為內在化的東西,文體的美表現為‘有意味的形式和不事張揚的自然美。”也就是說,從新時期到新世紀,長篇小說的文體和內容經歷了有合到分、由分到合的過程,這種回歸是螺旋式前進的,“文體由此達到了自己應有的位置,顯示出一種成熟內斂的風韻。”[2]
尤為引人注意的是,這些核心觀點之中還有著不少學術界尚未論及卻又是構成長篇小說文體理論體系的重要觀點。比如,新世紀長篇小說首要特征是內在化,救贖之途是本土化,而作為文體“理想之境”的混沌化則意味著文體圓熟的狀態。這種混沌化所產生的文體意味具有多向度的生成的可能性。在文體理論的具體構成上,其一,著者從敘述視角(全知視角的復歸與多樣視角的綜合)、敘述距離(零距離與大幅度距離)、敘述時間(順時序成分增加與敘事速度加快)與敘述空間(時間空間化與空間并置)等四個方面論證了新世紀長篇小說的“敘述減法”傾向。其二,著者從情節型結構(賦予故事性與內心的尺度)和開放型結構(生活流、心理圖式、系列小說以及空間并置)等兩種構造類型論證了新世紀長篇小說的“結構復歸”趨勢。其三,著者又從引語(直接引語增加與變體、自由直接引語的妥帖使用與自由間接引語的節制使用)和對話(微型對話、大型對話)等兩個基本方面考察了新世紀長篇小說“話語紛呈”的美學特征。可以說,這些關于長篇小說文體的觀點有著無可辯駁的原創價值,著者對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研究的關鍵問題所做的理論探討突破與深化了新時期以來小說文體的理論體系。
二是該書的理論出發點是“文體的本質是人造物”,這也是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理論體系構建的重要基石。不可否認,何謂文體?什么是長篇小說文體?這樣的問題并沒有統一而又被公認的學術定論。有學者將文體定義為“話語的組織、結構方式,是分析作品形式特征的一個概念”,但對于文體概念的這一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現代文體學研究格局的總體特點,即以語言形式作為文體研究的中心的傾向。”15當然,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進程中,長篇小說文體實際上呈現出了更為復雜的情況。這表明了要照搬西方的文體概念來闡釋中國當代小說尤其是新世紀長篇小說的文體問題是行不通的。對此,著者通過梳理國內外百十種關于“文體”的界定,結合自身對文學的體驗力圖對文體這一概念進行個人的理論建構。著者明確指出:“文體是文學作品中作為人造物的一部分,它規定作品的藝術特質,與作家的認知方式和現實世界存在一種對應關系。”[2]
37這也就意味著文體的本質是它的人為性,是文學作品之所以為文學的根據,而文體與作家哲學觀點及現實世界存在著隱性與間接對應關系。在對“文體”界定的基礎上,著者進而明確了長篇小說文體的基本范疇,亦即包括敘述、結構與話語三個層面,這些“最能體現文體作為人造物的幾個因素,內含著作家對小說的構造、設計和安排,與小說的內容、時代、社會、文化等非文體因素隱約呼應。”
當代作家格非曾指出:“中國當代的長篇小說創作似乎普遍存在著一種簡單化的趨勢,而其形式的真正成熟也許依賴著一種全新的創作方法的出現。”頗有意味的是,我們也似乎可以說目前學術界對長篇小說文體研究也普遍存在簡單化傾向,而真正成熟的研究同樣需要依賴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現。從這一層面來說,《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研究》這部著作正提供了這樣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其中不少觀點是當前小說文體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該書并不是用西方的“新理論”生硬切割當下小說文本,而是從個人的閱讀經驗與理論直覺出發,致力于小說文體問題的思考和透視,從而提煉出了新世紀長篇小說的詩學理論。
三
該書的特色還表現小說文體理論系統的建構是立足于詳實得當而又深入透徹的小說文本闡釋與解析之上的,這樣細致的文本剖析也貫穿于本書之始終。比如,著者對王葡萄(嚴歌苓《第九個寡婦》)到人家窯里幫忙公公討賬的對話的剖析就相當精細。王葡萄從早到晚守在人家家里等著給錢,問她餓不餓,她說餓,問她要不要喝碗湯,她答吃人最短,賬就收不回來了。要說欠的錢少,她便回應:“一家欠二斤,俺家連湯都喝不上了。”在著者看來,在大部分情況下,敘述者的隱而不露“往往為讀者提供一種雙重視角:我們得到了用主人公的眼睛觀看事物的印象,而在道德觀和價值觀上則始終是作者的主張。”[2]148然而,為了更生動地刻畫出王葡萄單純率真的可愛性格,敘述者對她的欣賞之情卻又在不經意之間流露了出來。這樣的敘述片段在小說平實的敘述之中顯現出了幾縷神性的光芒,使得小說主題在一定意義上得到了有節制的顯豁。又如,在閻真的《滄浪之水》中有這樣的對話:我說,說吧,說吧。他說,我真的從心里是這樣想的,您……我打斷說,說吧,說事情吧。他說,我,您看,我,我吧,研究生畢業都快八年了。從表面看,這是一段人物的口頭表述言語,敘述者也只是簡要而直接的記錄下而已。但從深層看,當了解到對話者是上級池大為和下級賴子云后,這段“我說——他說”的對話是意蘊便豐富起來了。正如著者所揭示的,“這些鮮活的人物語言,本身形成一股原生態的‘話語流,在小說內部一路流淌下來,再現了長沙市井小民庸碌的生活場景,同時把官場話語的暗藏玄機揭示得淋漓盡致。”
實際上,文本細讀本來就是文學審美批評的基礎,尤其是在長篇小說每年出版數千甚至上萬部的當下,能沉潛下來扎實閱讀大量的小說,這不僅決定了研究結論的嚴謹性與科學性,而且更是當前研究者個人優秀學術品格的見證。在這一點上,著者及其帶給讀者的研究成果恰恰體現了人文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擔當。當然,這種良知與擔當還表現在《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研究》至始至終都貫穿著著者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批評立場,尤其是顯現出了他鮮明的批評個性與批評風范。對于怎樣才算真正的批評家,他曾指出要做好批評家并非簡單的事,“拉幾個理論術語、概念或模式拼湊一篇文章是很容易的,真要把作品說清楚,說出真知灼見,說出普遍啟示、說出美的意味,就很難了。僅靠文學理論方面的專業知識是遠遠不夠的,需要批評家有廣博的知識面,有高度的藝術感悟力,有對世道人心的深刻洞悉,更重要的是‘跳入作者的世界,需要批評家對作品投入自己全部的生命體驗,和潛伏在文本背后的作者、人物、人群甚至整個人類進行深度的精神對話。所以,文學批評歸根究底不是一種學院派的知識生產,不是一種對文本的物質加工,而是一種生命活動和精神活動,是人和人之間打交道。”
需要承認,該書的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理論鮮活而又不乏靈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著者將理論建構與文學批評有效結合起來了。在著者看來,真正的文學批評是完整的、有力量的批評,是劃破文體的皮膚與小說的肌理,從而直抵小說精神內質的批評。正秉持著這樣一種文學批評理念,著者憑借敏銳的文學感悟力與開闊的理論視野深入地剖析了大量相關的長篇小說,力圖“跳入作者的世界”,并從紛繁復雜的具體小說創作現象中發掘了新世紀長篇小說的文體規律。換而言之,小說文本細讀與批評是圍繞小說文體理論問題的探討而展開的,這為系統構建起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理論系統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近些年來,著者一直投身于當代長篇小說研究,并且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與非凡努力,而《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研究》這部縝密、厚實且又富有創新價值的理論著作正是著者對小說文體潛心探尋的結晶。不過,我們也注意到,通透地研究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問題是難以做到的。因此,著者對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的考察,難免會在某些論述或某些觀點上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正如雷達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著作以新世紀長篇小說為研究對象,在整體上有“拔高”傾向,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這一時期長篇小說分層次的狀況。在我看來,除以上兩個方面外,著者對長篇小說文本的選擇上有令人質疑之處。不難發現,著者較多采用了個案研究的方式,試圖通過個案來取得論證觀點的合理性,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在于該書過于倚重一部分長篇小說,比如《秦腔》《玉米》《婦女閑聊錄》《村莊秘史》《我的丁一之旅》等,這也使得某些論述有值得進一步探討與闡釋的空間。然而,又必須承認的是,在如今操持“史詩性”等詩學話語難有作為的情況下,該書突破了傳統的研究模式,打開了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研究的一扇窗戶。這種對于小說文體理論系統的重新構架不僅對于將來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而且也起到了呼吁與激勵更多研究者來關注當前長篇小說詩學問題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滕艷.長篇小說文體研究的新收獲[J] .當代文壇,2014(2).
[2] 晏杰雄.新世紀長篇小說文體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3] 汪政、曉華.慣例及其對慣例的偏離[J] .當代作家評論,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