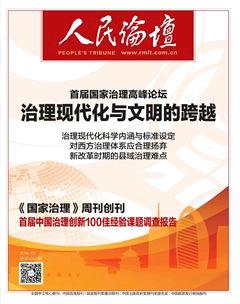踩在腳下的藝術
李心宇
在漫長的古代先民生活中,除了火之外,人們還用獸皮當衣服和被褥來防寒保暖、抵御潮濕。雖然天冷時,獸皮能起到保暖作用,但時間久了極易出現脫毛及糟朽問題,難以長久使用。于是,聰明的先民們開始尋找其他代替品。他們發現用羊毛捻線織毯能夠彌補獸皮的缺陷,還能抵御我國北方寒冷的天氣、隔離濕氣。至此,織毯技術慢慢傳播,日常生活中,逐漸有了毯的身影。
《物原》說:“毯,毛席也,上織五色花”,“神農做席,堯始名毯”。書中記載了遠古時期地毯名稱的演變。然而,幾千年后,絲綢之路釋放出讓地毯在中原地帶生根發芽的能量,也改變了地毯的身份,毯搖身一變,身份高貴了起來。這皆因織毯技術復雜、羊毛獲取不易,再加上運輸成本高,因此成品價格昂貴,地毯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原后就被少數貴族壟斷,“毯席干貝,亦比千乘之家”。
家必富貴
地毯的圖案紋飾與史前的陶器及殷商時期的青銅器一樣,記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變遷、宗教信仰、民俗風情及對“美”的創造與追求。
中國最早的毯是收藏在甘肅博物館的新疆東漢毯。在新疆出土的地毯有更早的,如新疆樓蘭的戰國羊毛地毯殘片是至今在我國發現的最早的手工打結羊毛地毯實物標本,但從染色、做工來看,它還不是手工打結地毯起源標本。
1959年,新疆民豐縣北的尼雅遺址夫妻合葬墓中,出土了一塊由棕、紅、中黃、淺黃、白等顏色組成的地毯殘片,在這塊毯旁邊還出土了一只與現代地毯廠使用的鐵耙子極為相似的木手。這塊毯子被證實是東漢時期織毯,現收藏于新疆博物館。此毯采用的打結方法至今在中國、波斯、土耳其等國仍在使用。可以斷定,雖然中國西北地區出土了很多地毯,但真正對后世影響深遠的還屬兩漢時期的手工打結地毯。
唐代宮廷設毯坊與氈坊,專為統治階級織造地毯。詩人白居易在《紅線毯》一詩中說:“彩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由于南宋遷都杭州,絲綢業發展迅速,但地毯織造業未見規模。直到元代,地毯織造才得以空前發展。因地毯是蒙古族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統治者更加重視地毯的生產。宮廷依舊設有專門的毯坊和氈坊。地方政府、諸王公貴族名下也有手工業局院,在元大都,僅宮營地毯作坊的織毯工匠就有2萬戶以上。盡管如此,這還不是地毯發展的最高峰。
伴隨著明清紫禁城的修建,以及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鼎盛時期的到來,地毯迎來了它的輝煌時代。整個明清紫禁城出現了“凡地必毯”的景象。明朝政府接管了元代毯坊,清代皇帝又從各地調手藝高超的毯匠到紫禁城專為皇家織造地毯。寧夏毯、藏毯、新疆毯、蒙古毯、北京毯均被裝飾在各個殿堂中。這幾大類別的地毯確定了中國手工地毯的織造技術和藝術風格。
大清皇帝偏愛地毯如偏愛瓷器。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二十五日,太監劉希文傳旨:“圓明園萬字房通景壁前,著畫西洋吉祥草毯子呈覽。”十月初一日,太監將畫樣呈皇帝御覽后,皇帝提出修改意見:“周圍的萬字錦邊不好看,另畫碎花,其地的顏色不必染黃。再圓明園殿上的毯子花樣亦不好,爾等亦畫樣。”幾經修改,待織出的地毯鋪在圓明園萬方安和屋內時,已是第二年的五月了。由此可見,在皇帝心中,毯是多么的重要。
為什么皇帝如此厚愛地毯?皆因“不計成本”。古代地毯選料精良,只有上好的羊毛才能織造地毯,而這些羊毛全部分布于寧夏、新疆、內蒙一帶,那時的羊吃的是一點污染也沒有的綠草,尤其是寧夏灘羊,喝的是賀蘭山流下來的天然雪水,產出的羊毛纖維均勻、手感柔軟,有絨毯之稱。織出的毯踏上去極富彈性,用手摸如綢緞般光滑。染羊毛的染料也是從天然植物和礦物中提取,如花果樹木的根、莖、葉、皮,其中不乏藏紅花等名貴的中草藥材。天然染料染出的地毯色澤柔和,顏色歷百年、千年不褪。
意必吉祥
中國古代紋飾有“言必有意,意必吉祥”之說。它們所表達的含義——富、貴、壽、喜四個內容是認知民族精神和民族旨趣的標志之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地毯的紋樣非常豐富。動物類有龍、鳳、麒麟、獅子、鹿等;花草類有牡丹、桂花、茶花、西番蓮、梅蘭竹菊、纏枝、卷草等;佛道類有佛八寶、暗八仙、佛人、金鋼杵、萬字等。不同類別地毯上面的紋飾還和當時的宗教信仰及政治策略有關。
寧夏毯分兩大類,一類是寺廟毯,一類是禮品貢品毯。寺廟毯多佛道符號,禮品貢品毯多吉祥富貴符號。這和當時的歷史背景有一定淵源。1697年,康熙皇帝將賀蘭山以西的阿拉善劃為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碩特部駐牧地,立阿拉善厄魯特旗。1730年,雍正皇帝在阿拉善設定遠營,以扼守賀蘭山通往內地的隘口。與此同時,藏傳佛教傳入阿拉善,大規模建設寺廟,朝廷指定在寺廟內鋪寧夏毯。還有一部分進貢朝廷,作為特供毯。這個做法既拉動了當地織造業的繁榮,還實現了清政府施行“懷柔”政策的策略。清政府為加強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統治,實現國家統一,對蒙藏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習俗為治”的方針。“興黃教以安眾”,反映了清政府尊重蒙藏宗教信仰的想法,同時拉近地方和中央政權的關系。所以,我們才看到寧夏毯與藏毯中有那么多與佛教相關的符號。可以說,上面的每一個紋飾符號都表達了當時社會大一統的呼聲。
西藏地區盛傳藏傳佛教,有寺廟毯和民用毯兩類。與寧夏毯一樣,寺廟毯紋飾多佛道符號,且多采用“黃教”崇尚的黃色。民用毯則多鮮艷的花卉紋及來自中原絲綢的紋樣。
與藏毯相比,新疆毯除了表現本民族特色外,還深受伊斯蘭教影響,紋飾圖案帶有異域風情。如各種顏色的花草、穆斯林神燈、巴旦果、麥加之石等都是主要的裝飾題材。新疆毯中最著名的是盤金絲毯和盤銀絲毯,就是將金銀絲用四股或五股金絲或銀絲合捻后,盤成“人”字紋與彩色絲絨花紋共同組成富麗圖案。這種毯量非常少,目前在故宮博物院和布達拉宮有少量收藏。
自古滿蒙是一家,清代滿族先祖與蒙古族人生活習慣相似。清太祖時期,八旗軍的大帳內就以毯做內飾。入關以后,從順治起,宮中設氈、毯、簾三項為一庫,并配置工匠。因清政府在漠南蒙古新建寺廟,蒙古毯紋飾也多佛教符號。不過包頭的“白三藍”毯則像“元青花”一樣名揚四方。
北京毯制作工藝雖然自元代就已發展成熟,但并未在民間流通,只在宮內織造,至清晚期發生根本變化,由宮廷轉向民間,跨入近代地毯生產行列。因是皇家用毯,故宮廷奢華味道濃厚,紋飾常根據宮內各殿功能所需而設計。龍紋、錦紋、云紋、海水江崖紋、纏枝蓮紋、各種花卉紋等常見,這些紋飾明確傳達著皇權的不可侵犯。
(摘自《中國收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