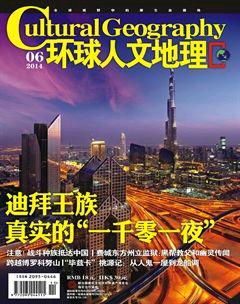穿越瓦罕走廊的多元文明

唐榮堯
信奉并堅持獨立精神下的田野人文地理寫作者、行者、修者和學者。迄今出版個人詩集《騰格里之南的幻像》;歷史散文《王朝湮滅——為西夏帝國叫魂》、《王族的背影》、《西夏帝國傳奇》、《消失的帝國:西夏》;人文地理散文《寧夏之書》、《青海之書》、《大河遠上》、《影像青海湖》、《中國新天府》、《文字背后的美麗》、《秘域》、《中國回族》(合著)、新史學專著《西夏史》等。
一場場殘酷的廝殺后,大唐軍隊的獵獵戰旗終于被撕裂于阿拉伯彎刀之下,從亞洲西部而來的遠征者,帶著勝利者的驕傲和笑容,循著唐軍敗退的路向,穿越瓦罕走廊而來……隆冬季節的瓦罕走廊,靜靜臥在冰雪中,視野中空無一人。這種空寂讓我想象瓦罕走廊曾經的盛景:一條順暢的文明之河,輸送著不同文明來往于帕米爾高原兩側。
千百年來,瓦罕走廊一直以高蹈的目光肅穆地俯視著亞洲大地,洞察著東來西往的客商、僧侶、軍隊穿行于帕米爾高原。它就像一條血管,迎來或送往亞洲的各種先進技藝、文化或文明,它們在這里做短暫的停留或交錯后,各自沿著命定的路向,抵達所在的歸宿地。來自中國的儒家文明、印度的佛家文明、從西亞輾轉而來的希臘文明、從阿拉伯半島和波斯高原上迅疾而來的伊斯蘭文明,就沿著這條血管,在瓦罕走廊匯聚、發散后,經過時間的緩慢加工,繪就了亞洲的文明畫卷。
影響深遠的怛邏斯之戰
1000多年前,任何一個像玄奘去天竺取經的內地來者,像任何一個到帕米爾高原西側去執行軍事任務的大唐將士,穿越瓦罕走廊時,還有著“此乃國內”的心理。然而,當阿拉伯戰馬馱負著波斯遠征者抵達走廊那頭時,沖突就開始了。
我開始懷想那位帶著大唐遠征軍穿越這里的將軍高仙芝,我的眼前再次浮現出大唐在這里的一幅圖景:朝廷設置了有效的軍事管理機構,當高仙芝帶領大唐遠征軍穿越瓦罕走廊,進入今天的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境內,并設置了軍事機構后,整個帕米爾高原都納入了大唐帝國。
站在瓦罕走廊中,我突然發現一個巧合:這里距離大唐帝國的國都長安和伊斯蘭教的圣地麥加幾乎一樣遠,都在4000公里左右。從兩個城市出發的兩種文明,抵達這里時,改寫亞洲文明史和宗教史的一幕出現了。
公元713年,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國向東遠征到4000多公里處的怛邏斯(即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從此和大唐軍隊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交鋒。當時,已經完全領受伊斯蘭教的屈底波,統帥著東征的阿拉伯人穿越波斯高原,奪取了中亞的布哈拉和撒馬爾罕。不久,他接到唐玄宗讓使臣帶去的一封信,希望他遣使長安,進行交流。屈底波傲慢地將信扔在了一邊,向唐朝使者揮起了波斯彎刀,并將刀鋒開始伸向帕米爾高原深處。屈底波的傲慢和對大唐帝國疆域的覬覦,挑戰了大唐帝國的尊嚴,于是唐玄宗下令唐朝軍隊向西穿越帕米爾高原,志在奪回怛邏斯。
得到唐軍進入帕米爾高原的消息,阿拉伯帝國駐巴士拉的東方總督艾布·穆斯林立即展開布置,讓部將賽義德·本·侯梅德帶領數千人的先遣部隊搶先駐守在怛邏斯城中,為阿拉伯軍隊的集結贏得了時間。
唐朝軍隊攻城不克,身為統帥的高仙芝沒有覺察到一場看不見的危險正在逼近:以快速奔駛著稱的阿拉伯戰馬馱著他們的主人很快集結到了怛邏斯另一側,從背后襲擊了唐軍。雙方在怛邏斯河兩岸展開了決戰。高原反應、長途行軍以及后勤保障跟不上,加上唐朝的葛邏祿部軍隊臨陣叛變等原因,導致唐軍失敗。
伊斯蘭文明進入中國
那場慘烈的戰爭中,1萬多名唐朝軍人被俘。俘虜中,有一個叫杜環的隨軍書記官。他和其他被俘的唐朝軍人跟隨阿拉伯軍隊轉戰于中亞、西亞,并曾到地中海沿岸等地區游歷、居住達10多年之久。阿拉伯人在清點俘虜時,在俘虜們身上發現了其攜帶的紙張,于是那些有造紙技術的工匠受命,不久就在撒馬爾罕修建了大唐疆域之外的第一個造紙作坊。
對于中國,怛邏斯之戰無疑是自唐宋以來影響最大的一場戰爭。俄羅斯歷史學家巴爾托里德這樣認為:“中國文化和伊斯蘭文化這兩種文化,究竟哪一種應當在河中(即中亞河中地區,包括今烏茲別克斯坦全境和哈薩克斯坦西南部)居統治地位的問題,就是由這次戰役決定的。”
一場場殘酷的廝殺后,大唐軍隊的獵獵戰旗終于被撕裂于阿拉伯彎刀之下,從亞洲西部而來的遠征者,帶著勝利者的驕傲和笑容,循著唐軍敗退的路向,穿越瓦罕走廊而來。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使節、傳教者緊隨其后,開始前往中國,他們在帕米爾高原西側經過充分的準備后,開始上路了,他們的目標便是帕米爾高原東側的中國,瓦罕走廊就是他們的必經之路。為人們熟知的是,這里是絲綢之路的要道,是佛教進入中國的第一站;不為人們所知的是,這里也是伊斯蘭文明進入中國的第一站。
法國學者魯保羅在他的《西域的歷史與文明》中這樣寫道:“在整個西域,穆斯林的長老、商人、旅行家們于口袋中裝著《古蘭經》,成了宗教傳播者。許多中文和阿拉伯文資料都指出,他們自公元7世紀起,便在亞洲四周存在。”站在瓦罕走廊,我想起魯保羅的這句描述時,眼前仿佛閃過這樣一幕:怛邏斯之戰后,那些伊斯蘭教的傳播者在這里停留時,從口袋里掏出《古蘭經》,念誦的聲音在瓦罕走廊上輕輕回蕩,影響了分布在走廊上甚至更遠地區的人們。
崇拜雄鷹的塔吉克人
塔吉克人是瓦罕走廊上的土著居民。“塔吉克”一詞為波斯語,意即“戴王冠者”。塔吉克族的祖先是古老的塞人,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這些塞人開始信奉瑣羅亞斯德教(又稱襖教或拜火教,曾隨絲綢之路傳進內地),他們心中的保護神是一位叫阿胡拉·馬慈達的太陽神。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圖騰崇拜,比如漢民族的龍圖騰、蒙古族的狼圖騰、哈薩克族的白天鵝圖騰。而生活在帕米爾高原的塔吉克人,則尊崇翱翔于天地間的雄鷹。
伊斯蘭教傳到瓦罕走廊時,他們被迫改信伊斯蘭教。按照伊斯蘭教規定,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是不允許動物崇拜的。一種文明落地于異域時,必然有個本土化的過程,因此,塔吉克人接受了伊斯蘭教,卻也保留了對鷹的崇拜和敬重,馴鷹、獵鷹、吹奏鷹笛、跳鷹舞等習俗保留至今。他們做禮拜,但不像內地信奉伊斯蘭教者那樣興建清真寺。拿塔吉克人的話來說:“我們的清真寺是建在心里的,不是建在別人的眼睛里的!”這便是我在瓦罕走廊沒看到清真寺的原因吧。 當地的塔吉克人做禮拜,一般每天只做兩次,而且在他們的習俗中,只有40歲以上的人才去做禮拜。
這是隆冬季節的瓦罕走廊,偶爾有幾戶塔吉克人的房子將土黃色倔強地亮于白色大地和山巒中,靜靜臥在冰雪中,村子里看不見人進出,路上更是空無一人。這種空寂讓我一次次想象瓦罕走廊曾經的盛景:一條順暢的文明之河,輸送著不同文明來往于帕米爾高原兩側。我尤其想象著高仙芝戰敗后的瓦罕走廊,戰刀后的經書,帶著伊斯拉文明傳播的使命,被一批批傳教者從這里帶向中國的西部乃至內地;清代的瓦罕走廊,由于國勢退萎,一度被沙俄勢力和英國軍方覬覦,部分路段甚至被割據而出,這便形成今日的瓦罕走廊。中國境內的這100多公里的路段,像個不規則的紐扣,將中國、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四國的衣襟連在了一起。一只在此展翅而飛的雄鷹,頭稍微一偏,眼神便會落在另一個國家,這便是鷹看四國的景致吧!
這條走廊,也是一部千年文明史中佛淚長落之地,更是一部近代史中邊境變遷的見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