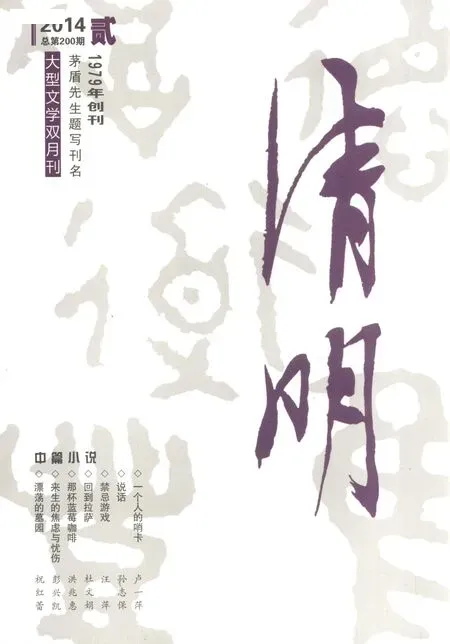一個人的哨卡
2014-11-17 12:32:06盧一萍
清明
2014年2期
盧一萍
一個人的哨卡
盧一萍
1
8月31日晚上,天堂灣邊防連連部通信員凌五斗終于下了決心,要對連長說,他不想當這個通信員了,他想去干點別的。
小小的營區很靜。軍犬不時無聊地吠叫兩聲,聲音散漫。發情的軍馬的嘶鳴讓人心碎。
軍醫程德全的二胡催人淚下。他小時候學過二胡演奏,開山時讓人帶了一把上來。他第一次拉《二泉映月》時把兵們眼睛拉潮了,指導員批評他“霏(靡)霏之音,擾亂軍心”。他就只拉些革命的曲子了,全像火車吭哧吭哧勇往直前的那種。但不管什么曲子,只要用二胡拉出來,總帶著哭音。如果說前一次拉的曲子像女人在嗚嗚咽咽傷心哭泣的話,其他的就像是一個男人在激昂地哭訴了。他跟凌五斗說過,二胡是一種哭泣的樂器。
房間里除了一種觸摸不到的特殊空氣外,只有鬧鐘的嘀嗒聲。凌五斗翻開日記本,他想把今天的事記下來。但今天的事和以前每一天都差不多。他把昨天的日記讀了一遍——
我醒來時是7點41分,我幾乎每天都是這個時刻醒來。外面的天已亮了。連長仍睡著,穿著襯褲,打著很響的呼嚕。我看了一眼他的臉,我想看出他對我的好感來,但是沒有。他睡著時的神態里沒有,呼嚕聲里也沒有。他臉上滿是對我的厭惡之情。
房間里充滿了睡眠后留下的味道。
我在心里嘆息了一聲,準備躺到7點50分。我開始想昨夜是否做夢了。沒有。我心里充滿了憂傷。時間到了,我開始輕悄快速地穿衣服。整理好內務,沒有超過5分鐘。……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