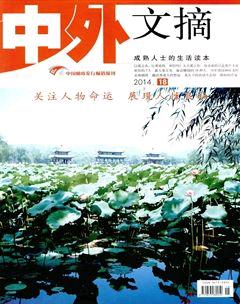愛與恨中滋長的鄰國之戀
蔣波
一切都得從1868年說起。時年,日本國孝明天皇駕崩,16歲的小皇子睦仁匆匆即位。當朝大臣們游目于卷帙繁浩的中國典籍,終而相中了《易經·說卦傳》里的句子——“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自此,年輕的天皇改元“明治”。
在此之前,“唐風”壓倒“和風”。日本一直孺子般貪婪地吮吸著西邊大陸的文化精髓。
明治維新之后,“和風”壓倒“唐風”。逐漸健碩起來的日本,不再需要母乳的滋養;而在中國,日本文化漸漸流行。毋庸多言,人們口頭和書面頻繁出現的現代高級詞匯往往來自日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文明”、“社會主義”……
“哈日先驅”變身“反清義士”
明治天皇登基后,從《詩經·大雅·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摘出“維新”二字,開始逐步實踐自己的強國理想。通過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日本國力迅速增長,一躍而成足以和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大國。此后,日本先后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
而在隔海的對岸,甲午慘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讓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從“洋務自強”的美夢中驚醒了,他們痛定思痛、立志變革。在看到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巨大進步后,疾呼在中國也推行變法運動。其中呼聲最高者,莫過于康有為,他在《日本政變考》中陳述“日本地勢近我,政俗同我,成速最速,條理尤詳,取而用之,尤易措手”。此時,中國呈現出第一次“哈日”的高潮。
這次高潮深刻地體現在赴日留學生的數量上。19世紀末,中國留日學生也不過一二百人,到1906年,在日的中國留學生數量持續井噴,超過12000人,在這批留學生中,包括中國近代史的一眾名人孫中山、魯迅、周恩來、郭沫若、王國維、秋瑾、陳獨秀、田漢、周作人、蔣介石、廖仲愷等。
在日的留學生們如饑似渴地學習日本的先進資本主義文化知識。課余,他們還創辦各類刊物,如《清議報》、《國民報》、《浙江潮》、(《江蘇》等,以期將日本的先進思想和文化介紹回國,啟發民智。創立譯書團體也是這些留學生熱衷的活動。
此時的哈日之風,對于促進中國現代化,改善風氣,宣傳自由、民主思想,自然功不可沒,更直接影響了中國近代的政治進程。康有為變法失敗后,匆匆逃往日本,魯迅在仙臺看到國人麻木的神情后,終究棄醫從文,女俠秋瑾甚至脫去旗袍馬褂,改著一身和服,腰佩倭刀,宣揚“反清”大義。這批留日學生的身上深深地烙上了“革命”二字,哈日派搖身一變成了革命派。
直到1915年,“二十一條”的提出,激起了中國上下一心的反日浪潮。這股反日熱也是由接受了新文化的留日學生首先發起。在中國各地大規模的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貨運動中,這場波瀾壯闊的哈日運動走向了尾聲。
“芭蕾外交”始破冰
20世紀中國的命運一波三折,中國人對日本的態度也經歷了大起大落、大愛大恨。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無疑給中國人帶來了最沉重的傷痛。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與日本的交往也幾乎完全停止。芭蕾舞開啟了中日兩國間的破冰之旅。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團第一次將中國的《白毛女》搬上日本的芭蕾舞臺,贏得各方好評。自此之后的50多年里,松山芭蕾舞團頻頻來華公演,受到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開啟了中日關系的“芭蕾外交”。
轉機發生在中美建交的1972年。那年秋天,周恩來總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在北京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兩國最終實現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兩國又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這份條約開啟了中日關系發展的新階段,從此,中日關系進入“蜜月期”,這個一衣帶水的東方鄰國,再次成為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樣板。
“友好之船”就是這一時期的特定產物。日本兵庫縣知事板井時忠最早提出這一創意,便帶領數百名日本青年乘船來中國港口訪問。后來發展成中日雙方友好交流的一種固定模式,史稱“友好之船”。
在神戶市市長宮崎辰雄和周恩來總理的提議下,大規模的中日“友好城市”工程拉開了序幕。天津與神戶,西安與京都、奈良,上海與橫濱、大阪有幸成為中日間的第一批友好城市。
日星橫掃影視圈
日本電影就在這個時候,悄悄地走進了中國。在那個剛剛解禁的年代,中國人早已厭倦了“橫眉冷對千夫指”的革命樣板戲,日本電影恰似從太平洋吹來了一陣清涼怡人的東瀛海風,血淚淋漓的情感故事打動了無數中國人。(《追捕》中高倉健的硬漢形象和中野良子的飄飄長發,《絕唱》中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的金童玉女組合以及《生死戀》中網球場上栗原小卷青春跳躍的背影,都成了一時的風尚。
火爆場景由此拉開。1979年,在《追捕》中扮演女一號的中野良子應邀訪華,中野下榻飯店中的工作人員一聽說“真由美”要來,都湊在一起為她表演舞蹈、彈奏樂器;大街上,到處都是中國影迷,揮舞彩旗,熱情呼喚著:“真由美!真由美!”
電視機的逐漸普及,讓日本電視劇也著實火了一把。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主演的《血疑》哭倒了半個中國,而荒木由美子帶來的《排球女將》在中國女排“五連冠”之際適時播放,引起一時轟動。1999年,日本學者原由美子和鹽田雄夫做過一項抽樣調查,在中國大陸有75%的人看過《血疑》,72.6%的人看過《阿信》、57.2%的人看過《排球女將》。
日本影視明星還塑造了一代中國人的時尚觀。在上海,愛美的姑娘們紛紛模仿《追捕》中的真由美,留起了飄逸的長發,有的店鋪甚至直接改名“真由美理發店”。山口百惠在(《血疑》中青春女大學生的穿著打扮,也成為很多中國女生一時追逐的時尚。
到90年代后,日本影視劇在華逐漸低迷,但成人電影(AV)卻在民間異軍突起。飯島愛、蒼井空先后贏得大量人氣。
質量“杠杠”的日本家電
日資家電是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家電軍團。在早期,中國內地的電視、報紙上鋪天蓋地都是東芝和松下的廣告,一時間,“Toshiba Toshiba”和“松下電器Panasonic”的廣告語成了人們耳熟能詳的段子。緊隨其后,三洋、夏普、日立、索尼等品牌的產品紛紛大舉進入中國。1978年中日貿易額為48.2億美元,1981年超過100億美元,到1991年達到228.29億美元。僅三洋一例,當年在日本國內曾是瀕臨倒閉的企業,后來向中國大陸大量銷售產品,漸漸地獲得了國人的認可,購買量迅猛增長,硬是被哈日族們救活了。endprint
到8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的家電廠商開始將銷售重心由產品市場轉移到生產設備和技術的出口上。單單一家松下,就在中國實施了180多個技術轉讓和成套設備提供,四川長虹電視和無錫小天鵝洗衣機就得益于松下的技術轉讓。
日本動漫:70后、80后的私房菜
“越過遼闊天空,啦啦啦飛向遙遠群星,來吧!阿童木,愛科學的好少年……”1979年底,日本動畫片《鐵臂阿童木》在中央電視臺開播。這個誕生于核時代,卻又英勇、無私、心中充滿友愛的機器人,立馬成為中國孩子們心中的偶像。
緊接著,《花仙子》、《聰明的一休》、(《圣斗士星矢》、(《龍珠》、《阿拉蕾》等日本動畫片大舉入華,每天下午5點之后,就在各大電視臺上輪番上演。國產的、日本的、美國的、歐洲的,在那個群雄逐鹿的時代,一枝獨秀的一定是日本動畫片。曾有機構做過調查“中國青少年喜愛的動漫作品”中,喜歡日本動漫的占60%,遠高于喜愛中國動漫11%的比例。
2006年,國家廣電總局一道令下,全國各級電視臺所有頻道在每天17時到20時的黃金時間內,均不得播出境外動畫片和介紹境外動畫片的資訊節目或展示境外動畫片的欄目。風靡中國熒屏的20多年的日本動畫自此被大舉清掃出門,國產動畫《喜羊羊與灰太狼》開始火熱,成為“零零后”孩子們的新玩伴。
日本動畫被趕出電視屏幕后,開始先后轉戰盜版VCD和電腦網絡領域。進入21世紀,互聯網和家用電腦的普及,讓看日本動漫變得易如反掌。已經20多歲的80后動漫迷們,自發組成各類團體,組建各類影視翻譯論壇,免費翻譯、校對、壓制、發布最新的日本漫畫。日本剛剛播出的動漫,往往在幾個小時之后,就可以在中國實現同步上映。《火影忍者》、《海賊王》、《名偵探柯南》、《夏日友人帳》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
對于看著日本動漫長大的80后來說,小小熒屏永遠滿足不了他們的欲望。COSPLAY和龐大的日漫周邊產品由此興起。除了實實在在的產業,日本動漫對于當代漢語的影響更不容小覷。調查資料表明,1998年中國學習日語的總人數為24.5萬,到2009年,增長到了82.7萬。日語則通過日漫在年輕的口頭快速傳播。“控”、“宅”、“蘿莉”、“給力”等詞語先后進入年輕人的口語中。
精致典雅的日式生活
用四個字概括日本人的生活氣質,“精致典雅”足矣。在這樣一個人多地少、資源匱乏的島國,日本人自古就形成了物盡其用的生活習慣,即使再狹小局促的空間,都能充分利用,并點綴得錯落有致。這樣的民族性格,造就了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上的作風,自然是頗為講究細節。
哈日派們崇尚日式的生活,自然免不了“小清新”的吃喝。對于習慣了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人,在舌齒間感受細膩爽滑的日料,已成為一種高規格的享受。生魚片得叫做“刺身”,海帶得叫做“昆布”、鮭魚得叫“三文魚”、豆沙糖叫做“羊羹”。在食材上,日本料理擅長呈現“初物”的原汁原味,因而生鮮美食自然成為哈日食客們的首選。
在這樣一個處處被詩化成藝術品的國度,飲茶自然也不是一件小事。中國傳統茶道古已失傳,哈日族們斷然不能接受現代的禮法。好在“禮失求諸野”,“和靜清寂”的精神在日本茶道中得以發揚光大,并永續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哈日族還“哈”回了失傳已久的抹茶。現在的中國,抹茶已大舉進攻食品產業,成為新的口味選擇。
哈日反日與知日
“哈日反日,不如知日”是蘇靜的話,他是(《知日》出版人兼總經理。作為力圖呈現一個鮮活、真實的日本,并呼吁當代青年理性思考、認識日本的Mook(以書代刊的出版物),《知日》的理念在其宣傳語中體現得很明朗——“專為兼具新知探索和思考力的華文年輕一代服務,提供最有創意、最具價值感的文化閱讀”。
思考與閱讀都是一種力量。弗洛伊德就相信,無論兩人之間存在何種親密關系,其中都包含著拒絕、積淀著仇恨。這種感覺被長期壓抑,一旦時機合宜,便會井噴出來。在中日關系上,弗洛伊德的論述相當恰當。這是一種鍍了不死之身的、被壓抑著的仇恨,在經歷了建國后的各類運動和七八十年代的蜜月期,仇恨仍然存在。而靖國神社與釣魚島就成了這種仇恨爆發的導火索。
日本領導人怎么敢悍然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參拜靖國神社?中國一些地方打砸日本汽車、焚燒日本廠商的“仇日”行為后,一個新的概念呼之欲出——“知日”。
“知日”并非簡單地知道日本、了解日本,而是通過全面、詳細、深刻的洞察,形成對日本的客觀、理性的認識。早在1928年,戴季陶在《日本論》的開篇中就指出了當時國人對于日本的兩種不正確態度,一是“實力主義”,一是“自大思想”——“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后,要切切實實地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功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曉得他的現在是從哪里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拿句舊話來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無論是怎樣反對他攻擊他,總而言之,非曉得他不可。”
戴季陶曾說:“日本把中國放在手術臺上、顯微鏡下觀察了幾千次”,而一百年來,中國對日本的反向了解卻始終難望其項背。
(摘自《天下傳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