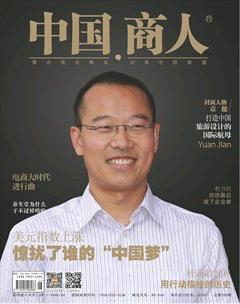企業(yè)需求錯位引發(fā)逆向淘汰
許一力
每斤1.6元,這不是超市里白菜的最新標價,而是上半年我國鋼鐵的價格,這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都是非常少見的。究竟是什么讓中國的鋼鐵業(yè)一步步走向了目前的狀態(tài)?
這讓我想起了今年1-7月,我國粗鋼產(chǎn)量同比增長2.7%,增速較去年同期已經(jīng)是下降了4.4個百分點,意味著產(chǎn)能淘汰開始起到作用。但與此同時,產(chǎn)量的增長卻沒有完全止步。前7個月我國4.8億噸的粗鋼產(chǎn)量,仍然還是占據(jù)了全球總量的半壁江山,比例超過50%。
一邊是產(chǎn)能過剩引發(fā)的價格暴跌,另一方面則是絕對量仍然在不斷擴張的現(xiàn)狀,這兩個大相徑庭的數(shù)據(jù)之間暴露的,正是鋼鐵企業(yè)需求和“控制人”需求的錯位。
企業(yè)的最上層控制人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在鋼鐵為代表的多個行業(yè)里,地方政府的需求,或者說地方政府官員的需求,與企業(yè)是脫節(jié)的。
現(xiàn)代企業(yè)的需求無非是盈利,但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企業(yè)是否盈利并非其官員考量的第一標準。官員考核看什么?看GDP,而GDP對應在類似的企業(yè)上,實際上就是產(chǎn)能。
因此,我們看到最近幾年,地方鋼企扛著巨大的虧損,賣得越賤越擴張,越擴張鋼價就越賤。為什么最近幾年節(jié)能減排、產(chǎn)能淘汰推進緩慢,就是源于此。地方政府監(jiān)管不力,導致了大量零環(huán)保成本或者低環(huán)保成本的企業(yè),在利潤上壓制環(huán)保設備做得很好的鋼企。
目前國內(nèi)環(huán)保較好的企業(yè)每噸鋼材成本在120-150元,而基本沒做環(huán)保的鋼企,噸鋼環(huán)保成本則維持在30元左右。再加上地方政府的監(jiān)管不力甚至人為的逆向淘汰,造成了環(huán)保達標企業(yè)干不過不達標企業(yè),按規(guī)定繳納員工福利的企業(yè)抗不過“奴工”企業(yè)。于是,環(huán)境越來越差,專業(yè)人員越來越少,價格戰(zhàn)成為惟一的出路。
說逆向淘汰并不夸張。河北作為我國第一大鋼鐵省份,在國家出臺產(chǎn)能淘汰政策之后,每年都出現(xiàn)瞞報粗鋼產(chǎn)量的現(xiàn)象。前年,這一數(shù)字達到5000萬噸。為什么要這么做?一方面是保留產(chǎn)能,對應的實際上就是地方官員的GDP考核;而另一方面,瞞報產(chǎn)量實際上可以有效壓縮環(huán)保成本。
可笑的是,中國類似的事情并不僅僅局限于鋼鐵業(yè)。
2001年,我國電解鋁產(chǎn)量世界第一,到了2009年,國務院頒布《有色金屬產(chǎn)業(yè)調(diào)整和振興規(guī)劃》,當時明確指出,三年內(nèi)不新建、不擴建。結果如何?2003年的五百多萬噸產(chǎn)能到2007年硬是翻倍到一千兩百多萬噸,2009年政府宣布不再核準新建、改擴建電解鋁項目后,當年電解鋁產(chǎn)能仍然出現(xiàn)25%以上的增長,到2010年底產(chǎn)能達到了2300萬噸,2011年突破2500萬噸。23個在2009年下馬的項目全部違規(guī)上馬。這背后體現(xiàn)的就是地方政府考核標準和社會以及企業(yè)需求的嚴重脫節(jié)。
地方官員只看GDP,企業(yè)生死不入我法眼。同樣的,社會經(jīng)濟所考慮的成本因素,同樣不在考慮范圍之內(nèi)。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主導下的經(jīng)濟模式,有了諸多賠本賺吆喝而且吆喝得越來越響的違背經(jīng)濟學常理的現(xiàn)象。
這種模式下,我們勢必要進入低價、低質(zhì)的惡性競爭狀態(tài)。就像PPI的連續(xù)回落,好幾年一直是負值,為什么?好事的人以為這是中國要進入通縮了,而實際上, PPI也就是工業(yè)品出廠價格的回落,單純的是因為中國地方政府主導下的畸形工業(yè)品模式:原本在虧損的過程中,就需要減產(chǎn),以此來保證價格,但是因為GDP考核之下的規(guī)模需求,鋼企在價格下跌的同時,繼續(xù)不斷擴張產(chǎn)能。最終,在看得見的手過度干預下,市場主導供需的作用越來越弱。PPI的回落,顯示的就是這種模式下,市場因素力不從心的現(xiàn)狀。
想要救中國的制造業(yè)和重工業(yè),并非幾個紅頭文件就可行,這其中首先需要的是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打破政府公司化的現(xiàn)狀,讓政府之手退出市場,抑制GDP考核模式下,地方政府對于產(chǎn)業(yè)的非市場化干涉。
鋼企如此,其他企業(yè)亦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