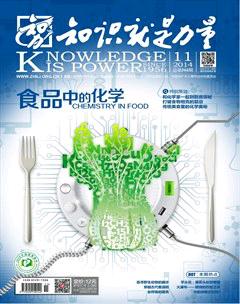浣熊火箭:“生物朋克”的影子 苗若玖
苗若玖

今年10月熱映的科幻電影《銀河護衛(wèi)隊》里,外表超萌舉止暴力的宇宙賞金獵人浣熊火箭,與植物形態(tài)的智慧生命樹人格魯特這對主仆,與男女主角星爵奎爾和女殺手卡魔拉一樣引人注目。當浣熊火箭在城市廣場使出種種奇特的武器,試圖捕捉奎爾賺取賞金的時候,相信不少觀眾都會忍不住琢磨一個問題:這個小東西到底是什么?
按照《銀河護衛(wèi)隊》的官方設定,浣熊火箭是一次基因實驗的產物。作為一種混合了人與浣熊基因的智慧生物,它擁有與普通浣熊一樣靈敏的感知能力,而且接受了武術和射擊等方面的強化訓練。這個耐人尋味的角色,代表著科幻作品中一個頗為獨特的門類—“生物朋克”。
“古”已有之的“生物朋克”
早在現代意義上的科幻小說萌芽的19世紀,“運用現代科技創(chuàng)造新物種,或者把寵物或野生動物改造成智慧生物”的構思,便與星際旅行、地底探險、史前生物和時間旅行等創(chuàng)意一道,成為一種科幻的“母題”或者說“戲核”。
在整個19世紀,醫(yī)學界對人體結構的了解不斷深入,再加上麻醉術和微生物學的發(fā)展,使外科手術的死亡率顯著降低,也讓一些人對外科手術在未來的發(fā)展?jié)M懷暢想。
1896年,英國科幻作家H·G·威爾斯出版了科幻小說《莫洛博士島》,反映了外科手術發(fā)展帶給當時人們的幻想之一,那就是賦予動物以智慧,從而讓它們成為更好的人類伴侶和仆役。但在這部作品中,威爾斯最終為這種想法潑了一盆冷水:再高超的技術,也終究不能壓制自然界千萬年的演化史賦予動物的獸性。一旦動物的野性本能沖破技術設下的禁制,災難便會立刻來臨。
“朋克”科幻的“千手觀音”
20世紀80年代初,由于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發(fā)展,科幻小說中興起了“賽博朋克”流派。通常以電腦網絡或信息技術為主題,反映數碼化為人類社會蒙上的躁動與灰暗色彩。這一類科幻作品的成功,也使諸多名為“××朋克”的科幻類型陸續(xù)誕生,表現某一類技術畸形發(fā)展可能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劇烈的、甚至含有陰暗面的改變。或者說,當人類的心智發(fā)展落后于技術的時候,技術進步就不一定帶來繁榮和富裕,也可能會帶來更多的殘酷和負能量。
在“千手觀音”式的“朋克”科幻作品中,最為人們熟悉的或許是“蒸汽朋克”,也就是假設蒸汽機技術畸形發(fā)展,乃至讓人類進入信息時代的科幻作品。而“生物朋克”作品的背景,往往設定在近未來世界,展示生命科學的發(fā)展帶給人類社會的改變。在這一類作品里,與人類共存的是一些經過基因改造的物種,或者純粹的人造生物,甚至是由它們構成的全新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而它們與人的互動,也是作品的主要看點。
警示世界“可能的樣子”
如今,“生物朋克”已經成為科幻作品中的一種常見題材,而且涌現出諸多膾炙人口的佳作。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的《魔鬼積木》,就虛構了美國軍隊進行的基因混合實驗:通過混合人與動物的基因,美軍得到了身心素質出眾的“超級戰(zhàn)士”,但也在探索技術的過程中,制造了不少半人半獸的“怪胎”。后來,出于保密的需要,美軍決定銷毀所有的“中間成果”,但負責實驗的黑人科學家奧拉博士反對這種做法,并將技術成果帶回自己的祖國繼續(xù)研究,最終培育出了擁有翅膀的“飛人”戰(zhàn)士保家衛(wèi)國。
事實上,《魔鬼積木》已經提出了一個相當尖銳的問題:人為制造的全新物種,或者經過基因改造的人類,應當如何與既有的人類社會共存。而不久前曾引起轟動的一部“生物朋克”力作,美國科幻作家保羅·巴奇加盧皮的《發(fā)條女孩》,則把這個問題向前推進了一步。在這部作品里,經過基因改造的生物已經極大的改變了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面貌,“生物黑客”制造著更為猛烈的病蟲害,不斷沖擊一些科技實力較弱的亞洲國家的農業(yè)。這種科技背景,與全球變暖和化石能源枯竭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就構造出一幅充滿了紛爭和壓迫,而且看起來近在眼前的未來圖景。
“生物朋克”勾勒出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的樣子,并以此向人們的心靈提問:我們的心智,是否足以駕馭最先進的科技成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們便如同偶然得到了火種的猴子,也許能幸運地吃到幾頓熱餐,但最終的結果將是燒掉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