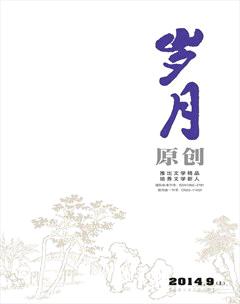賈平凹訪談
人物介紹:賈平凹,原名賈平娃,出生于陜西省丹鳳縣棣花鎮,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現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委會委員,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西安市人大常委,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文學院院長,《美文》雜志主編,當代著名作家。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賈平凹文集》(21卷),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商州》《浮躁》《廢都》《白夜》《秦腔》《古爐》《帶燈》等,小說《臘月·正月》獲中國作協第3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滿月》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浮躁》獲1987年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蘭西共和國文學藝術榮譽獎,《廢都》獲1997年法國費米娜文學獎,《秦腔》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帶燈》獲2014年第三屆《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作品《我不是個好兒子》《月跡》《落葉》入選中學教材,是我國當代文壇屈指可數的最具叛逆性和創造性的文學奇才,被譽為“鬼才”,也是當代中國可以進入世界文學史冊的為數不多的著名文學家之一。
訪談時間:2014年6月5日(第三屆《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頒獎,浙江省慈溪市)
文學無法逃避現實
峻毅:祝賀平凹老師榮獲《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為您這樣的大家做訪談,我有點緊張,老實說這不是我的長項,真的。
賈平凹:沒事,沒事(mò sì)!隨便說說,沒啥緊張的。(他悠悠地點煙,緩緩地呷茶,滿口濃重的陜西鄉音。)
峻毅:我不只一遍讀《帶燈》,與你獲茅盾文學獎的《秦腔》相比,我更喜歡《帶燈》,因為主人公帶燈是位女性,且非常內秀。盡管她看上去也被繁瑣粗糙的基層生活打磨得開始變形,但她的知性美對我依然有種魔力,就像所有成功的小說主人公一樣。所以,首先想請平凹老師談談對“帶燈”這個人物的設計思路和借此想要完成的創作目的。
賈平凹:那就先說說為啥叫帶燈吧。帶燈,原叫螢火蟲的螢,螢火蟲是比較浮躁的一種蟲子,后來改名帶燈,寓意是自帶的一盞燈,發出的光雖然是很微弱很微弱,卻是發自內心。
帶燈大專畢業進了鎮政府,從女大學生成了一個鄉鎮干部,鎮政府綜治辦主任,能有這樣一份工作,在西北農村已經很不錯很不錯了。但她每天要接觸方方面面的人,上面是領導,下面是各種各樣的群眾,夾在中間,面對那些形形色色的上訪者,她想堅持自己的一些東西,也堅持了自己的一些東西,過得挺不容易的。
《帶燈》展示的,實際上就是眼下中國農村最現實、或者說是最接近現實的,也是一般作家很不愿意弄的。距現實太近,很不好寫,弄不好就沒文學性了。所以,我在后記里談到寫這個東西,要把它寫得有文學性,就得學學兩漢的東西。因為我們絕大部分人學的是明清的東西,是從學明清小品這一類東西過來的,這些東西大多是你們江浙一帶的人寫的,文筆很婉約,很柔美。有好多文體性的作家,基本吸收了明清東西。但隨著年齡增長,我覺得,尤其作為一個西北人吧,老吸收明清的東西不能滿足,老覺得明清的東西不夠。兩漢吧,在我的理解里,它就是很簡約,也很硬朗,語氣里沒有太多虛的東西,還有些在史的味道。寫當下現實生活,是有好多可以吸收的東西的。但同時也要特別注意,弄不好,就成了調查報告啥的了。
我寫的帶燈吧,這個帶燈不是帶燈一個人,是一個集體,是通過帶燈這個人寫帶燈集體;是按目前中國農村鄉鎮狀況來寫的。《帶燈》里邊的那些上訪情節,也不是在寫上訪故事,與劉震云那個上訪故事《我是潘金蓮》完全不一樣,是通過這些上訪人上訪事寫鄉政府的基本工作生活。“維穩”是鎮政府日常工作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鎮綜治辦的基本工作,是帶燈的工作,但最后她自己也上訪了。元薛兩家那場血腥械斗發生后,鎮政府把她做替罪羊,降級撤職處理以后,她也很壓抑,開始有病了,后來就是夜游癥,整夜跑。竹子就為她抱不平,找了王后生,因為工作多少年一直和那個老上訪戶作斗爭,最后還是叫那伙兒往上給報了。那些上訪情節,那些上訪人物,都是反映當下中國農村的現狀。如果只寫帶燈這樣一個人,我寫帶燈的故事就可以了,簡單多了,不用涉及那么多,鋪展得這樣大。比如寫老街改造,寫建大廠,寫辦沙廠爭地盤血腥械斗……
帶燈是有些悲劇色彩的,家庭生活不順,工作環境也很混亂,但并不悲觀,現實就是這樣。帶燈就像一個螢火蟲,自身帶燈在跑。小說結尾,莽山上出現了螢火蟲陣,成千成萬的、十幾萬幾十萬的螢火蟲聚在一起,場面壯觀,令人震撼。
文學無法逃避現實,要面對這個社會的丑陋和黑暗,但是更要去尋找光明。
峻毅:帶燈從改名到靠抽煙和傾訴來排泄內心的煩惱和落寞,再到身上長了虱子,與起初那個連名字都文縐縐的女子大不一樣了。她剛到鎮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可是要鎮干部搞個人衛生滅虱子的,后來卻在各村結交了一群老伙計,和村民們相處得如魚得水,這多少有點像前蘇聯老電影《鄉村女教師》中那個瓦爾瓦拉,甚至比她更“土”;按您對人物的設計,這是帶燈這個人物(這里指她的原型)本來的性格使然呢,還是想揭示基層生活對這個人物的磨礪?
賈平凹:你這里的下鄉,與她(帶燈)那個下鄉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西北農村吧,那里農村還是很閉塞很落后的(咳嗽)。
峻毅:是,我在讀《帶燈》時也感覺到了,您作品里的農村離我們江南農村很遙遠,那種貧困和落后我很陌生,好像在二三十年以前似的。
賈平凹:對!對!對的!就是這樣的。剛才已經說過,我寫的這個帶燈吧,她不是一個人,是一個集體,是工作生活在當今中國西北農村的鄉鎮女干部群體的代表,就想把她寫得有血有肉,有靈氣,有一種神兒的。在現實生活里邊,帶燈的原型很聰明,很靈秀,很能干,很會處理問題。她整天接觸的都是社會最基層那些亂七八糟的煩瑣事情,不是處理上訪的事情,就是處理民間各種糾紛的問題,都是那些不能不面對又特別煩人特別混亂的事,當時她的現實生活就是這樣子。
她不知從哪兒弄了我的手機號,給我發短信,我以為她是一位業余作者,給她復了信,她卻接二連三地又給我發信,要是平常,我簡直要煩死了。她是個鄉政府干部,具體在綜治辦工作,并不是文學青年,工作又繁忙又潑煩(陜西方言:“煩惱、煩心、煩躁”的意思),但她寫的短信文筆很好,很有文學感覺,就想去看看她和生她養她的地方。我真去找她了;她是個滔滔不絕的傾訴者,我是個忠實的傾聽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樣的生活和工作。她又領著我走村串寨,去給那特困戶辦低保,也去堵截和訓斥上訪的人,帶我跑了她包的那個村里,跑到她的那些老伙計那里,就是和她聯系的那些山里邊的人家里。不用說,她的干群關系很好,在村鎮里很有威信,很受歡迎,這是她樂于助人、正直善良的品性使然。endprint
不一樣的思維,組織語言也不一樣
峻毅:“帶燈”讓我想起了前蘇聯作家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里的主人公葛利高里。您和肖洛霍夫不是同一時代的作家,創作背景相距很遙遠,但作品的反映鏈很相似,都是以主人公個人生活和感情波動相結合的藝術手法來刻畫人物性格的,與您以往的小說不同是同時存在兩條敘述鏈;一條是以故事情節推進,另一條卻是以帶燈內心情感和精神寄托的展露推進——“給元天亮的信”,這弄得不好很容易破壞作品的整體風格,閱讀時會給讀者一種支離破碎的感覺。您如何敢于這樣以虛托實,并且完成了對帶燈性格的文學審美?這樣做是展現帶燈內心世界所必須的嗎?
賈平凹:對!對的!一個方面是大量地寫現實生活、日常生活,現實生活、日常生活是寫實情的;另一個方面是要把精髓寫出來,把精神的東西寫出來。給元天亮的信,就是當作一種精神來寫的。那些信吧,有虛幻的東西,有愛情的東西,有傾訴的東西,里邊有各方面的因素吧,帶燈全靠這些想象的東西、向往的東西當作精神支撐,基本寄托在元天亮這個人身上,在很骯臟、很混亂、很庸俗、很惡劣的現實生活中,她要是沒有那些東西支持她就沒法活下去,就靠對元天亮的傾訴作為精神依托活著。這樣,就把那些很現實的、很麻煩的、很焦躁的、很讓人無奈的東西提升起來了。把精神的東西和現實的東西弄到一塊來寫一個人,不把這個人陷到具體的事情中去,就能把這個人刻畫好,基本上就這樣來處理的。再從小說的結構來講,寫實情的東西太多太滿,閱讀起來特別費勁,加些詩情的東西,加些明亮的東西,能增加讀者的閱讀快感嘛!“給元天亮的信”這條敘述,主要是起到這個作用。故事發展過程中,如果去掉那些信,故事也是完整的,那純粹只是個故事而已了。
峻毅:您是作家,帶燈的原型給您發過很多信,給您提供創作素材,而您在構建元天亮這個角色時,除給他一個省委副秘書長身份,還給了他一個作家身份,這容易讓讀者想象您與那個“元天亮”之間會不會有什么關聯,在“給元天亮的信”里,有帶燈的原型給您的信嗎?
賈平凹:嘿嘿(笑)!
這啥,這樣理解吧,帶燈她畢竟是個大學生,是個喜歡閱讀的文藝女青年,小知識分子,心很高,有小資情調,充滿理想,也充滿浪漫想象,但工作生活偏偏整天和這些煩心的人煩心的事打交道,把她煩死了,她太需要有適合的可以傾訴的對象。
元天亮這個人物設計成雙重身份,是有很多鋪墊的。
這里只說作家身份吧。元天亮是作家,帶燈愛讀書,讀到元天亮的書,她發現了元天亮,找到可以傾訴的對象,把他當作可以信任的精神依托,才會呈展內心情感世界。在給元天亮的信里,盡是唯美的,或者是滿天空跑的那種思維的,用很優美很睿智的話,抒發小資情調。要我說帶燈原型給我的那些短信吧,后來在寫作中,有一部分內容就處理成“給元天亮的信”了。
峻毅:是的,所有“給元天亮的信”語言和意境都相當美,每一封信都可以說是散文佳作,但明顯與我以往讀過的您的散文語言不同,您的散文語言很獨特。記得您的散文《紅狐》,也是以書信形式向Z傾訴內心,但與“給元天亮的信”的文字相比語言大不一樣了。請您談談您對散文和其他文體中“散文化”語言的區別。
賈平凹:那是!散文吧,是作者在訴說。你還記得《紅狐》啊?很早的,八十年代寫的。給元天亮的信,是小說人物帶燈在訴說,是現代有些小資情調的知識女性寫的信,是她向元天亮的傾訴。不同角色,不一樣的思維,組織語言也不一樣。所處背景不同,傾訴的表達的對象不同,情感就不一樣,語境語氣肯定不一樣的。
一個作家有他作家的使命
峻毅:《文學報》有一篇《〈帶燈〉:一部沒有骨頭的小說》的評論,不知道您讀過沒有,我個人并不認同文中的質疑,但他提到了“這個時代需要什么樣的小說”,對于這類問題您是怎么看的?
賈平凹:是個批評文章吧。那些東西啊,口說可以,要給人力量啊,給人精神啊!但具體要看怎么個認識,表達正能量有各種辦法。讀小說,怎么讀,怎么理解都可以,但小說就是小說,不是故事,不能把什么都寫了。你把事情都說完了,讓讀者怎么弄?要給讀者留有空間嘛。那個人肯定沒有好好讀,寫批評沒說到點子上,不在點子上,基本上對我沒留下什么印象。批評吧,就怕人家一說就能說到你的痛處,你就能馬上感覺到了。對《帶燈》的評論很多,正面評論寫得比較多有陳曉明,寫了一萬多字,人家是從評論家的角度評的,不是說僅僅是評價我的。上海還有個評論家陳思和,上海復旦大學的挺有名,尤其在南方是個領頭的。他在讀《帶燈》后寫了幾篇文章,我覺得寫得特別有意思,寫得很好。這個人很厲害,學生的學生的學生都博導了,其實他和我的年齡是一樣的。
峻毅:我剛開始讀《帶燈》時,也覺得很散,靜下心來讀,漸漸地被那些鎮政府的人、村干部、上訪者、群眾、瘋子甚至狗的生活情節拽著拉著推著去感受人性善惡、情感微妙、世態多變、生活無奈,讀著讀著,好像置身在生活里邊了。
賈平凹:它是一種散文體的寫法,把它散開了,不是講故事;只講故事,再完整也沒法表達中國基層社會的東西。
峻毅:在您的很多作品里都能讀到禪意,讀到佛說俗世之味,感覺您是信佛的,而且很虔誠。佛學對您的創作有什么影響嗎?您最喜歡讀的是哪部佛經?您在《帶燈》里隱喻處處可見,在后記里還寫到了從廟里請回來一尊地藏王菩薩,給它鮮花供水焚香,這隱喻了什么?
賈平凹:對!小時候受家庭的影響,受社會的影響吧,陜西農村信佛的多,道觀也很多,哪里都有,潛移默化受影響。要我說佛學對我的創作有什么影響,那倒沒有,也說不上特別喜歡哪部佛經,我沒有特別研究佛經,只是了解了解。
《帶燈》這本書里面有很多隱喻,隱喻了很多臆想。地藏王菩薩說,地獄不空,誓不為佛。地藏王菩薩現在還在做菩薩,還沒有達到最高的佛,還有很多鬼災吧,隱喻了在基層社會工作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多少年以來,我看到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期取得了進步,同時也看到轉型時期社會有了更多問題。面對這些問題,雖然沒有能力改變很多東西,但起碼我也很擔憂,也想把自己體會到的一些東西表達出來。作家在研究社會,但不決定政策,起不了更大作用,只有寫文章。有的時候,很多事情是無解的,尤其是在目前社會大轉型時期,只能慢慢來改變。endprint
峻毅:我讀過您的長篇小說,幾乎會是寫農村題材的。我在讀《帶燈》的時候就在想,您已經寫了那么多農村題材的,尤其是后幾部,都很成功,《秦腔》獲了中國長篇小說最高獎茅盾文學獎,《古爐》好評連連,是什么促使您又投入同是農村題材的《帶燈》創作?您有沒有考慮過,萬一《帶燈》不能有所突破怎么辦?
賈平凹:一個作家,他要寫他比較熟悉的那個方面;一個作家有他作家的使命,哪一類的作家就應該完成哪一類作家的使命。你大可以寫歷史啊,寫未來啊,寫當下啊。我是一個寫當下的,自己出自農村,對農村的情況比較熟悉,相對容易把它表達實了,寫實了。農村吧,就是農民,農民的骨子里就是農耕為民。作為我來說,自己熟悉這方面,關注這方面,就把它寫了。或許過些年,農村就又不一樣了,起碼自己有義務把我知道的這些寫出來。
創作素材方面的來源就是這樣:我和帶燈的原型成了朋友。她每天都給我發信,有時一天發兩次,都是幾百字或上千字的,信息內容有好多講她具體的工作,說人生、說理想、說愛情、說書法、說其追求和向往、啥歡樂的、悲傷的、憤怒的、苦悶的似乎什么都不避諱,還定期給我寄東西,五味子果、鮮茵陳、核桃、蜂蜜,還寄鄉政府下發給村寨的文件啥的,我了解了這個鄉鎮的日常工作都弄啥,每天弄些啥。她確實是位真正熱心扶弱幫貧、從沒為自己思謀升官發財的基層鄉鎮干部,還能堅持自己的一些東西,真是挺不容易的。
寫完《古爐》以后吧,我又跑了很多地方,想把現在的農村了解了,并沒有帶著寫什么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最基層、最落后的,把最好的與最落后的都看看,數次在陜南、甘肅、河南、湖北一些縣、鎮、村游歷,看到農村落后貧困的現狀,越是最基層、最落后的地方,社會矛盾危機越突出,那些事情特別令人痛心,很有感觸。當我在電視里看西安天氣預報時,不知不覺地也關心了那個深山地區的天氣預報,就是從那時起,我就坐不住了,沖動地了寫《帶燈》。
我在后記里說了,在寫《帶燈》過程中,也是我整理自己的過程。通過寫《帶燈》我進一步了解中國農村,尤其深入了鄉鎮政府,知道那里的生存狀態和生存者的精神狀態,我的心情不好。社會基層有太多的問題,就如書中的帶燈所說,它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這些問題不是各級組織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決,可有些能解決了,有些無法解決,有些無法解決了就學貓刨土掩屎,或者見怪不怪,熟視無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閉上了什么都沒有發生吧,結果一邊解決一邊又大量積壓,體制的問題,道德的問題,法制的問題,信仰的問題,政治生態問題和環境生態問題,一顆麻疹出來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來,搔破了全成了麻子。認識了帶燈,了解了帶燈,帶燈給了我太多的興奮和喜悅,也給了我太多的悲憤和憂傷,而我所要寫的《帶燈》都一定是文學的,這就使我在動筆之前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書出來以后,很多時候不屬于作家了,更多的是屬于社會了,由社會來評判了。
峻毅:讀到“……或許或許,我突然想,我的命運就是佛桌邊燃燒的紅蠟,火焰向上,淚流向下”時,我的閱讀經驗告訴我,這是對帶燈做了概述,之前所有的故事只是鋪墊。帶燈瘋了,小說到這里結尾也是很完整的。您為什么又寫了狗毛的變化,寫了瘋子咬狗,寫了帶燈學瘋子動作,寫螢火蟲群……明知這些都是虛的,讀著卻依然充滿神秘感。
賈平凹:對!這是文學性的需要,文學作品吧,有的時候就需要有神秘性,這就是我要的效果。
采訪結束時,我向平凹老師提了個額外的要求:請您為我們慈溪的作者們寫句話吧!他欣然同意,揮灑命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