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是“御用翻譯嗎”?
錢之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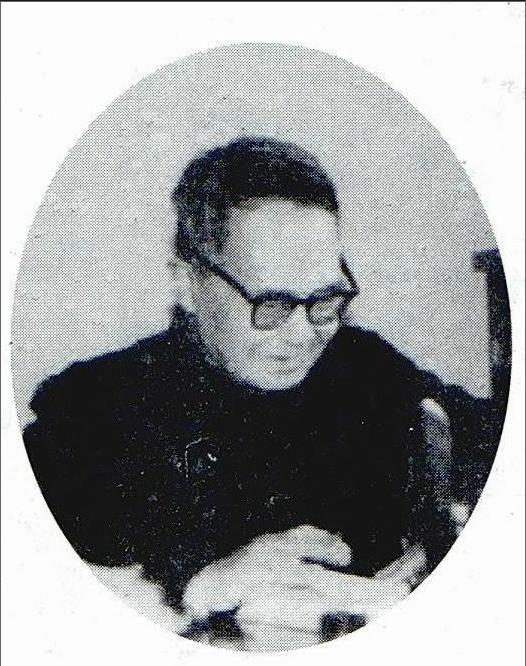
國內一些論壇討論錢鐘書的翻譯水平時,有人以“御用翻譯”來稱呼1949年后的錢鐘書,言語中不無譏諷。一位以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聞名于世的學者、作家,為何被冠以“御用翻譯”的頭銜呢?
翻譯《毛澤東選集》
1949年8月26日,錢鐘書從上海回到闊別十余年的清華園。但他在清華只工作了一年,1950年仲夏,清華同學喬冠華來找他翻譯《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把他借調到“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工作。據說,當初喬冠華是找費孝通參加翻譯的,而費表示,自己的英譯水平恐不足勝任,于是推薦錢鐘書擔當此事。
錢鐘書并非中共黨員,為何會被調去擔任這一具有政治意義的工作呢?除了自身專業技術水平高,喬冠華的舉薦自然是關鍵。對錢鐘書一直比較關心的另一位清華同學胡喬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新聞總署署長,同時也是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成員,他的作用也不能忽略。此外,正如著名詩人何其芳所言,中央對錢是經過嚴格審查的,黨對他是了解的,信任的。
《毛選》英譯委員會辦公處設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開始參加英文翻譯的有金岳霖、錢鐘書、鄭儒箴、王佐良等人,還有史沫特萊、愛潑斯坦、愛德勒等一批外國專家,一年以后,只剩下錢鐘書和幾位年輕助手。錢鐘書平時就住在城里,一般周末才回校住,并繼續指導他門下的研究生。
從1950年7月至1954年2月,錢鐘書一直從事《毛選》(前三卷)的英譯工作,“始終地和全面地參加了初版稿和舊改稿的工作”,這項工作正如他自己說的——“并不是那么好做的”。《毛選》的英文翻譯與中文原文的編輯在同步進行,原文在編定過程中不斷修改,英譯也不得不跟著變動,往往是一篇已經定下來的譯稿反復地改個不停。另外,也存在認識不一致的情況,夫人楊絳說:“好在鐘書最順從,否了就改,他從無主見,完全被動,只好比作一架工具。不過,他工作還是很認真的。”
錢鐘書做事認真,辦事效率卻不低,別人干一天的活他半天就能干完,甚至兩個小時就干完;省下來的時間就偷空看書。他甚至認為《毛選》英譯委員會的最大好處是“人少、會少”,搞運動也聲勢不大,有時間讀書。
在這期間,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錢鐘書雖還在城內,但已被調入文學研究所外文組。文研所的編制、工資屬新北大,工作則由中宣部直接領導(1956年正式劃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1954年2月,翻譯《毛選》工作告一段落,錢鐘書回到文研所工作。1957年“反右”時,在所內的“拔白旗”運動中,他本人并沒有被打成右派。1960年夏,《毛選》第四卷英譯工作開始,1961年春完成。錢鐘書沒有參加第四卷的翻譯工作,但做過“潤色”。
《毛選》的英譯分為翻譯和定稿兩個階段。1958年初到1963年,錢鐘書成為英譯《毛選》定稿組成員。據說,這也是胡喬木推薦的。
翻譯毛澤東詩詞
1963年英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結束,1964年,錢鐘書又成為“翻譯毛澤東詩詞五人小組”成員,任務是修訂或重譯已經翻譯的全部毛澤東詩詞,最后出單行本。
這“五人”的另外四人是袁水拍、喬冠華、葉君健和趙樸初。袁水拍當時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詩刊》雜志編委,葉君健是英法文版《中國文學》主編。在“五人小組”成立前,外文出版社已出版了由安德魯·博伊德等譯的《毛主席詩詞》英譯本,但譯文并不令人滿意,袁水拍還特別撰文批評。葉君健是《毛主席詩詞》英譯本的組織者和參加者,他向有關領導部門建議成立一個毛詩英譯定稿小組,由袁水拍任組長,喬冠華、錢鐘書、葉君健作為成員。錢鐘書與葉君健主要做翻譯和譯文的潤色工作,袁水拍與喬冠華主要負責對原作的解釋和對譯文的斟酌。有關部門同意了這項建議。為了全面修訂舊譯并翻譯新發表的詩作,后來小組又增加了趙樸初作為成員,并請英文專家蘇爾·艾德勒協助譯文的潤色工作。工作地點在中宣部三樓會議室。
“文革”開始后,翻譯毛澤東詩詞的工作暫時停止,錢鐘書此時才真正嘗到運動之苦。1966年8月,他被群眾“揪出來”成了“牛鬼蛇神”,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1969年5月,一對革命青年夫婦搬進他們家合住,不久,錢鐘書被下放干校。1972年3月從干校回來后,他與合住者發生爭執,被迫“逃離”原房子而暫住北師大,大病一場,差點送命。最后,他遷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七號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翻譯毛澤東詩詞的后期工作就是在這間屋里完成的。
1974年11月,江青要求“五人小組”繼續翻譯毛澤東詩詞的工作。也有文章說,是周恩來調錢鐘書參加毛澤東詩詞英譯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怕他被下放干校折磨而死。翻譯期間,由于錢鐘書年初才大病,他要求“足不出戶”。翻譯小組成員不得不每天來陋室工作。袁水拍幾次想改善工作環境,換個大點的房子,江青也同意他們搬到釣魚臺工作,但錢鐘書不愿意。
1976年“五一”節,《毛澤東詩詞》英譯定稿本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這個英譯本,后來成了接著出版的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語等幾種譯本的藍本。“革命者”不敢對錢鐘書“太革命”
1949年后,錢鐘書從擔任《毛選》翻譯工作開始,就一直從事和政治關系密切的譯事,他本人因此確實受到了一些積極影響和不一般的待遇。1957年的反右風潮中,錢鐘書在1956年“黑材料”的風波下,居然有驚無險,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的“毛選翻譯”、“外事翻譯”等身份。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因為這些特殊的經歷,不僅使錢鐘書避過了風頭,還享受到了同時代很多知識分子無法享受的待遇。1958年知識分子下鄉改造,錢鐘書于12月初下放昌黎,到次年的1月底就回來。從1958年初到1963年,他是英譯《毛選》定稿組成員。此時“三年饑荒”已開始,錢鐘書回來后,房子比以前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但并不擔心吃飯問題。楊絳說,因為一同為英譯《毛選》定稿組的有外國人,他們還“常和洋人同吃高級飯。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應。我們還經常吃館子。我們生活很優裕”。1962年8月14日,他們又遷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個房間,還有一間廚房、一個衛生間、一個陽臺,他們新添了家具,住得很“寬舒”。“文革”中錢鐘書雖也遭到不幸,但萬幸的是沒有被抄家,還可以繼續寫日記,做筆記,并完整保存下來。“文革”結束初始,他就拿出了巨著《管錐編》,這是其他知識分子做不到的。錢鐘書是“御用翻譯”嗎?endprint
1998年12月,錢鐘書去世。他在1949年后所做的這些翻譯工作,被官方再次提及并放大。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的李鐵映在《人民日報》撰文懷念錢鐘書。
“文革”結束,錢鐘書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還連任了幾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委,也都說明官方對他這位非黨學者的另眼相待。那么,錢鐘書是否真如有些人評價的,是“御用翻譯”呢?實事求是地說,這個稱呼并不恰當。
其實,這些翻譯工作只是集體工作,是政治任務,并非他的本職工作。如果說錢鐘書翻譯《毛選》與毛澤東詩詞“是最重要的學術活動”,這種認識與實際情況是存在偏差的。楊絳一再強調:“這么多年的翻譯工作,都是在中央領導下的集體工作。集體很小,定稿組只二三人,翻譯詩詞組只五人。”
在英譯《毛選》小組中,錢鐘書一直是以英語專家的身份被肯定的。楊絳也說:“鐘書從未把翻譯毛選和以上這類任務當成自己的本職工作。在他自己填寫的個人履歷中,從未寫入以上經歷。”“都是有關部門向鐘書所在單位借調的。”沒有當成本職工作是真,但錢鐘書在填寫履歷時,并不回避這段經歷。如1955年,錢在填寫中國作協會員表時,在“近三年來有何新作”欄寫道:“自1950年7月起至去年2月皆全部從事《毛澤東選集》英譯工作(現在尚部分從事此項工作),故無暇顧及其他活動。”
像這樣錢鐘書在簡歷中寫譯《毛選》的事,在以后幾乎沒再見到。他并不希望自己因此而被記住,而是盡量淡化此事,更不要說以此為炫耀的資本,向組織提要求。翻譯毛澤東詩詞期間,很多人寫“鑒賞”類文章,連毛澤東自己都認為“注家蜂起,全是好心”。有錢鐘書的傳記作者稱,錢鐘書是很有條件寫的人,但在阿諛奉承之風盛行之時,錢鐘書一反時流,不著時文,不發時論,仍默守學術獨立的立場。“文革”后,錢鐘書對這些經歷更有意輕描淡寫。1979年,他隨中國社科院代表團到美國訪問,知名學者余英時向他求證是否如外界所說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錢鐘書說,這完全是誤會,大陸曾有一個英譯毛澤東選集委員會,他是顧問之一,其實是掛名的,偶爾提供一點意見,如此而已。自己沒有做過毛澤東的秘書,也沒譯過毛澤東的“哲學”著作。
確實,在當時的情況下,沒人敢懈怠黨和政府交給的任務,正當盛年的錢鐘書難以說“不”。錢鐘書在解放后非常“識時務”,少說話,多做事,在得到信任做翻譯工作期間,更是謹言慎行,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1953年,翻譯《毛選》期間,友人鄭朝宗到其工作處看望他,他出示了一首新作,其中有一聯云:“疲馬漫勞追十駕,沉舟猶恐觸千帆。”焦慮不安的心情躍然紙上。
在1949年后所有的這些翻譯工作中,最重要的要數最先翻譯的《毛選》了。那么,錢鐘書對此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從現有的回憶文字看,他對這項工作還是非常認真的,但他的內心卻另有一番想法。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著名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為參加這次會議,參加者特別是與知識分子有關的部門,都為會議準備了詳細的材料,當時高等教育部在一份關于北京大學的調查報告中,對當時北大的知識分子進行了政治分類。報告中提到當時北大的一部分“反動教授”,特別點到了錢鐘書,說他在解放后一貫地散布反蘇、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動言論,1952年,錢鐘書在《毛選》英譯委員會時,有人建議他把《毛選》拿回家去翻譯,他說“這樣骯臟的東西拿回家去,把空氣都搞臟了”,污蔑《毛選》文字不通。這份報告,直到“文革”開始的1966年,別人貼錢鐘書的大字報時他才得知。錢在大字報旁貼出了申辯的小字報,說自己一向敬仰毛主席,正因如此,他才認真負責地主持審定英文版的《毛澤東選集》。他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對毛主席著作有絲毫不敬之處。舉報的內容雖查無實據,但當時軍宣隊認為“告發”的事情情節嚴重,料必事出有因,還是命錢鐘書寫了一份自我檢討。這份報告中關于錢鐘書的言論是非常嚴重的,如果中央后來沒有核實清楚的話,他在1957年是無論如何逃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命運的。但,錢鐘書如果沒有這個意思,難道是空穴來風?
余英時說錢鐘書“是一個純凈的讀書人,不但半點也沒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興,而且避之唯恐不及”。以此話為底線,我們就不該太苛求于錢鐘書。在一個政治和社會生活極不正常的年代里,對更多的諸如錢鐘書一類的知識分子來說,應該報之以同情的理解,他們的損失與傷痛并不比其他人少。
(摘自《編譯參考》2013年第27期)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