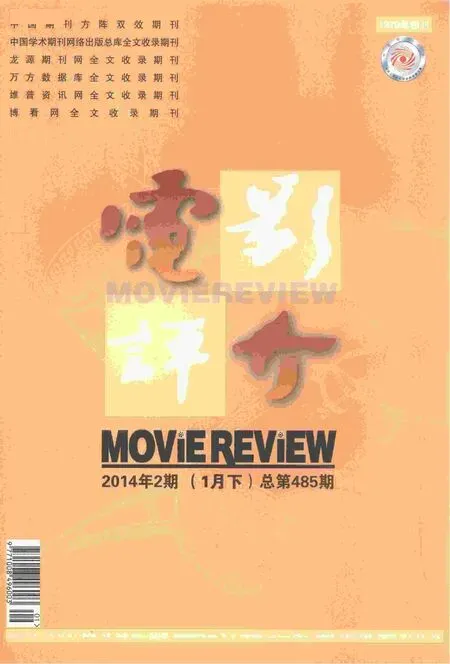中國電影史學的歷史——在西方歷史學與西方電影史學的視野下
□文/黃 鵬,中國傳媒大學博士后
一、反思中國電影史研究
我國對中國電影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20 年代,兩部最初的著作分別是程樹仁的《中華影業年鑒》(1927 年1 月)、徐恥痕的《中國影戲大觀》(1927 年4 月)。而以“電影史”為明確提法的著作則為谷劍塵著《中國電影發達史》(載《中國電影年鑒》,中國教育電影協會1934 年出版)和鄭君里著《現代中國電影史略》(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 年版)這兩部史述專著。這些早期的電影史研究實踐為后來的中國電影史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史料,但尚未在學術價值的高度上對后世的研究產生引領式的影響,歷史研究的總體水平仍然較低。在世界范圍內,這種情況也很類似。在1937 年,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喬治·薩杜爾向法國著名電影評論家亨利·朗格盧瓦透露打算寫一本電影史時,“電影史基本上是一種從作者直接經驗和親身經歷的知識產生出來的見解與判斷……所有當時已經出版的或者正在編纂的電影史,都是對多年來觀摩的影片和經歷過的爭論與看法的一個鳥瞰,或者更明確點說,是一個批判性的概述,旨在使人對電影藝術及其進步有所認識。一句話,電影史在1937 年只不過是電影評論的一個派生物而已。”[1]相較電影批評和電影理論,作為電影誕生地的法國,電影史研究的起點同樣是既晚且低。然而,僅僅十年之后,喬治·薩杜爾的宏著《電影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就先后橫空出世,將電影史研究推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其影響至今仍然輻射電影史學界。而中國電影史研究在20 世紀40 年代結束時也沒有出現可以與其比肩的研究著述。我們不禁思考,如此短的時間,西方電影史研究者何以出現如此大的變化?
關于電影史的研究,我國電影史學家李少白后來曾經指出,電影歷史學應“作為電影學和歷史學的一個交叉學科。”[2]歷史學家汪朝光也提出“未來研究中應將電影史視為一般史學研究之一部分,進一步拓寬研究視野,擴大研究選題”。作者又進一步指出,“研究民國時期的電影發展史”應當“為電影史和民國史研究所應為。”[3]我想,至此我們應該可以找到答案了。事實上,西方電影史研究產生如此之大的變化,一個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電影歷史研究者在研究進程中自覺地與西方歷史學形成了聯動,在西方歷史學的視野下進行電影專史的研究。然而,盡管電影史學界和歷史學界都已意識到電影史與一般歷史的關聯,但時至今日,“中國電影史研究還沒有跟當前的史學研究建立起應有的關聯性,也正因為如此,迄今為止的中國電影研究者大多無視,也無力觀照歷史研究的狀況及史學范式的轉換”。“努力倡導在史學視野里進行中國電影史研究”[4],將中國電影史研究納入一般歷史研究的視野,無論是對中國電影史研究格局的開拓、學術品性的提升還是對一般歷史研究本身的完善都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如果說,早期的中國和外國電影史研究工作者一開始尚未找尋到電影史研究的方法的話,那么在較短的時間內,西方電影史研究者就通過對自身歷史研究傳統的梳理,迅速找到了參照系,從而將電影歷史的研究大大的往前推進了。
二、西方歷史學:沿革
西方古典史學傳統源自公元前5 世紀的古希臘,從被尊為“歷史之父”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約前484 年- 前425 年)和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前460 年至前455 年間—約前400 年)開始,經歷近千年的綿延,于公元5 世紀前后經歷了從傳統的人本主義向基督教神學史觀的轉折。作為神學的附庸,史學的獨立發展態勢被阻斷。14 世紀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后,在人文主義的大背景下,人作為歷史發展核心地位的古典史學傳統得以延續,人文主義史學得以發展。19 至20 世紀,在自然科學勃興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在“求真”的渴望下,歷史學得以高度專業化,以“近代史學之父”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歷史研究者主張通過史料考證如實地再現歷史的史學觀念,確立了傳統史學的研究領域與研究方法,建立并影響了近代歷史學研究的范式①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代表“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和技術手段等總體,并為其所擁護而共同遵守的準則。與進程。
20 世紀上半葉,蘭克的傳統史學仍然具有活力。但其他史學思想也已逐漸開始對歷史研究展開影響。如果說1917 年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在除前蘇聯的史學界以外獲得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的話,“1929 年的大蕭條結束了無視或蔑視地排斥馬克思主義的時期。”“馬克思的歷史判斷的正確性這時看來得到了證實。”“1930 年以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廣泛擴展,即使那些否定馬克思主義歷史解釋的歷史學家們(他們在蘇聯以外仍占大多數),也不得不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重新考慮自己的觀點。”[5]隨著二戰結束,特別是20 世紀50年代以來,源自20 世紀20 年代末的法國年鑒學派逐漸成為新史學的代表。以呂西安·費弗爾、馬克·布洛赫、布羅代爾為代表的年鑒學派,在史學觀念上注重分析,突出歷史學家作為認識主體在歷史研究的中心地位,與傳統史學家通過考證描繪來還原歷史有很大不同。在研究范圍上,新史學將傳統史學的研究范圍從政治史擴充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勞工史、婦女史、黑人史等成為歷史研究的新的領域。”[6]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學注重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借鑒引入其它學科的新技術和新方法。這種對現代科技和情報檢索處理的依賴甚至改變了歷史研究的工作形式,“正如布羅代爾所說的,歷史學家越來越像實驗人員那樣‘依靠設備’進行工作,從事歷史研究的機構與組織也隨之增加,今天歷史學家所面臨的史料太宏富了,學科門類又多繁復,那種靠歷史學家個體單槍匹馬地去操作,拒絕使用任何集體組織形式,已無力適應現時代史學變化的這種新情況。”[7]
歷史的車輪繼續向前,就在新史學依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科學化的進程上大步邁進時,具有自省性發展特性的西方史學又發現了新史學傾力研究大跨度靜止不變的歷史,過分追求深層分析而忽略人對歷史能動作用的弊端。從20 世紀70 年代末開始,新敘事史開始出現。與以蘭克為代表的“傳統的敘事式歷史學相比,這種歷史學往往包含有更為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往事”[8],其所涵蓋的內容要比傳統敘事史豐富復雜得多。還是在70 年代,作為時代的文化思潮,后現代主義的影響波及了人類文明的各個方面,它同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一道,影響了史學研究的格局。微觀史、新文化史等開始出現,與后現代主義、傳統史學、法國年鑒學派、新敘事史一道構成今天西方史學豐富立體的多層次多向度的研究格局。
三、喬治·薩杜爾:背景與標尺
一個富有科學精神的研究工作者無疑會受到當時科學思想體系的影響,并有意識地根據自己的工作范疇有選擇性地接受這種影響。法國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的杰出就在于他接受當時各種史學觀念的影響,積極地使電影史的研究置于一般歷史學的研究背景下,其研究實踐和理論表述終將電影史納入了一般史學的范疇。因為他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朗格盧瓦評價道:“正如電影有戈達爾之前的電影與戈達爾之后的電影一樣,電影史也有薩杜爾之前的電影史與薩杜爾之后的電影史。”[9]
薩杜爾在《緒論:電影史的資料、方法與問題》中,他詳細討論了電影史學家所需要據有的三類資料:“一、書面的原始資料和參考資料,包括手抄稿或印件;二、口述的原始資料;三、膠片上的原始資料,亦即影片本身。”[10]薩杜爾詳細討論了每種史料的考證原則和方法,其對于史料完全占有與充分考證判斷的治史理念體現出其對于蘭克以來的傳統史學理念的認同。其細致與繁復的考證頗似部分歷史學界傳統史學的懷疑者所詬病的“枯燥無味的職業作風”,“缺乏洞察力”,“迂腐窮酸地追逐細枝末節”[11]等。比如,薩杜爾通過研究膠片的化學結構來確定拷貝的制作日期和產地。指出“對它作國際性的系統研究,無疑可以確定那些缺乏說明材料的拷貝的產地和日期。賽璐珞片基的組成同乳劑的成分一樣,在各個國家、各個年份是有極大變化的。根據已經鑒定其制作日期的影片,我們就可以制定各國的影片年表,這些年表向電影史家提供的資料,其準確性甚至比放射探測對史前歷史學家和地質學家提供的數據更大。”[12]又如確定膠片制作的時間和產地還“可以根據拷貝兩邊孔眼的數目、形狀以及在片底時常印上的膠片工廠的商標來研究,就像通過水印來辨認古代的紙張一樣。”[13]其科學實證研究的態度表露無遺。作者還不厭其煩地通過對盧米埃爾那部經典的《工廠大門》的拍攝時間考證表明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對薩杜爾而言,“對書寫材料、印刷品、手稿以及口述資料的評論,判斷它們的作證價值,長期以來已成為史學家們研究的對象……在這方面,無論是電影史或是一般歷史,都運用同樣的方法。”[14]在薩杜爾看來,電影史的研究除了有些特定的研究對象外,在史觀與研究方法上與其它歷史研究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從而自覺地將電影史研究置于歷史研究的背景與框架下。對于薩杜爾的電影史研究,朗格盧瓦非常清晰地明白薩杜爾的著作與其它“電影史”的不同,在他看來,電影史研究要“穿過那些使他看不清的陰影和虛假的前景去追蹤過去,以便顯示過去的面貌……而要深入了解過去,只有大量搜集資料,使用一些必不可少的鑒別、判斷與考證的原則,才能辦到。”[15]
正是這種將電影史研究置于歷史研究大背景之下的治史理念與實踐,使薩杜爾在歷史觀與電影史觀、電影觀的和諧統一上走得更遠。薩杜爾撰述電影史的上世紀前半葉至中葉是歷史學破立變革的時期,蘭克傳統史學在對薩杜爾電影史觀產生重大影響的同時,作為法國共產黨黨員,又是在有長期革命傳統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氛圍的法國,上世紀30 年代開始愈發產生廣泛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也對他的電影觀、電影史觀產生了影響。他明確表示:“把電影作為一種藝術來研究它的歷史,如果不涉及它的企業方面,那是不可能的,而這種企業又是與整個社會、社會的經濟和技術狀況分不開的。因此,我們的計劃是把電影作為一種受企業、經濟、社會和技術嚴格制約著的藝術來加以研究的。”[16]在薩杜爾的歷史研究實踐中努力地將這樣原有的電影綜合觀、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對社會和經濟的關注及對作為整體的工業關系的關注融合到一起,進一步完善了其獨有的電影史學觀。對此,同代的電影史學家和理論家讓·米特里評價道:“在我草擬的第一部電影史中,我完全忽略了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研究。正是喬治·薩杜爾打開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必須把電影放在與其相關的各種因素中加以考察。”[17]米特里的肯定是建立在電影理論界對電影綜合觀這一認識的基礎之上的。對大多數電影領域的研究者而言,非常清楚電影作為工業和藝術這一復合形態的身份。那么比起馬克思主義史學關注的其它領域,其對于電影的研究就先天地具有與馬克思主義融合的特征。這是薩杜爾實現的將原有的,主要是蘭克歷史觀的電影史觀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融合,也是電影史研究與整個西方歷史學背景的第一次融合。
如果說這一次的融合實現得還比較迅速與便捷的話,原因恐怕在于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學的影響除了研究領域從政治拓展到經濟與社會,研究開始注重整體觀,注重“非精英人物”的人民大眾和注重階級結構的概念以外,在觀念本質上依然要求還原歷史的真實,而在研究方法上尚未與傳統史學有激烈的沖突。薩杜爾正好又從電影這一本身有著高度綜合性的即是工業又是技術與藝術的領域切入,在電影史研究的實踐中流暢漂亮地實現了蘭克傳統史學研究方法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學觀的結合。這次結合既然如此完美,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說薩杜爾采用了一種包容了蘭克史學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在擴大了的傳統史學研究對象范疇內從經濟與社會、技術與工業的整體角度對電影歷史進行了蘭克式的考證研究呢?我們認為,這樣理解是不完整的,至少沒有概括清楚薩杜爾史學研究范式的完整向度和層面。
20 世紀30 年代以來,除了馬克思主義,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也在日益擴大,面對年鑒學派要求歷史研究領域從政治史擴展到廣泛的人類生活領域的要求,電影史的研究從對象上一開始就應對了這一革新的呼聲。但是,對于年鑒學派在歷史觀念上要變敘事史為分析史,突出歷史研究者在歷史研究中的主體地位這一大破大立的舉動,薩杜爾顯然無法做出更大的讓步。雖然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指南,沒有對歷史學研究的技術路徑進行太具體的制約,但是在史學觀念上強調一種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總體性要求,而且認為“歷史并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8]這種“人有目的的追求”和“揭示總體規律”的闡述實際上表明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是敘事式的,這就無法與年鑒學派“人”的缺席的忽略敘事突出分析的史觀相融合。盡管如此,薩杜爾還是在自己的范式中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工作形態上肯定吸收了年鑒學派的不少做法。例如他把世界電影史的范圍拓展到了除歐洲以外的其他亞非拉和第三世界國家。在電影史這個研究對象上打破了傳統西方歷史敘事中的“歐洲中心”窠臼,而這個研究對象是從蘭克傳統史學的政治史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經濟、社會史可能都還不夠廣泛的。他還強調電影史研究過程中盡量利用現代化技術,如“照相復印”等并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樣的中間機構進行國際間的廣泛協作。薩杜爾于1967 年逝世,他未能看到后來的年鑒學派歷史學家們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間更廣泛的跨學科研究以及充分利用電子計算機進行資料搜集與整理的研究方法。在可能的范圍內,他的電影史研究工作體現了從傳統史學到新史學的整個向度,為電影史學建立了影響深遠的研究范式,影響了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電影史研究工作者。中國1963 年出版的《中國電影發展史》就是這種影響的直接與明顯的體現。
[1]喬治·薩杜爾.世界電影史[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2.
[2]李少白.中國電影史研究方法[J].文藝研究,1990(4):55.
[3][4]李道新.中國電影史研究專題Ⅱ[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33,232.
[5](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楊豫,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5-26.
[6][7][8]張廣智.歷史:文化中的文化[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342,343,345.
[9][10][12][13][14][15][16]喬治·薩杜爾.世界電影史[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3-4,5,19,11,3,32.
[11]F.M.波威克.現代歷史學家和歷史學研究[M].//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楊豫,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8.
[17]汪流.中外影視大辭典[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59.
[1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