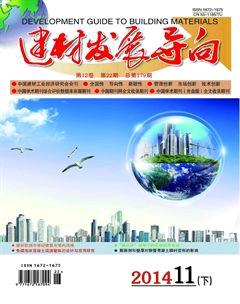走向山水城市
司國輝+李悅來
摘 要:山水,與其說是一種傳統的文化,不如說是一種情感。東方人對于世界的理解,對于自我的認知,都建立在這種人與自然特殊的情感之上。工業革命至今的歷史,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歷史,扶搖直上的鋼筋混凝土大廈成了贊美權利、資本,蔑視人性的紀念碑。未來五十年,當城市化告一段落,我們現在的建筑實踐、城市實踐,能給未來的城市文明留下更多的鋼筋混凝土殼子,而不是像北京四合院那樣的鳥語花香的院落。未來的社會發展將從對物質文明的追求轉向對自然文明的追求,這是人類在經歷了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的工業城市文明之后的回歸,自然和人將建立在平等和諧關系基礎之上。未來應該是將城市的密度與功能和山水意境結合起來,建造具有人文價值觀的城市,或者稱其為“山水城市”。
關鍵詞:山水城市;建筑;靈魂
現代都市建筑沒有靈魂。走過很多城市以后,城市像是超市里的貨架,上面擺放著建筑,雖然琳瑯滿目,卻也大同小異。或平淡或奇異的建筑像物品一樣被展示出來,并按照功能被分門別類地放好,等待被人買走。或許貨架上的商品略有不同,但是這個超市的貨架其實與另一個超市的貨架沒什么不一樣。貨架是一種目的性極強的使用設計。展示、可復制,一切都與銷售有關。現代主義城市的布局就像在搭建一個巨型貨架,用土地開發價值和使用效率來引導城市規劃。城市變得越來越功利化、商品化。以這種利益模式發展出來的城市,很難真正去考慮人的精神需求。但是快速化的城市浪潮使貨架城市變成最有效的推進模式。伴隨著資本的不斷涌入和消費的過剩,城市貨架變得擁堵不堪,這樣的城市模式就走到了盡頭,城市里的建筑也成為囚籠。城市和建筑的發展應該像生物體的新陳代謝一樣,是動態的。
美國建筑師文丘里提出過“向拉斯維加斯學習”的口號,再看今天的拉斯維加斯,除了游客外儼然是一座空城,孤魂野鬼般的繁華。如同當年代表了美國汽車工業繁華的底特律一樣,這些城市正因為靈魂缺位而日漸衰落,失業率增加、犯罪率攀升、人口外流。
紐約,這座最具代表性的現代大都市,的確是個特例。紐約的曼哈頓島始于一個烏托邦式的宏大造城理想,設計者把現代主義的思想推到極致,在如此高密度的現代大都市中,竟有一片占地340公頃的綠地——中央公園,它以極端方正的邊界把城市與自然分割的一清二楚,城市密度和綠地規模形成極大反差。即使是柯布的“光明城市”,在曼哈頓面前也遜色不少。紐約的城市規劃的極致也造就了這座城市獨特的氣質,居住在這里的人們以紐約人自居,享受著它的紛雜與生機。
住宅不是居住的機器。柯布西耶在他的《走向新建筑》里說過一句極具煽動性的話:“住宅是居住的機器”。在戰后住房緊張、能源短缺的一段時間里,這句話經受住了考驗。當人們的居住狀況已經危及到一個政權和社會穩定的時候,建筑思潮就不再是一個純粹建筑學范疇的問題了,而是更多地被當成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政治手段,住宅成為“居住的機器”是歷史的必然。
住宅緊張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現代城市仍然繼續充斥著大量的“居住機器”。我們應該意識到,機器是工業生產的產物,沒有任何機器是生產情感和思想的,它滿足的只是社會批量生產的需求。然而住宅首先應該把人當作主體,人的情感歸屬恰恰是住宅最應該考慮的問題。大城市的問題其實并不是摩天大樓本身,而是隱藏在那些建筑物背后的價值觀所導致的人性和精神的缺失。這是一個科技進步、物欲充裕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匱乏、情感麻木的世界。城市中的住宅不應該成為居住的機器。
回到山水之初。在中國古代的建造思想中,天地的秩序被視為最基本的法則,建筑和環境始終被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對自然的尊重和親近貫穿于大到城市小到住宅的各個尺度中。這種源于自然的設計思想不單純是形式上的模仿,更重要的是把從自然中獲得的身心體驗傳達給他人,因此有神似高于形似的說法。感受是超越語言的,感受即真實。
每個人心中都有山水,那是一種對自然的理解和記憶,對外部世界的情感體驗,而不是山、水、植被這些具體的自然物。
古代城市的建筑很多時候是由庭院組成的。庭院里,人和人在一起生活,人在這里感受自然、生命和四季的變化。庭院和公園、廣場不一樣,它與人們有著更為親密的關系,庭院通常是圍合或者半圍合的私密空間,尺度宜人。在城市里,庭院微觀而密集地散布在各個角落,建筑仿佛消失在這種自然的滲透之中。正如老舍寫到的,老北京的美在于建筑之間有空兒,在這些空兒里有樹有鳥,每個建筑倒不需要顯示自己。庭院是一種格局,它讓建筑消失,讓自然發生。馬巖松在北京和羅馬老城中心的兩座建筑就運用了“漂浮的庭院”的概念。就是把庭院疊起來,形成立體的空兒,將這些庭院或者平臺錯落地堆砌成立體的“山”。這樣的微山水以一種新的方式繼承傳統居住空間的一些特征,逐漸生長,相互匹配,滲透到城市的各個角落。
北京和羅馬是兩座典型的東方和西方城市,一個是由木結構的四合院組成,另一個是由石頭堆砌的大庭院組成;一個展現了小尺度細胞般的空間組織,另一個擁有紀念碑式的、永恒的街道立面。嘉德藝術中心位于老北京的核心,與紫禁城和中國美術館為鄰,同時被古老的四合院包圍。然而老北京的小尺度城市肌理正在遭受大尺度現代建筑的破壞,將這座新建筑碎片化也許是解決這一困境的基本辦法。它是一座由多層庭院空間堆棧而成的立體城市肌體,沒有清晰的幾何形狀和輪廓,但在各個方位和不同層高上,庭院、平臺和宜人的小尺度園林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系列漂浮狀的室內外空間。“空兒”成為了空間組織的核心。
在羅馬的設計是針對老城中心的一棟現代建筑的改造。它是一個功能復雜的多層街區院落建筑,里面包含著公寓、辦公空間和一座教堂。羅馬是一座永恒城市,看起來像一座博物館,這里的每一座建筑,即使是廢墟,都有著這座城市不可磨滅的靈魂。在羅馬,古典的街道是由代表不同時期風格的建筑立面所組成的,少數后來建造的建筑也用立面展示著它的時代特征;或者復制老建筑的立面,或者用現代的語言造成和古典建筑的反差。馬巖松打開了厚重的歷史外衣,只保留建筑的樓板和柱子,然后重新插入新的居住單元和空中的庭院。立面因此消失了,建筑和街道之間呈現出一個模糊的界面,人和自然在漂浮的花園中相遇。這座建筑表達的是現代人生活和自然之間的真實關系,這跟以往所有以立面為表達語言的建筑物都不同。通過打開,反而實現了一種消隱。這個建筑也圍合了一個內部的庭院,相對于外部臨街的開放和喧鬧,內部庭院則追求寧靜、私密的氣氛,竹林、水池和白色的混凝土鋪地也給內部庭院一種東方的意境。室內的景色與室外的庭院交融在一起,整個建筑猶如城市中一片漂浮的園林。
這是一種把現代城市生活與自然山水中的情感體驗相融合的實驗,讓建筑成為自然的延續,并喚起曾經寄托于古老的東方山水之間的情感。如果說古典城市是關于神的,現代城市是關于資本和權利的,那么未來的城市就是應該關于人的。
山水城市中的建筑是自然和人的情感聯系為核心的有機體。它們可以是山而非山,是水而非水,是云而非云;形式上不拘一格,精神上高度提煉。城市走向山水,是現代城市從物質走向精神的升華過程,是人性的回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