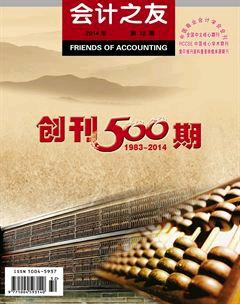公司特征對高管薪酬的影響
余海宗++王博++楊洋
【摘 要】 高管薪酬的制定不僅能夠激勵企業高管更好地為公司服務,還能成為向資本市場投資者傳遞財務信息透明度的一種手段。影響高管薪酬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自身特征、高管人力資本理論、資本市場與法律法規等方面。為更好地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從而提升公司業績,對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2009—2012年的財務數據進行線性回歸,通過公司自身特征對高管薪酬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為創業板監管制度的出臺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 高管薪酬; 經營業績; 公司治理結構; 創業板
中圖分類號:F272.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4)32-0077-04
一、引言
在華爾街金融風暴之后,人們對于高管薪酬的關注上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近年來,我國上市公司高管們持續進行著“收入冠軍”的競賽。對此,公眾不免質疑:高管薪酬究竟由哪些因素決定?高管薪酬作為一個復雜的治理概念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主要包括:公司特征、高管自身特征、資本市場與法律法規等。為了研究公司的薪酬政策制定是否合理,本文擬研究高管薪酬受公司特征的影響是否顯著,即假定某管理人員自身條件與所處地區、市場一定,公司因素如何作用于其薪酬。所謂公司特征,即是指公司本身為了更好地經營與發展區別于其他公司的方面,主要包括:公司經營業績特征、公司發展規模特征、公司治理結構特征、公司所處行業特征、公司成長潛力特征等。
2009年10月30日,28家創業板公司在深交所掛牌上市。眾所周知,在創業板上市之前,33位高管為了獲取股票套利資金,竟主動放棄高額薪酬集體辭職,這一新聞使得人們將高管薪酬與創業板這一新興的市場聯系起來。如今,五年時間已然過去,創業板市場的泡沫漸漸退去,投資者與上市公司雙方都逐漸回歸理性,公司股價、業績等數據趨于平穩,這為創業板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研究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創業板多為高科技、高成長性的民營企業,將他們集中起來,單獨研究高管薪酬與經營業績的相關性,可以有效排除因公司行業不同、潛力不同、股權性質不同而產生的干擾。因此,本文將著重從公司業績、規模及治理三個特征出發對創業板高管薪酬的影響因素作出實證分析。
二、研究假設
(一)研究假設
1.公司規模與高管人員薪酬相關性
根據管理理論,公司規模越大,管理層級越多,高管人員需要控制的資源越多,經營的復雜多變要求管理者具有更高的管理技巧,并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去協調、優化資源配置。因此,根據人力資源成本理論,高管人員的薪酬待遇自然也應相應提高。另外,企業規模越大,其破產的風險越低,融資渠道更加多元化,薪酬支付能力也就越高。Rosen(1992)與Fleming(2002)等學者的大量研究也發現,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高管人員薪酬也會隨之增加。基于此,筆者提出本文第一個假設。
假設1:高管薪酬水平與企業規模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2.公司業績與高管人員薪酬相關性
根據代理理論,企業所有者委托專業的代理人員代其管理企業日常經營活動。但由于高管人員與股東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股東所掌控的信息少于管理者所了解的信息。作為委托人,股東雖然不能清楚地了解經營者的努力程度,但對于企業的績效是可以清楚看到的,他們可以根據企業的績效來衡量經營者的工作情況,給予相應的報酬。若經理的報酬由企業的經營業績來決定,高管人員勢必會努力提高企業經營業績以提高自身報酬。Hall和Liebman在1998年的研究也可以證實這一理論。基于此,筆者提出本文的第二個假設。
假設2:高管薪酬水平與企業經營業績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3.董事會人數、監事會人數與高管人員薪酬相關性
董事會或監事會成員越多,所掌握的專業技能越廣泛,管理能力越強,對待關鍵問題時決策更全面周到,不易受到經營者的蒙蔽,其控制經營者的能力提高,從而使得不利于高管的薪酬方案容易得到通過;并且,由于人員充足,董事會可以利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分別控制管理層,使得薪酬方案更加不利于高管。基于此,筆者提出第三個假設。
假設3:高管薪酬水平與董事會及監事會的人數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4.獨立董事占比與高管人員薪酬相關性
一些有社會聲譽或專業素養的人才成為獨立董事后,會因較為關注其個人的聲譽或職業操守而成為管理層的有效監督者,促進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方案向合理化的水平發展。因此,筆者提出第四個假設。
假設4:高管薪酬水平與獨立董事占比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5.股權集中度與高管人員薪酬相關性
在股權高度集中的狀態下,大股東既具有獲取信息和監督經理層的動力,又能夠通過在董事會派遣自己的代表對公司實施有效的管理。當公司相當數量的股份集中在少數大股東手中,且控制權帶來的收益足以覆蓋成本時,大股東有理由也有能力監督管理層。在股權高度集中的狀態下,股東對高管的監督更強,會限制高管薪酬的增長。于是,筆者提出最后一個假設。
假設5:高管薪酬水平與股權集中度負相關。
(二)變量選擇與模型設定
1.變量定義
相關回歸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2.模型形式
(三)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9—2012年的創業板上市公司年報數據作為樣本。剔除了被審計師出具非標準意見的上市公司;剔除了這四年間創業板高管人員發生非正常變動的企業;剔除了存在高管違規①記錄的上市公司。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部分缺失數據由金融界和鳳凰財經網站公司年度報告查得。具體的樣本量為:2009年58家公司,2010年186家公司,2011年178家公司,2012年258家公司。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其中,高管薪酬對數標準差為0.8872,說明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較大的差異,前三名高管年薪之和最高的達804萬元,而最少的前三名加起來只有16萬元,三人之和平均112萬元左右,每人平均高達40萬元,說明創業板高管薪酬水平總體較高。同時,公司規模標準差為0.6321,說明創業板公司規模相差較大,其中最大的資產總額為32億元人民幣,最小的僅有1億元左右,但總體來講,創業板上市公司規模偏小,這主要與其所處的高科技或服務類行業性質有關。公司董事會平均8.5人,與10人的國際慣例相近。其中獨立董事平均比例約為35.3%,即約三分之一的董事為獨立董事,說明大多數上市公司符合我國董事會成員中應當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獨立董事的規定。樣本中董事會成員最多18人,最少9人,在《公司法》規定5至19人的范圍內。第一大股東占比均值為34.76%,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股權相對集中,這也與公司規模普遍較小有關,其中,高管人員持股比例平均為26.21%,明顯高于其他板塊,這與上市前公司不斷推出股權認購計劃有關。公司平均每股收益0.74元,但波動較大,最高達2.78,最低只有0.033,但總體上講,業績水平較高。
(二)多元回歸
回歸結果見表3和表4。結果表明模型的擬合程度中等,可能是由于被解釋變量高管薪酬受到企業本身、管理人員自身以及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多方面的共同作用,甚至其中的很多變量難以量化或是難以獲取數據。因此,本文擬研究公司特征的相關指標對經理人薪酬的影響,不考慮高管人員自身因素。
四、研究結論和建議
(一)研究結論
由表3和表4可知,LnASSET系數均為正,與預期相一致,說明公司規模與高管薪酬正相關。并且,P值分別為0.0015與0.0002,均遠小于1%,說明公司規模對于高管薪酬的正相關關系在1%水平下顯著。公司規模越大,對管理人員的學歷、能力、精力要求越高,所產生的人力資源成本也就越大,自然會導致薪酬的上升。這與李增泉、魏剛等人的實證結論相一致,同時也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
上述兩表中,公司業績的衡量指標EPS系數均為正,與預期相一致,說明業績與薪酬兩者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而對應的P值分別為0.0473與0.0608,基本可以認為EPS與高管薪酬的正相關關系在5%水平下顯著。公司業績作為衡量高管人員代理績效的直接可觀測指標,與高管薪酬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薪酬政策能夠有效反映代理質量,較為合理。這與宋增基、張宗益以1997年12月30日之前上市的129家滬市A股的中國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相一致: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這也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設2。
值得注意的是,從表3中可以看到,BSIZE變量系數為正,與預期相反,說明董事會人數與高管薪酬之間正相關,并且,二者的相關性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正常情況下,二者應該是負相關關系,即董事會成員越多,對高管的監督越強,其薪酬會越低。但這里卻出現了異常,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會監督效率低下:隨著董事會規模的擴大,董事們對關鍵問題的討論參與程度受到限制,協調與溝通的成本增大,董事會控制管理層的能力下降,有利于高管的決策容易通過;并且,獨裁型的CEO得以利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手操縱和控制董事會,從而使得其薪酬方案有利于高管。另外,SUPERVISER變量系數為負,雖與預期符合,即監事會人數與高管薪酬之間負相關,但P值較大,即二者相關性不顯著,說明監事會監督效率較低,絕大多數公司的監事會無法掌控公司實權,其設立只是為了滿足證監會的基本要求,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花瓶”,對高管薪酬的影響不大。并且,由于大多數公司為節省費用,均直接以證監會規定的監事會下限3人為標準,導致各公司監事會規模相差不大,回歸結果不顯著。基于此,本文的假設3沒有得到驗證。
從表4可以看出,DRATIO變量系數為負,且P值為0.0009,說明獨立董事占比與高管薪酬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即獨立董事占比越高,高管薪酬越低。這說明在創業板市場,一向被認為形式化的獨立董事制度對高層管理人員是有一定的監督作用的,這也與創業板市場特點有關。創業板上市公司大多具有成長快但風險較高等特點,市場泡沫嚴重,股價容易被高估,因此擔任創業板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專業人士必須加大對管理層的監督力度以降低風險,從而保全自身的名譽。基于此,假設4得以驗證。
最后,上表中BIG1指標相關系數為負,與預期相符,說明股權集中度對高管薪酬有負向影響。第一大股東所占比例越高,股東對公司高層的監督作用越大,高管薪酬會略有下降。但該指標t值偏大,二者的負相關關系僅在10%水平下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當第一大股東占比過高時,第一大股東對董事會有絕對控制權,也許反而會為高管人員提供一份不匹配的高薪酬以令其作出有利于絕對控股股東利益的決策。這與La Porta.R.和Lopez-de-Silanes在1996年的研究成果相一致,同時也驗證了本文的假設5。
同時可以看到,對于本文出現的控制變量MSR,實證結果顯示高管持股比例與薪酬正相關,雖然相關系數的符號符合預期,但二者不顯著,說明關聯性不大。筆者認為,創業板高管持股比例雖然較高,但創業板高管們持有公司股權并非為了在董事會占領一席之地,從而擁有公司決策權與控制權。由于創業板股價的持續上漲,高管們更愿意利用手中的股權在資本市場套現,實現高額的資本利得。這種行為具有明顯的短期投機性質,對高管們爭取長期薪酬水平的提升幫助不大。由于這種創業板市場特有的不成熟性,也就促成了本文開始提到的創業板公司上市不久便有33位高管先后辭職的轟動事件。因此,創業板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對其薪酬影響不顯著。
(二)建議
本文對創業板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2年上市期間公司特征對高管薪酬的影響進行分析,發現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正相關,與公司規模正相關,與董事會人數正相關,與監事會人數負相關關系不顯著,與獨立董事占比負相關,與股權集中度負相關。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創業板上市公司應盡可能完善和落實高管持股期限政策,并加強對分期股票解禁的審核力度。股權激勵過大,管理人員只需坐等企業上市便可輕松獲取額外收益,從而導致管理人員缺乏提升企業業績的動力。基于此,筆者認為,證監會應當完善和落實高管持股期限政策,加強對分期股票解禁制度的審核力度,維護創業板管理層的相對穩定。在高管持股期限的確定上,應結合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成長周期,待公司日趨成熟后,逐步減少高管持股,避免長時間持股,保持股權的流通性,促進外部資金流入企業。另外,要加強分期解禁股票時的審核力度。當持股高管準備解禁股票套取現金時,可以通過離職審計等手段考核其任期內公司成長性、未來發展能力等長期指標,避免一些高管人員以損害公司長期發展能力為代價一味追求其任期內的短期盈利目標,待套現離職后留給股東與繼任者一個“千瘡百孔”的問題企業。
【參考文獻】
[1] Fleming G. Stellios G. CEO Remuneration, Managerial Agency and Boards of Directors in Australia[J].Accounting Research Journal, 2002,15(2):126-145.
[2] Hall B. J., Liebman J. B. Are CEOs Really Paid Like Bureaucrat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113(3):653-691.
[3] Rosen S. Contracts and the Market for Executives[J].Contractual Economics, Oxford: Blackwell,1992:181-211.
[4] 杜勝利,翟艷玲.總經理年度報酬決定因素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05(8):14-20.
[5] 杜興強,王麗華.高層管理當局薪酬與上市公司業績的相關性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07(1):58-63.
[6] 張必武,石金濤.董事會特征、高管薪酬與薪酬敏感性——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分析[J].管理科學,2005,18(4):32-39.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其中,高管薪酬對數標準差為0.8872,說明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較大的差異,前三名高管年薪之和最高的達804萬元,而最少的前三名加起來只有16萬元,三人之和平均112萬元左右,每人平均高達40萬元,說明創業板高管薪酬水平總體較高。同時,公司規模標準差為0.6321,說明創業板公司規模相差較大,其中最大的資產總額為32億元人民幣,最小的僅有1億元左右,但總體來講,創業板上市公司規模偏小,這主要與其所處的高科技或服務類行業性質有關。公司董事會平均8.5人,與10人的國際慣例相近。其中獨立董事平均比例約為35.3%,即約三分之一的董事為獨立董事,說明大多數上市公司符合我國董事會成員中應當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獨立董事的規定。樣本中董事會成員最多18人,最少9人,在《公司法》規定5至19人的范圍內。第一大股東占比均值為34.76%,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股權相對集中,這也與公司規模普遍較小有關,其中,高管人員持股比例平均為26.21%,明顯高于其他板塊,這與上市前公司不斷推出股權認購計劃有關。公司平均每股收益0.74元,但波動較大,最高達2.78,最低只有0.033,但總體上講,業績水平較高。
(二)多元回歸
回歸結果見表3和表4。結果表明模型的擬合程度中等,可能是由于被解釋變量高管薪酬受到企業本身、管理人員自身以及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多方面的共同作用,甚至其中的很多變量難以量化或是難以獲取數據。因此,本文擬研究公司特征的相關指標對經理人薪酬的影響,不考慮高管人員自身因素。
四、研究結論和建議
(一)研究結論
由表3和表4可知,LnASSET系數均為正,與預期相一致,說明公司規模與高管薪酬正相關。并且,P值分別為0.0015與0.0002,均遠小于1%,說明公司規模對于高管薪酬的正相關關系在1%水平下顯著。公司規模越大,對管理人員的學歷、能力、精力要求越高,所產生的人力資源成本也就越大,自然會導致薪酬的上升。這與李增泉、魏剛等人的實證結論相一致,同時也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
上述兩表中,公司業績的衡量指標EPS系數均為正,與預期相一致,說明業績與薪酬兩者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而對應的P值分別為0.0473與0.0608,基本可以認為EPS與高管薪酬的正相關關系在5%水平下顯著。公司業績作為衡量高管人員代理績效的直接可觀測指標,與高管薪酬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薪酬政策能夠有效反映代理質量,較為合理。這與宋增基、張宗益以1997年12月30日之前上市的129家滬市A股的中國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相一致: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這也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設2。
值得注意的是,從表3中可以看到,BSIZE變量系數為正,與預期相反,說明董事會人數與高管薪酬之間正相關,并且,二者的相關性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正常情況下,二者應該是負相關關系,即董事會成員越多,對高管的監督越強,其薪酬會越低。但這里卻出現了異常,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會監督效率低下:隨著董事會規模的擴大,董事們對關鍵問題的討論參與程度受到限制,協調與溝通的成本增大,董事會控制管理層的能力下降,有利于高管的決策容易通過;并且,獨裁型的CEO得以利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手操縱和控制董事會,從而使得其薪酬方案有利于高管。另外,SUPERVISER變量系數為負,雖與預期符合,即監事會人數與高管薪酬之間負相關,但P值較大,即二者相關性不顯著,說明監事會監督效率較低,絕大多數公司的監事會無法掌控公司實權,其設立只是為了滿足證監會的基本要求,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花瓶”,對高管薪酬的影響不大。并且,由于大多數公司為節省費用,均直接以證監會規定的監事會下限3人為標準,導致各公司監事會規模相差不大,回歸結果不顯著。基于此,本文的假設3沒有得到驗證。
從表4可以看出,DRATIO變量系數為負,且P值為0.0009,說明獨立董事占比與高管薪酬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即獨立董事占比越高,高管薪酬越低。這說明在創業板市場,一向被認為形式化的獨立董事制度對高層管理人員是有一定的監督作用的,這也與創業板市場特點有關。創業板上市公司大多具有成長快但風險較高等特點,市場泡沫嚴重,股價容易被高估,因此擔任創業板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專業人士必須加大對管理層的監督力度以降低風險,從而保全自身的名譽。基于此,假設4得以驗證。
最后,上表中BIG1指標相關系數為負,與預期相符,說明股權集中度對高管薪酬有負向影響。第一大股東所占比例越高,股東對公司高層的監督作用越大,高管薪酬會略有下降。但該指標t值偏大,二者的負相關關系僅在10%水平下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當第一大股東占比過高時,第一大股東對董事會有絕對控制權,也許反而會為高管人員提供一份不匹配的高薪酬以令其作出有利于絕對控股股東利益的決策。這與La Porta.R.和Lopez-de-Silanes在1996年的研究成果相一致,同時也驗證了本文的假設5。
同時可以看到,對于本文出現的控制變量MSR,實證結果顯示高管持股比例與薪酬正相關,雖然相關系數的符號符合預期,但二者不顯著,說明關聯性不大。筆者認為,創業板高管持股比例雖然較高,但創業板高管們持有公司股權并非為了在董事會占領一席之地,從而擁有公司決策權與控制權。由于創業板股價的持續上漲,高管們更愿意利用手中的股權在資本市場套現,實現高額的資本利得。這種行為具有明顯的短期投機性質,對高管們爭取長期薪酬水平的提升幫助不大。由于這種創業板市場特有的不成熟性,也就促成了本文開始提到的創業板公司上市不久便有33位高管先后辭職的轟動事件。因此,創業板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對其薪酬影響不顯著。
(二)建議
本文對創業板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2年上市期間公司特征對高管薪酬的影響進行分析,發現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正相關,與公司規模正相關,與董事會人數正相關,與監事會人數負相關關系不顯著,與獨立董事占比負相關,與股權集中度負相關。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創業板上市公司應盡可能完善和落實高管持股期限政策,并加強對分期股票解禁的審核力度。股權激勵過大,管理人員只需坐等企業上市便可輕松獲取額外收益,從而導致管理人員缺乏提升企業業績的動力。基于此,筆者認為,證監會應當完善和落實高管持股期限政策,加強對分期股票解禁制度的審核力度,維護創業板管理層的相對穩定。在高管持股期限的確定上,應結合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成長周期,待公司日趨成熟后,逐步減少高管持股,避免長時間持股,保持股權的流通性,促進外部資金流入企業。另外,要加強分期解禁股票時的審核力度。當持股高管準備解禁股票套取現金時,可以通過離職審計等手段考核其任期內公司成長性、未來發展能力等長期指標,避免一些高管人員以損害公司長期發展能力為代價一味追求其任期內的短期盈利目標,待套現離職后留給股東與繼任者一個“千瘡百孔”的問題企業。
【參考文獻】
[1] Fleming G. Stellios G. CEO Remuneration, Managerial Agency and Boards of Directors in Australia[J].Accounting Research Journal, 2002,15(2):126-145.
[2] Hall B. J., Liebman J. B. Are CEOs Really Paid Like Bureaucrat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113(3):653-691.
[3] Rosen S. Contracts and the Market for Executives[J].Contractual Economics, Oxford: Blackwell,1992:181-211.
[4] 杜勝利,翟艷玲.總經理年度報酬決定因素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05(8):14-20.
[5] 杜興強,王麗華.高層管理當局薪酬與上市公司業績的相關性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07(1):58-63.
[6] 張必武,石金濤.董事會特征、高管薪酬與薪酬敏感性——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分析[J].管理科學,2005,18(4):32-39.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為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其中,高管薪酬對數標準差為0.8872,說明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較大的差異,前三名高管年薪之和最高的達804萬元,而最少的前三名加起來只有16萬元,三人之和平均112萬元左右,每人平均高達40萬元,說明創業板高管薪酬水平總體較高。同時,公司規模標準差為0.6321,說明創業板公司規模相差較大,其中最大的資產總額為32億元人民幣,最小的僅有1億元左右,但總體來講,創業板上市公司規模偏小,這主要與其所處的高科技或服務類行業性質有關。公司董事會平均8.5人,與10人的國際慣例相近。其中獨立董事平均比例約為35.3%,即約三分之一的董事為獨立董事,說明大多數上市公司符合我國董事會成員中應當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獨立董事的規定。樣本中董事會成員最多18人,最少9人,在《公司法》規定5至19人的范圍內。第一大股東占比均值為34.76%,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股權相對集中,這也與公司規模普遍較小有關,其中,高管人員持股比例平均為26.21%,明顯高于其他板塊,這與上市前公司不斷推出股權認購計劃有關。公司平均每股收益0.74元,但波動較大,最高達2.78,最低只有0.033,但總體上講,業績水平較高。
(二)多元回歸
回歸結果見表3和表4。結果表明模型的擬合程度中等,可能是由于被解釋變量高管薪酬受到企業本身、管理人員自身以及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多方面的共同作用,甚至其中的很多變量難以量化或是難以獲取數據。因此,本文擬研究公司特征的相關指標對經理人薪酬的影響,不考慮高管人員自身因素。
四、研究結論和建議
(一)研究結論
由表3和表4可知,LnASSET系數均為正,與預期相一致,說明公司規模與高管薪酬正相關。并且,P值分別為0.0015與0.0002,均遠小于1%,說明公司規模對于高管薪酬的正相關關系在1%水平下顯著。公司規模越大,對管理人員的學歷、能力、精力要求越高,所產生的人力資源成本也就越大,自然會導致薪酬的上升。這與李增泉、魏剛等人的實證結論相一致,同時也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
上述兩表中,公司業績的衡量指標EPS系數均為正,與預期相一致,說明業績與薪酬兩者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而對應的P值分別為0.0473與0.0608,基本可以認為EPS與高管薪酬的正相關關系在5%水平下顯著。公司業績作為衡量高管人員代理績效的直接可觀測指標,與高管薪酬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薪酬政策能夠有效反映代理質量,較為合理。這與宋增基、張宗益以1997年12月30日之前上市的129家滬市A股的中國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結果相一致: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這也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設2。
值得注意的是,從表3中可以看到,BSIZE變量系數為正,與預期相反,說明董事會人數與高管薪酬之間正相關,并且,二者的相關性在5%的置信水平上顯著。正常情況下,二者應該是負相關關系,即董事會成員越多,對高管的監督越強,其薪酬會越低。但這里卻出現了異常,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董事會監督效率低下:隨著董事會規模的擴大,董事們對關鍵問題的討論參與程度受到限制,協調與溝通的成本增大,董事會控制管理層的能力下降,有利于高管的決策容易通過;并且,獨裁型的CEO得以利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手操縱和控制董事會,從而使得其薪酬方案有利于高管。另外,SUPERVISER變量系數為負,雖與預期符合,即監事會人數與高管薪酬之間負相關,但P值較大,即二者相關性不顯著,說明監事會監督效率較低,絕大多數公司的監事會無法掌控公司實權,其設立只是為了滿足證監會的基本要求,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花瓶”,對高管薪酬的影響不大。并且,由于大多數公司為節省費用,均直接以證監會規定的監事會下限3人為標準,導致各公司監事會規模相差不大,回歸結果不顯著。基于此,本文的假設3沒有得到驗證。
從表4可以看出,DRATIO變量系數為負,且P值為0.0009,說明獨立董事占比與高管薪酬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即獨立董事占比越高,高管薪酬越低。這說明在創業板市場,一向被認為形式化的獨立董事制度對高層管理人員是有一定的監督作用的,這也與創業板市場特點有關。創業板上市公司大多具有成長快但風險較高等特點,市場泡沫嚴重,股價容易被高估,因此擔任創業板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專業人士必須加大對管理層的監督力度以降低風險,從而保全自身的名譽。基于此,假設4得以驗證。
最后,上表中BIG1指標相關系數為負,與預期相符,說明股權集中度對高管薪酬有負向影響。第一大股東所占比例越高,股東對公司高層的監督作用越大,高管薪酬會略有下降。但該指標t值偏大,二者的負相關關系僅在10%水平下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當第一大股東占比過高時,第一大股東對董事會有絕對控制權,也許反而會為高管人員提供一份不匹配的高薪酬以令其作出有利于絕對控股股東利益的決策。這與La Porta.R.和Lopez-de-Silanes在1996年的研究成果相一致,同時也驗證了本文的假設5。
同時可以看到,對于本文出現的控制變量MSR,實證結果顯示高管持股比例與薪酬正相關,雖然相關系數的符號符合預期,但二者不顯著,說明關聯性不大。筆者認為,創業板高管持股比例雖然較高,但創業板高管們持有公司股權并非為了在董事會占領一席之地,從而擁有公司決策權與控制權。由于創業板股價的持續上漲,高管們更愿意利用手中的股權在資本市場套現,實現高額的資本利得。這種行為具有明顯的短期投機性質,對高管們爭取長期薪酬水平的提升幫助不大。由于這種創業板市場特有的不成熟性,也就促成了本文開始提到的創業板公司上市不久便有33位高管先后辭職的轟動事件。因此,創業板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對其薪酬影響不顯著。
(二)建議
本文對創業板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2年上市期間公司特征對高管薪酬的影響進行分析,發現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正相關,與公司規模正相關,與董事會人數正相關,與監事會人數負相關關系不顯著,與獨立董事占比負相關,與股權集中度負相關。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創業板上市公司應盡可能完善和落實高管持股期限政策,并加強對分期股票解禁的審核力度。股權激勵過大,管理人員只需坐等企業上市便可輕松獲取額外收益,從而導致管理人員缺乏提升企業業績的動力。基于此,筆者認為,證監會應當完善和落實高管持股期限政策,加強對分期股票解禁制度的審核力度,維護創業板管理層的相對穩定。在高管持股期限的確定上,應結合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成長周期,待公司日趨成熟后,逐步減少高管持股,避免長時間持股,保持股權的流通性,促進外部資金流入企業。另外,要加強分期解禁股票時的審核力度。當持股高管準備解禁股票套取現金時,可以通過離職審計等手段考核其任期內公司成長性、未來發展能力等長期指標,避免一些高管人員以損害公司長期發展能力為代價一味追求其任期內的短期盈利目標,待套現離職后留給股東與繼任者一個“千瘡百孔”的問題企業。
【參考文獻】
[1] Fleming G. Stellios G. CEO Remuneration, Managerial Agency and Boards of Directors in Australia[J].Accounting Research Journal, 2002,15(2):126-145.
[2] Hall B. J., Liebman J. B. Are CEOs Really Paid Like Bureaucrat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113(3):653-691.
[3] Rosen S. Contracts and the Market for Executives[J].Contractual Economics, Oxford: Blackwell,1992:181-211.
[4] 杜勝利,翟艷玲.總經理年度報酬決定因素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2005(8):14-20.
[5] 杜興強,王麗華.高層管理當局薪酬與上市公司業績的相關性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07(1):58-63.
[6] 張必武,石金濤.董事會特征、高管薪酬與薪酬敏感性——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分析[J].管理科學,2005,18(4):3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