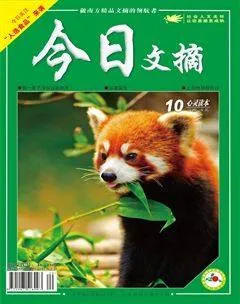馬魯姆火山,是地獄也是天堂
張昕宇
“要征服馬魯姆火山,需要先征服當地的土著人。否則,他們會送給我們飛鏢、利劍,最后把我們的尸體扔進火山里。”飛抵瓦努阿圖首都維拉港,準備向馬魯姆火山進發時,我們的向導、法國人帕斯卡撂挑子了。
作為世界上最活躍的兩座活火山之一,馬魯姆火山是瓦努阿圖人的圣山,我們得到了瓦努阿圖最高行政法院和文化部的同意,可以登山并進行拍攝。但通過火山下的安布里姆島上土著那一關,還得靠我們自己。
瓦努阿圖獨立于1980年,之前的150多年,這片島嶼群一直被英、法兩國殖民。因此,獨立后,土著們依然很痛恨白人。帕斯卡幫我們聯系了在安布里姆島上的另外一個向導喬伊斯。此人是當地土著的首領,島上的一切生殺大權全由他掌控。
以煙相待,以誠相待
我們租了三架飛機,兩架固定翼飛機負責把我們和行李送到安布里姆島。一架直升飛機負責從安布里姆把我們送到馬魯姆火山上。
到了安布里姆島,直升飛機在那兒等著我們,還有土著。村子一下子就亮堂了起來,無數火把點燃,還有燈。我們見到了喬伊斯一個30多歲的中年漢子,穿著一身戶外運動裝,完全是一個現代都市人的樣子。但除他之外的其他人,部分上了年紀的套著短褲,剩下的全都光著腳、戴著草帽,用樹葉蔽體。我們帶著微笑將從中國帶來的小禮品送給他們,他們并不感冒,一個老者走到我面前,跟我比劃,意思是問我有沒有煙。在安布里姆,煙是奢侈品,跟他們并肩抽著煙,友好的關系很快建立起來。
第二天,六個人上山,我、梁紅、魏凱、曾喬、向導喬伊斯和他的助手。
飛機低空飛行,一座座山頭像濃縮的3D地圖一樣,忽高忽低,特別壯觀。靠近火山的時候,天氣變了,這是火山帶的獨特氣候,多雨、濕度高、霧氣大,迷迷茫茫一片。直升飛機著陸費了點兒工夫,走下飛機,到處霧氣騰騰的,我們仿佛在云里。
我和梁紅走到馬魯姆火山的邊緣,一陣風吹散了山口的濃霧熔巖翻滾,熾焰沸騰,鮮紅耀眼,仿佛太陽的一塊脫落在了這里,任何語言都無法形容。梁紅淚眼婆娑地說:“這是我30多年以來,見過的最美、最震撼的大自然景象。這趟火山之行,已經圓滿了。”
喬伊斯的部落稱馬魯姆火山為天堂入口,如果有人在這里死去,靈魂會通過這里,進入到天堂。山下部落歷任酋長的遺體都被送進了火山里,包括他的父親。
在一種“神圣”的氛圍中,我們打開裝備、支帳篷、扎營……下雨了。查了一下天氣,臺風來了。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備受折磨,帳篷的支撐桿全折了,雨幾乎就是橫著飛,子彈一樣射在身上;裝備箱被吹得往高處滾……如果太冷了,我們就鉆出去,把身體往火山口里邊探一下。連續四天,我們的身上都沒干過。
第五天,雨勢轉弱,物資儲備耗得差不多了,即將彈盡糧絕,要進入馬魯姆火山,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經過一番勘察,我們確定了下降路線先是一個80度左右的斜坡,100米左右;接下來是一個絕對直角的垂直峭壁,再下面又是一段斜坡,然后經過一個負角度降到馬魯姆火山里面400米的地方,靠近熔巖湖。
路線確定后,我們開始制作錨點,弄好一切,天也黑了。喬伊斯找到我,說:“我不希望剛交到的幾個中國朋友,因為這次下火山而出現意外。”這些天來,每頓飯我們都讓土著兄弟先盛,這讓他們感受到了我們的尊重,也回饋給我們真誠。
“我不是瘋子,也不是傻子,我相信我能下去,也能上來。”我對喬伊斯說。
新西蘭人杰夫·邁凱里跟馬魯姆火山較了十幾年勁,三個月前,終于下去了。他有句名言:人生要么是一次不可思議的冒險,要么是平淡如初。
生死一線
行動的那天,天氣依然不好,但至少沒有下雨。所有的攝像設備,全被前幾天的酸雨腐蝕了,11臺攝像機,九臺報廢。我套上防護裝備,除了防毒面具,還有三層防護服。最里面是陶瓷纖維防護服,中間是石棉纖維防護服,最外層是鋁箔防護服。如果沒有這些,在離熔巖湖100米的距離,人最多只能待十分鐘。還有一個特別定制的一個上升器材,那種懸崖峭壁,爬上來不現實,如果靠上面人拉,我能被巖壁上尖銳的石塊撕成碎片。
第一次試降失敗了,但還來不及傷感,我們就等到了又一個壞消息——第二波臺風將在后天早晨到達。時不我待,我生命中最嚴峻的一次挑戰時刻,到來了。
第一個100米還算順利,但下到那個垂直峭壁時,通訊斷了。攀巖或者巖降,最怕兩件事:繩子斷了、通訊斷了。繩子斷了馬上死,通訊斷了等會兒死。
酸雨又開始稀里嘩啦地下來,霧氣越來越濃,什么都看不見。我在絕望中等了一個小時,對講機里終于有聲音了,原來是酸雨導致了通訊故障。后面沒有再出大問題,五個小時后,我到達了此次征服馬魯姆火山的第一個目標位置下降275米,這也是我的最低要求。
俯身往下,跳動的馬魯姆火山就在我眼前。隔著厚重的防護服,我的肌膚也能感受到它的熱情。沸騰的巖漿翻滾著,透著要吞噬一切的霸氣,要鉆到人心里去。眼前的馬魯姆火山,像有魔力一樣,牢牢攥著我的心,讓人不舍再離開,但在某個瞬間,我突然感到一陣窒息。防毒面具在酸雨中浸泡間太長,有點兒失效,一陣酸霧上涌,感覺全世界的氧氣都被抽光了。我放棄了繼續下降,因為,絕不玩命。
回到火山口的地面上,同伴捏著一段保險繩給我看,它已經被巖壁磨損得只剩一發相牽。還有那些金屬的繩套、鎖扣,都已經被酸雨腐蝕得變形了。如果我選擇繼續下降,可能就真的跟馬魯姆火山終生相伴了。
第二天,臺風如約而至,無法搭乘直升機的我們只得跟著喬伊斯步行下山,“我讓部落里的人上來幫你們搬行李,”他說,要知道,這本不是一個向導的義務。
我們整整翻越了九座山,還蹚了好幾個水坑,終于走出了火山覆蓋的地帶。眼前,是一片茂密的熱帶雨林參天古木,遮天蔽日,兩邊生長著從未見過的植物,還有好聽的鳥鳴婉轉。找了片空曠地休整,陽光穿過樹叢照射下來,八天里我們第一次曬到太陽。
喬伊斯爬上一個高地,開始唱歌:“這就是我們每天的生活,爬到山頂看到煙霧升起,就勇敢地擁抱我們的生活,擁抱我們美好的生活。”土著人獨有的醇厚嗓音,淳樸的歌詞,很動人。
在上個世紀瓦努阿圖人民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喬伊斯的父輩們也都曾去主要城市參與運動。國家獨立后,政府給他們分配了一些資源和土地,但是他們拒絕了,他們只需要他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生活在那里,守護那里。
回到安布里姆,帳篷、繩索等村民用得著的東西,我全都留給了喬伊斯。離開時,從直升飛機上俯瞰安布里姆,就像阿凡達的世界我們在這里見證了生死相依,我還在這里得到了一個兄弟。
(孫沖薦自《壹讀》)
責編:易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