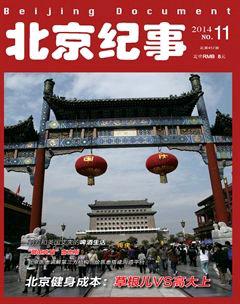用《小蘋果》征兵是一種進步
多思

最近音樂界有兩件轟動的事,一個是著名歌唱家李香蘭去世,另一個是神曲《小蘋果》被部隊拿去征兵了,還獲得了一等獎。但是兩件事其實并非毫無關聯。當年李香蘭優美的流行歌曲被稱為“靡靡之音”而禁唱禁聽幾十年,官方視之如洪水猛獸。如今流行歌曲《小蘋果》被用于征兵宣傳片,雖然被一些網民批為不嚴肅、惡心,但是沒有什么人再上綱上線到“亡國之音”了。而官方授予它一等獎,說明國人終于開始擺脫對“靡靡之音”的恐懼了。
人民網北京9月4日報道,據《解放軍報》官方微博消息,國防部征兵辦、總政宣傳部聯合主辦的2014年全國征兵宣傳片評選活動今天公示評選結果。軍營版《小蘋果》反響強烈,勇奪第一。
此前的7月27日,根據這首當紅歌曲改編的軍版《小蘋果》登錄國防部網站,這一由西安市征兵辦制作的征兵宣傳片迅速躥紅網絡,這一作品也被網友稱為“萌”系征兵代表作。但是這種做法也引起了巨大爭議,有不少反對的聲音認為:軍隊是神圣的地方,征兵應該是嚴謹、嚴肅、一絲不茍的工作,出現如此嘻哈的征兵宣傳片有失妥當。甚至有評論說:大老爺們兒扭著這首歌,真惡心!這首歌純粹是男人對女人的愛慕之情,怎么又變成對好男兒的召喚之聲!
但是筆者搜索查看了不少評論,還真沒什么人上綱上線到“亡國亡黨之音”和“靡靡之音”了。新華社甚至發表評論,認為對使用神曲征兵這個現象要寬容。曾幾何時,中國可不是這個樣子。9月7日,著名藝人李香蘭在日本逝世,終年94歲。李香蘭以一曲旋律悠揚的《夜來香》成名,與當年周璇、白光、張露、吳鶯音齊名“上海灘五大歌后”。但是解放后《夜來香》等歌曲被視為“靡靡之音”,在大陸禁止傳播幾十年。
這里想說的是,“靡靡之音”作為中國老祖宗發明了幾千年的詞語,曾經令人極度恐懼,誰要被扣上“靡靡之音”的帽子,輕者坐牢,重者殺頭。“文革”前的新聞報道中,只要充斥“妹呀”“愛呀”一類,均被扣上“靡靡之音”的帽子,“用低級趣味引誘聽眾”,“麻醉毒害人民”;要求代之以“人民大眾的雄壯聲音”。“文革”中,報紙把《花兒與少年》《哎喲,媽媽》等流行歌曲均斥為“消磨人們革命意志的‘靡靡之音’”。
鄧麗君在大陸當紅的80年代,一直都被作為“靡靡之音”“黃色歌曲”的代表,是一個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花花舞女的聲音。她的歌只能通過敵對勢力的電臺收聽。 當時最早傳進大陸并流行開來的鄧麗君歌曲是《何日君再來》。然而這樣一首在今天看來中規中矩的情歌,被當時的《人民音樂》雜志分析為“這不是一首愛情歌曲,而是一首調情歌曲,不是藝術歌曲而是商業歌曲,是有錢的舞客和賣笑的舞女的關系……”不止鄧麗君,李谷一的《鄉戀》學習鄧麗君唱法,被批為“低沉纏綿的靡靡之音”,李也被批為黃色歌女。
與李谷一差不多同一時期的蘇小明也曾被批為“靡靡之音”“低俗”。1980年秋,蘇小明演唱《軍港之夜》一舉成名,然而很快批判接踵而至。《人民音樂》說它“格調不高”。《軍港之夜》曲作者劉詩昭還記得當時老一代音樂家們的反對之聲尤其大,甚至有人說,聽到這首歌就像聽到過去在30年代舊上海迎接外國水手的妓女所唱的歌曲。
說起對歌曲積極向上意義要求最嚴格的時代,那肯定是“文革”時期莫屬。當時所有的文藝工作都要服務于政治宣傳,中外經典作品紛紛被掛上“封資修”的帽子,如《二泉映月》被說成是“黃色爵士音樂低沉悲戚的節奏,傾吐著一個沒落階級垂死前的哀怨和呻吟”。瞎子阿炳被批成“一個從精神上屠殺勞動人民的職業道士”。
筆者以為,小蘋果是一首比較俗氣的愛情歌曲,要是放到“文革”前,肯定屬于“靡靡之音”無疑。但是“靡靡之音”真的能亡國嗎?著名的陳后主的一首《玉樹后庭花》就讓南朝皇帝沉溺酒色不理朝政,最終亡國?還是本末倒置?記得有個社會問題“磚家”,他搞出一個研究主題是“過早接觸性,造成少女暴力傾向”。如果想證明這個主題,本應該先去找一些結婚比較早的地區,例如云南傣族地區,或者中國農村地區去調查。但是他卻跑到少管所,找到所有暴力傾向的少女,然后挨個問:“你們是不是性生活比較早?”當然得到的答案是這位“磚家”想要的。
低俗的音樂只和素質有關,和道德品質沒有必然聯系。固然,如果中國大眾的音樂素養都能達到欣賞貝多芬、瓦格納的水準,那么用這種音樂征上來的兵就有達到德國士兵的潛質了。可是如今國人就《小蘋果》和《月亮之上》《最炫民族風》的水平,用這種音樂征上來的士兵就不愛國,就女性化嗎?這也太牽強了吧。從這次官方對《小蘋果》征兵的態度來看,中國人對音樂作品的態度絕對是進步了一大塊。
(編輯·宋冰華)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