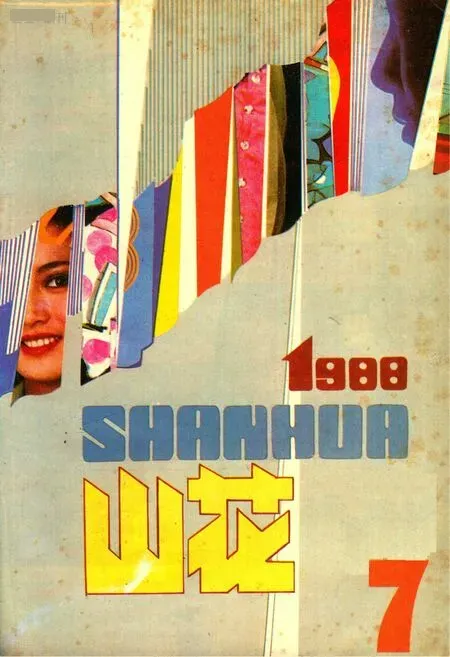我曾居住在亞洲中心
一
小心冰柱!
清晨,當我背著雙肩包,繞過馕坑和賣袋裝鮮奶的小店,來到這幢灰樓底部時,視線里出現(xiàn)了這張白紙黑字——小心冰柱!
在嶺南,看慣了“小心扒手”、“小心搶劫”、“小心陌生人”,我完全不記得,“冰柱”,也如此強勢。我像頭即將挨宰的獸,全身被速凍起來。
順著墻壁看上去,七八米高的屋檐上,有一灘冰柱,參差不齊的錐形,比狼牙晶瑩,比和田玉透明,兇猛冥頑,放肆猙獰,似千軍萬馬要出籠,撒著性子朝前跑,拉都拉不住,慌亂中,便狠命地往下一刺,刺穿無遮蔽的腦殼、柔嫩的肩膀、脆弱的脊椎、汩汩的動脈。我趕忙移動腳步,離開屋檐,才覺得踏實了,但這一來心臟便似驚馬般躍起,呼吸隨之急促起來。
二
烏魯木齊,亞洲中心,中國離海洋最遠的內陸之城,孤獨之城,一出生,便遭嫌棄,被拋在遠方,是死是活,悉聽天便。
從1993年8月至2010年8月,我居住此地,2013年1月,我才再次回到這里。
遷居后,我將全部注意力都轉移到嶺南,試圖忘記這個城市,無論它的公交線路圖,或習慣用語,我試圖像一個從荒漠里走出的野人,沒有過去,沒有歷史的烙印,然而此刻,“小心冰柱”的斷喝,讓我陡然清醒——我曾努力收集的南方溫暖,在這一刻,土崩瓦解,我又陷入到冰雪世界,變成瑟縮人。
雪被西伯利亞的風吹來,落在艾德萊斯綢的圍巾上,羊羔皮的帽子上,清真寺、教堂和寺廟的屋檐上,雪在田野里形成凍土,在馬路上化成泥濘,在樓房外墻的空調散熱器上,凝成疙瘩。所有這里的孩子,都是寄宿在風雪中的孩子;所有這里的路燈,都在風雪中暗淡著,微弱的光無法傳遞溫暖;所有這里的街道,都被積雪淹沒;所有這里的行人,都像個球,跌跌撞撞地滾動著。雪對此地,不是滑雪場、冰雕、風光片,而是冰霜、嚴寒和瑟縮。
我忘不了第一次進入嶺南夜市,目睹喧囂的大排檔、人字拖里的赤腳、霧騰騰的蝦粥、黑油的荔枝樹時,身體里陡然涌起的沖動。我感到身體所有的細胞都醒來,我被百分之百打開,我被這種豁然敞開嚇了一跳。我默默地行走著,恥于告訴本地人,我的身體從未這樣松弛過,即便是盛夏,我依舊延續(xù)著冬季恐懼癥,依舊會被驚悚糾纏,不信任那天空,那白云,那街道,感覺某一時刻,它們會突然改變顏色,將我整個裹挾,時而騰空,時而陷落。
此時此刻,我笨重地,著了魔似地,盯視那張紙——小心冰柱,我試圖調動聽覺、視覺、嗅覺,來揣測它的危險程度,然而,我越靈敏,它越放肆。我曾從一個又一個冰柱下走過,懵懂無知,倘若我稍一抬頭,便知那殺人利器,一直高懸于頭頂。
是的,冰柱無處不在:無論五星路、青年路、北門、八一中學、七四三八工廠、南門劇院……我從未認真凝視過那蟒蛇般殘忍,又格外健壯的家伙,當我從它的勢力范圍走過,渾然不覺。像我從未看清過烏魯木齊,看清過自己,看清過我和這座城市的關系般,囿于某種羞愧、虛弱或虛榮,甚而冷酷——我從未看清過這一切。
三
在嶺南,我見過月租金一百元一間的瓦房:低矮、潮濕、逼仄。地面抹著水泥,潮氣匯聚,形成水汽,反射出薄薄的銀光,幽深墻角的綠苔,毛茸茸一團,如只綠爪。向上攀附,半空中用木板搭出閣樓,孩子睡,樓下的雙人床,是打工多年的夫妻。女人黝黑粗糙,男人精瘦寡言。女人在砧板上切菜,紅臘肉綠萵筍。男人夾著煙卷,盯著電飯煲的指示燈,從紅變綠。兒子順木梯而下后,父親丟掉煙蒂,從墻角摸出瓶啤酒,用嘴咬掉瓶蓋。
當男人說起租房時間是1993年時,我的心尖一疼。
這一年,我大學畢業(yè),被分配到哈密某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震驚之余,我無暇了解那個廠是做腸衣,加工番茄醬,或釀造紅棗酒的(我并不打算和這些泥腥味很重的東西有任何牽連),將檔案存在鄉(xiāng)政府后,我決定到烏魯木齊自謀生路。乘火車離開哈密時,已是深秋。我并不明白這懵懂的選擇,會讓我既定的人生軌跡,如地殼皺褶般,發(fā)生巨大錯位。
走出烏魯木齊火車站,乘8路公交車,在紅山站下車后,我驚詫萬分:用一座山來做地名,烏魯木齊,你好奢侈!半空中,確實有座塔在搖晃,似火柴棍;2013年,當我走過西大橋,掏出照相機,對著那根火柴棍按下快門時,已徹底淪為游客。
在這座風雪之城,我所消耗掉的17年,像一道閃電,再也找不回來;我的性格,被這個城市定型;我的寫作,始于這個城市;雖然我已離開,但鼻孔里依舊殘留著辛辣的冰雪味;在嶺南,在棕櫚樹簇擁的盛夏,我身體的某一部分,依舊被冰雪速凍著;多少次,我夢回這里的大街小巷。
而關于1993年的自己,我是通過姜雪(為辦理遷戶,我需要她幫忙查閱一個文件),才陡然想起的——
“那時,你又年輕,又漂亮,又努力……”
看不見的眼淚,唰,從心尖滾下。
1993年冬,我試圖抵抗命運,擺脫由父母、親戚、同學編織的人際蛛網(wǎng),抵達另一座城市,開始冒險生活,這個命令,是我自己下達的。此前的那些歲月,我的反叛都是局部和微小的,這一次,我快刀斬亂麻。無依傍,無背景,無智慧,無技巧……這個混沌女生,將盲目上路的戲劇,居然,在人生歷程中上演了兩次(1993年,她尚且年輕;2010年,她痛恨照鏡子),兩次行為的內核,都是逃離。像高壓鍋的出氣口,嗤嗤燃燒,若沒有這樣一個通道,那鍋,早晚要炸裂。繼續(xù)滯留原地,我的肉身尚且活著,但精神,會日漸枯萎,我必須拯救自己。
于是,新我誕生:休閑外套,牛仔褲,白運動鞋,黑發(fā)束在腦后,臉頰白里透紅,眉毛淡而彎曲,唇膏棕紅。這個新來的女子,在烏魯木齊南門體育館旁的綠樓下,手拿鐵鍬鏟雪,身后,是通往報社的一級級臺階,其上,辦公室狹小,樓道兩頭架著兩部電話,鈴聲不斷,被喊到名字的人,像穿了溜冰鞋,滑翔而過(如今,體育館不復存在,綠樓已被炸,新崛起一排高層)。
我們在掃雪:揮鐵鍬、推紙板、跺著腳、哈著氣(我曾無數(shù)次夢到這個場景)。進入這個集體尚不足一個月,我還不能將那些記者的名字,和這些活動人形黏在一起,但我已迷戀上這個戰(zhàn)斗場景,我已從這些青年才俊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來。雖然新聞是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我急于得到榮譽,便使出文學青年的全部招數(shù),孤身上場,開始搏斗。
采訪、寫稿;寫稿、采訪。
20年后,我陡然發(fā)現(xiàn),這個節(jié)奏,是我一生的主旋律。
20年后,已是中層領導的的女友向我抱怨說:我是報奴。我驚詫于這個詞:“報奴”!不……不……我向來喜歡文字,無論將它們排列成何種方式,我都會在困難的勞作中獲得愉悅,而不會將怨憎擴大,將自己貶損為奴隸。
我不斷出差:南疆、北疆、東疆;不斷寫稿:消息、通訊、特寫。我興沖沖,忙碌碌,狼奔豕突,刀光劍影,披荊斬棘的生活,和資料員姜雪安靜、單調、乏味的生活,截然相反。那時的姜雪,剛褪下軍裝,臉上還延續(xù)著女兵的單純微笑。我在資料室翻報紙時,隨口講述的出差場景,都會令她唏噓嗟嘆。她像個玻璃美人,永遠被囚在牢房中;而我是灰姑娘,赤足奔跑在長滿荊棘的道路上。她安全,我危險;她四平八穩(wěn),我心驚肉跳;她是直線,我是波浪。我們的生活原本沒有交集,卻相遇在一個意外的拐點上。
這一天,資料室里只有我和她。她的眼仁里閃爍同情之光(前女兵在聆聽新記者訴苦):出差苦,寫稿苦,發(fā)稿苦,挨批評時苦……然而最終,苦水匯集成一條河,流向正題:無論怎樣的苦,都無法和沒有單獨空間的苦,相提并論。我發(fā)揮文字特長,塑造出抒情畫面:
“為了構思,我一個人走在雪路上,走啊走,走啊走……”
啊……我多么矯情。我看到自己在大演特演滑稽戲。無論我怎樣講述,都有故作高尚之嫌。我嘩眾取寵地表白,“構思文章需要單獨空間”,可是不,換衣服和痛哭,擁抱和接吻,都需要單獨空間。我尚無能力購房,也無法指望分房(要有結婚證),在本市又無親朋好友,如何能獲取一個單獨的自由空間?
我想到了姜雪——她有個小宿舍。她父母家就在本市,且她新近結婚,她根本無暇光顧那個小空間。可我垂涎三尺,認為那個兒童房,堪比天堂。我厭倦透了多人共居。小宿舍,哪怕它小如針尖,我也可以把門閉上,把自己變成比針尖還小的物件。我受夠了——不僅要踩著冰雪采訪,忍饑挨餓,四處奔波,還要在各種噪聲中寫稿,在各類鼾聲中閱讀,深夜醒來,感覺胸口憋悶,像呼吸被別的軀體搶光,恨不能捂住那些嗤啦啦的鼻孔。
2013年,我背著雙肩包,穿著厚底牛皮鞋,腳上套著兩雙棉襪,這裝扮,延續(xù)1993年的風格,只是那時的自己,更瘦,更憂郁,更尖銳。那個年輕女孩,尚不能駕馭自己,任由火山蓬勃的身體,隨著盲目熱情,肆意漫流,我看見她走在落雪的燈下,注目天空被巨型塑料薄膜籠罩,地面騰起白霧,雪花從下而上飛舞,像在酒里蘸過,姜紅橘黃。伸出手,那彩色雪花在掌心消融,喪失觸角后,變成一串淚。她不斷采訪,甚而忘記了自己的角色,好像不是在走路,而是在疾馳,被一股狂暴的龍卷風所裹挾。
1993年,在邊城烏魯木齊,尚不流行“打工”這個詞,到達嶺南后,我陡然發(fā)現(xiàn):1993年,我已開始打工。雖然在心理上,我從未讓自己淪為“報奴”,然而事實上,放棄分配的工作,在另一個城市,以聘用者的身份謀生,我已和那些從湖南、湖北、廣西到達珠三角,進入電子廠、制鞋廠、音像帶盒廠的女工,無任何差別。
哦,有一點差別:在我的打工之路上,有冰雪做背景。冰雪加劇了打工的艱辛,讓我對無情的理解更深刻,讓我身體里的某一部分,變得僵硬;冰雪滲進我的血脈,循環(huán)至心臟,將我牢牢掌控,我像那些從爐窯里燒制而成的瓷器,我是從冰雪的洞窟里鍛造出的物件,不是瓷不是鐵不是塑膠,而是一種以泥土為主要原料,又增加了各種金屬元素的新產(chǎn)品,遇冰不寒,遇火不燃,遇水不融。
我決定賄賂姜雪的,是只平底鍋(開會禮品)。

陳家剛 《城事-上樓的女人》 攝影 2013

陳家剛 《城事-上海的早晨》 攝影 2013
裹上黑塑料袋,塞進紙袋,拎著,來到資料室。那鍋很小,但厚、重、結實、華美、絕對招主婦喜歡。我笨拙、慌亂、堅定地,將紙袋塞進資料員手中,誘導她:“你可以煎雞蛋,一點都不粘……”這句慌亂的臺詞真是精彩,好似一切童話的精髓:“你可以……”、“你當然可以……”、“你為什么不可以呢……”。
兩個20歲出頭的女孩,在1993年冬日,第一次行賄,第一次受賄。
20年后,我為這個場景傷痛,并非因我對這不加思索,突兀而為的率性舉動后悔,更看到自己在青春期,曾犯下了一系列如此這般,唐突而混亂的錯誤。我是我行為的犧牲品;我正是被這樣的舉動傷害著,變成今天這個模樣。現(xiàn)在的我,完全不理解年輕的自己:何不更理智點?更聰慧點?然而,來不及了,一切都來不及了,我慌里慌張,將平底鍋塞給姜雪,同時,也將一份難堪,塞進她的人生。
20年后,我進入姜雪的辦公室。這是她一個人的辦公室。她抄起電話,喚來助手,囑咐他去辦事時,口氣溫和而威嚴。辦公桌上放著電腦和打印機,墻邊是成排的文件柜,存著姜黃檔案,硬殼脊柱上,黑筆標注“退休”、“在職”。柜子頂部,是黃燦燦的獎牌,閃爍紅字。衣架上,藍底黃花的絲巾,延續(xù)前女兵的一貫風格:明朗、熱情。
她打開柜門,搬出一大摞文件,翻找著,回憶著。突然,她頓住,像想起點什么(或者,她等待這個機會,已20年)。她說:“我們那個時候,真是太傻了……”
姜雪說起女記者海莉推開資料室的門,質問她為何把宿舍讓給別人時,她脫口而出:“人家早都給我說了……”傻里傻氣的姜雪,還說:“而且,我還收了她的平底鍋……”
女記者目光灼灼地望著資料員,聲音威嚴:“姜雪啊,為了個平底鍋,你就把宿舍出賣了……”
這真是個驚駭?shù)脑~——“出賣”!
姜雪變成冰雕,不僅僅是尷尬,還夾雜著驚恐。她頭暈腦脹、心驚肉跳、惶恐不安。在報社這個龐大的三角體系里,資料員處于最底層。當資料室變得空空蕩蕩,冰冷的寒氣傳導進身體,讓姜雪篩糠般顫抖起來。20年后,當姜雪向我復述時,好像這件事就發(fā)生在昨天——昨天,資料員聽到耳畔一聲悶響,一塊沉默的大石,噗通一聲,墜入胸腔海洋。
那種梗塞……那種委屈……那種難堪……她從未經(jīng)受,卻要隱忍20年。
姜雪的手停在文件上,望著我,突然,噗嗤笑了起來——那個當年的心結,在今天的這一刻,獲得了結;那個秘密之鎖,只有通過知情人的鑰匙,才能打開,迎來敞亮,否則,它便如墻根積雪,曠日持久地盤亙心頭。
我和姜雪在此后,遭遇到無限厭憎;而這厭憎,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后半生。這個20年后浮凸而出的平底鍋,難道是罪惡之源?不……不……顯然,平底鍋是無辜的,是我的任性、私欲和莽撞,損害了自己,也累及他人。我是殘忍的;我的自私亦是殘忍的。我根本無法彌補這事的后果,任由它像一道傷疤,經(jīng)風吹日曬,腐爛到骨髓。
而我所懊悔的,又何止平底鍋一件事;而我所傷害的,又何止姜雪一個人!
在嶺南,我總是防止思緒漫溢,觸及那座中亞之城。

陳家剛 《城事-上海人》 攝影 2013
烏魯木齊,不是我的故鄉(xiāng),也不是我最終的屬地,然而,如那團屋檐上的冰柱,高懸在我的頭頂,時刻盯視著我,念念不忘我曾最狼狽不堪,最混亂不堪,最寒酸不堪的青春歲月。一想起烏魯木齊,便像是用手揭開尚未痊愈的傷疤,痛癢難忍。我幻想自己從未做過錯事,可以將青春改寫,然而雪花,像從天外降落而下的咒語,被冥冥之力驅使,讓我的肺擴張,讓我的眼明亮,讓我豁然洞悉,無論我逃得再遠,也無法回避那散落一地的詰問;我若不能正視曾經(jīng)的羞恥,便永遠無法矯正自己,去除心魔。無論我多么奮發(fā)圖強,抬頭翹尾,讓偽裝好的自己,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搖過市,那過去的疼痛,依舊會像冬日街道上,從井蓋里蒸騰起的柱狀熱氣,讓我無法回避。
啊,怎樣的暴力,曾侵蝕過我的身體;怎樣的怠惰,曾麻木過我的魂靈?怎樣的冷酷,如腐蝕性極強的生石灰,施放出巨大磁力,曾摧殘過我的青春?我一面向著2013年1月之后的日子前行,同時,又一點點倒回去,撿拾1993年冬天的日子。這兩種方向不同的生活,并不打架,也不混淆,它們各自向前發(fā)展,獨立成章。我只有厘清最初的罪虐,才能撥開此刻的烏云。
我看到過去年代的自己,坐在幸福路宿舍的門廳里,木桌上鋪著鵝黃桌布,方格稿紙攤開,手握鋼筆。門廳周圍,有四扇門,全都關閉著。我在寫稿。我的模樣,是否具有表演性質?我是否在扮演某種更高尚的角色(先讓自己整個身心投入進去,然后,就以為自己從此高尚起來)?啊,平底鍋出現(xiàn)得那么晚——要過去整整20年!
我的一生,都無法擺脫這個昭示自私、偏狹、執(zhí)拗、刻薄、虛榮、狂妄的污點!
我將永遠都不可能美好,永遠殘缺,永遠被指指點點,釘在十字架上。
我的鋒利青春,就這樣疾馳而過,我不再刀光劍影,興興沖沖,我的日子變成落花流水,嘴角微笑日漸慈祥。我已性情大變;甚而,某個曾在烏魯木齊見過我的男人,在2013年1月嶺南宵夜時,雙眼環(huán)睜:“你不是這個樣子的……這不是你……”
面對這樣的嗟嘆,我欲哭無淚。
是的:終于有一天,我平和溫順,宛若一只波斯貓。我也有這樣的一天?!連我自己都悻悻然。然而,一旦我收起笑容,夜深人靜,心情便會一落千丈,降到谷底。我的本性又將暴露:那波斯貓的爪子,抓撓著,正無限躁動。
四
我和海莉的關系,多么具有戲劇性:我和姜雪的私下交易根本不算數(shù),報社總務處統(tǒng)一分配宿舍,神使鬼差,我和海莉被安排在一間屋,兩張單人床,面對面。
這真是世上最嚴厲的酷刑:讓兩個根本不相愛的人,共居一室。

陳家剛 《城事-上海往事》 攝影 2013
這個被壓縮的空間,像沒有欄桿的監(jiān)獄,兩個雌性動物,互相厭棄。出現(xiàn)在這個空間里的床,是預備給“姑娘”的。“姑娘”獨自一人睡著,再醒來時,依舊保持處女的貞潔;而當兩個“姑娘”的目光交織在一起時,陡然間,對方變得可怕起來。如此之近——能聽到對方心跳,及埋藏在噗通聲中的仇恨。半米之遙,鋪滿玻璃碎片,尖銳僵硬。其實,她們的任何行為,都沒有出格,要命的是,當這些細節(jié)展現(xiàn)在宿友面前,像人在顯微鏡下看到自己的手掌,會被嚇得不能呼吸。
海莉嚷嚷著頭疼,躺在床上不起來;海莉厭煩噪聲,笑聲,以及任何公開的熱情;海莉純潔如白雪,女王般側臥;海莉善于表演德行,或者,她不需要表演,只需拿出本色就已超群;海莉永遠目光平和,充滿對現(xiàn)存秩序的敬重;和我顛三倒四,毛毛躁躁,前言遮不住后語的混亂相比,海莉受到眾人的贊揚,幾乎輕而易舉。
海莉閉著眼睛在哼哼,奇怪的是,那來自半米之遙的肉體信息,卻像穿越了寬廣銀河,千回百轉,抵達耳膜時,已微弱得像不存在,我像看一幅畫,或一個電視鏡頭,雖然也有反應,但卻是禮貌而節(jié)制的。我凝視海莉,眼神里沒有任何溫度,那個呻吟的軀體,和我看到的桌子、凳子、拖把、水杯一樣。這種相互的冷漠,讓兩個女人的心靈,像被大雨蹂躪過的田野,泥濘而艱澀。那時,我曾嘲笑過她(她亦然),現(xiàn)在想來,不免后悔。海莉確信一切皆好,讓她自己恍如公主,有何不對?也許在海莉這樣的土壤里,根本不適合生長邪惡,故而海莉喜歡人人,人人喜歡海莉。
然而,她卻不喜歡我。
直到傻瓜姜雪招供出平底鍋,那些不詳?shù)念A感,才一一坐實。
那時,我只知海莉看我,宛如月光下的雪堆。在海莉白皙的皮膚下,鼓凸的血管里,流淌著高貴的藍色血液,恰和我這渾身躁動的茸毛怪獸成反比。海莉有資格高高在上,俯瞰于我;直到她瞌睡,躺下,輪到我看她時,驚悚片才正式上演。我看到她像一塊案板上的肉,只是更大一些。這可怖的想法,讓我覺得自己在干人類中最羞恥的事。然而,我無法克制這種暗夜里的覬覦。我恍如暴怒的法官,手提皮鞭,圍著那團肉打轉轉。
我說:我讓你看到了那么多,可我卻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為什么?!
我想發(fā)作,但憤怒的河流卻在喉管處倒流回去。我下意識地伸出手,捂住嘴唇,確信自己并未出聲,但我又分明感到憤怒曾聲勢浩大地來過。我這是怎么了?我會不會發(fā)瘋?我會不會干出更出格的事?
多么可怕……這女人與女人的對壘。
多么可怕……這源自冷漠的傷害。
對床的眼睛,越來越像放大鏡、顯微鏡、天文望遠鏡,而我是她的山峰,只需一抬眼皮,便可清點山脊山谷:你就是這樣……你從來就是這樣……你再假裝,也是這樣……
明晃晃的傷害,可用明晃晃的辦法回擊,如若只是沒精打采,熟視無睹,相對無言,那簡直——可以發(fā)瘋。后來,當我看到有關集中營、嚴刑拷打、大肆搶劫、對不設防的城市進行轟炸的文章時,驚詫地發(fā)現(xiàn),那些暴行,我似曾相識——當飛機扔下炸彈時,那對在宿舍里相互厭棄的女人,也在空中,品嘗過炸裂開的滋味。肉體在接受貧困、饑餓、疼痛的折磨時,會感到受了傷害,而在遭遇無視和冷漠時,所感受到的傷害,更甚。
我曾有過一個大黑包,斜掛右肩,銀鏈閃爍,三層內里,裝著采訪本、鋼筆、錢包、口紅、紙巾、面霜、牙刷,每日奔波采訪后,到妹妹的大學宿舍,和她顛倒著睡,懷里抱著她的腳丫。早起,在長條水泥池邊,接冰涼的自來水刷牙,牙床冷至發(fā)麻。那雙白色運動鞋,走過北門、西大橋、紅山、向陽坡、鐵路局、卡子灣、南梁坡、水磨溝……某一天,脫下雙層襪子,襪底濡濕,反過來,鞋底從中間斷開,裂出道黑縫。
1993年冬,冰雪依舊,然而,南方自由的暖風,已吹到邊城,我所打工的這家報社,試圖通過占據(jù)市場份額來抗衡大報,它如新興資產(chǎn)階級,破除封建門第,吸納新鮮血液,讓每一篇報道,都和那張大報,迥然不同。
于是,我來了。
如果時間更早,烏魯木齊根本沒有這樣的打工機會;如果更晚,各種配套制度已完善,我亦不會遭遇那些毛糙傷痛;然而那時,一切剛剛開始,混亂無序,鮮活緊張。
來自南方的思想解凍,提供出一片精神園地,一群青年知識分子,在狹小辦公室里,討論選題,聯(lián)系采訪,奮筆疾書,激揚文字。是的:無需分配,無需專業(yè)對口,無需要經(jīng)驗豐富,來了就干,先干起來再說。上班僅一周,我被派去南疆采訪。稿件上了頭條后,我讀報時,渾身顫抖。而且,多勞多得:第一個月收入870元,(那時,這是個很大的數(shù)字)。20年后,報社搬了家,辦公樓簇新,然而,骨子里卻喪失了青春熱血,恍如夕陽殘喘。
和海莉相處得越久,傷害便越深:我們都沒有能力在短時間內搬離宿舍,便要互相忍耐,然而,每當我遭遇那冰涼目光,都會倒吸涼氣,想到她真會演戲,一離開宿舍,便對別人熱情萬丈,愛心充盈。我早已看透她——她對我的蔑視,發(fā)自肺腑。在她眼中,我和所有聘用人員一樣,都無足輕重,這讓我既羞恥,又憤怒;然而,攤開報紙,海莉的稿子四平八穩(wěn),每個詞語都像戴著腳銬,而我的文字,肆意汪洋。啊,這是我唯一能戰(zhàn)勝她的地方;這也是這個金字塔體系,能接納我、容忍我的原因所在。
真相水落石出:我和她,根本就是階級不同。
我們的關系,比愛情已死亡的夫妻,更可怕——我們無法離婚。我們要將千刀萬剮的難受,轉化成日常生活中的空氣和水,以坦然之姿吞咽。我們同室操戈,將自己撕裂得支離破碎,成為鏡子的正反兩面。我甚至,學會了用她的眼睛來觀察自己:
你真的有那么好嗎?你其實,不過就那樣!你真的,不過爾爾……
我們僅僅是室友——終有一天,我們會搬出宿舍,所有圍繞著這個逼仄空間的苦惱,都將煙消云散,可我甚至到了嶺南,都無法忘記海莉,無法忘記她的臉,她的頭發(fā),她嗜好怎樣的電視節(jié)目,她睡覺的姿勢。記憶的天平,并不歸順我的擺布,反而讓她的模樣,隨著時光流逝,清晰如刀刻。
這個我不愛也不恨的女人,始終,存在于我的腦海。
五
姜雪一邊翻閱文件,一邊抱怨:時間太久了,真的不好找……
我抱歉地等待著。我需要這個文件,來證明辦理戶口時的一項指標。
少頃,她驚嘆:找到了!
那張紙,面黃肌瘦。在它從白到黃的變遷中,打印在它上面的名字,那名字的主人,同樣,也經(jīng)受著時間的熬煮。
等待復印件時,她突然說:海莉的辦公室,就在樓下……
不,我擺手,我并不打算拜訪海莉;然而,卻止不住好奇:她怎么樣(結婚了嗎)?
姜雪淡然一笑:還是那樣(依舊獨身)!
海莉還是一個人——即便海莉已從宿舍搬出,住在自己買的的屋子里,她依舊將單人床的素凈狀態(tài),延續(xù)下去。
我忽然憂傷起來:這世上,原是沒有忠誠的。
我似乎看到清冷的月光傾瀉于床,女人睜著眼,想著自己浮游半空的人生,被雨淋,被風吹,被閃電刺穿,便控制不住,滾下淚來;不,這不是真的。我曾見到的,是另一個海莉。海莉將眉頭一拱,海莉隱隱一笑,海莉深夜凝眸,海莉在筆記本上疾書……那個外表圣潔的女人內里,正翻涌著不為外人所察的瘋狂。毋庸置疑,海莉在熱戀,海莉渾身澎湃的潮汐,能將一切障礙物化為齏粉。
這樣的愛戀,居然,被我驚魂一瞥;這樣的愛戀,居然,無疾而終。
海莉啊海莉。我們曾離得那么近,甚至能聽到對方呼吸,卻巋然坐在自己的床上,坐成一尊冷性雕像;我們從沒有邁開腳步,像走進篝火那樣,走進對方的生活,讓自己的身體,生出些許暖意。
我一直都無法理解我和海莉的曖昧關系,一直都耿耿于懷:何以她不能像汽車舊殼那樣,松懈掉螺絲,咔噠一下,整個脫落而去?重返烏魯木齊,我陡然明白,是我自己不愿讓海莉離開,是我自己將海莉典型化,讓我讓她成為我青春時代的審判者、質疑者。
事實上,我所寫下的海莉,已不是真實生活中的海莉,而是多個他者的綜合形象(他們都叫海莉,他們都用灼灼目光,長時間、跨地域、不放松地,盯視著我),他們關注我所走的每一步,助我成長,是我的逆行菩薩。
小心冰柱!
我站在灰樓下,看到小巷被黑雪覆蓋,腳印深深淺淺,頭頂冰柱碩大尖銳,便快步離開屋檐,將身體挪到空曠處。我知道,那頭頂利器,在某個時刻,當真會變成老虎舌頭,舔我的皮,噬我的肉,嚼我的骨。我瑟縮著,站在狂風冷雪中,不停地打擺子。
這一刻,我原諒了自己。
是的:我必要離開這里,才能將噩夢滌蕩得一干二凈,才能收拾起青春骸骨,重新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