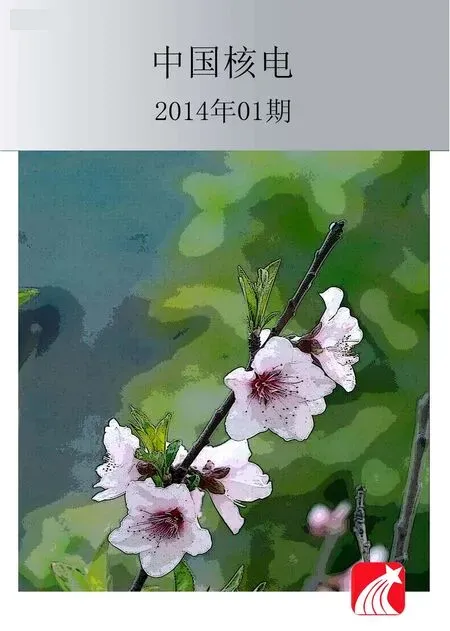核能發展的歷史觀
杜祥琬
核能發展的歷史觀
杜祥琬
20世紀初期,是引人入勝的核科學發現時期,人們對核結構和核能的一系列原創性的發現,引起了物理學乃至整個科學技術領域的革命性變革,把人類對物質世界的認識提高到一個全新的水平。
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1913年,玻爾提出了原子的核式結構理論,愛因斯坦稱贊玻爾提出的原子模型是“思想領域中最高的音樂神韻”。1932年,英國物理學家查德威克發現了中子,同年,海森堡和伊凡寧柯分別獨立提出了原子核由質子和中子組成的模型。1938年,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等發現了核裂變。后來科學家又發現了核聚變,以及原子核結合能隨原子量變化的規律和質量虧損的概念。
這一個個歷史性的重大發現與一個最簡明方程式(E=mc2)的結合,奠定了核能的理論基礎。核科學揭示了微觀世界的結構和規律,也揭示了宏觀世界的某些內在規律(如太陽內部的核聚變)。
在核科學的開創階段,以錢三強、趙忠堯、吳有訓、王淦昌等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也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貢獻。核科學技術是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創造之一,是科學技術史上的輝煌篇章,對世界文明進程帶來了多方面的、深刻而長遠的、戰略性的影響。
戰爭和政治的需要,使大規模核能的釋放首先以武器形式實現
20世紀中期,以核武器研制成功為標志的震撼世界的核能釋放,在軍事、政治、外交、科技等領域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核裂變發現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全面爆發,武器成了當時人們最需要的東西。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核技術被率先應用于發展核武器,出現了一系列驚世的新概念:原子彈、氫彈、核武器;核試驗、核潛艇、核導彈;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接著又出現了核威脅、核威懾、核戰略、核擴散與核軍備控制等概念。
人們在認識核能作用空前巨大的同時,也認識了它巨大的破壞殺傷力。理智的科學家從一開始就提出了反對制造核武器,政治的需要與科技能力的結合使其很快成為現實。1964年,中國首先提出了“無核武世界”的思想,誠懇表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致力于全面禁止和銷毀核武器。
世界范圍內“禁核試”和“核不擴散”步履艱難,在“無核武”這個理想世界未實現之前,我國保持有限核力量有效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我國從一開始就制定了“不比數量,要爭質量;適合國情,可以承受;不背包袱,持續發展;戰略威懾,可靠有效”的“一點兒”發展方針,這就使兩彈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相一致,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高效的發展道路。
盡管核武器的存在使人類難以擺脫核戰爭的陰影,但一些國家還是不愿放棄核武器,并且存在著核擴散的現實危險。今天的人類還需要一個很長歷史時期的進步,才能進入真正的“生態文明”乃至“大同文明”,到那時,人類將遠離核武,核能將只用于為人類造福。
核能的和平利用,進入“穩中求進”的新常態
核武器成功研制后不久,各國紛紛推進了核能的和平利用,核技術得到廣泛應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顯著。
銅仁春旱不多,一般不影響花生適期播種、正常出苗和幼苗生長。但夏季伏旱多有發生,大面積種植花生區應加強基礎設施,做到能排能灌,同時,加強空中水資源開發利用,政府主導做好人工干預天氣工作。
核能的應用是基礎物理研究的成果迅速轉化為工程應用的范例。全球已有20多個國家發展核電,已經建成400多座核電反應堆,積累了1.4萬堆·年的運行經
驗,為全球電力需求每年作出約14%的貢獻。同時,核動力與核技術應用成就顯著。
以歷史眼光來看,像任何工程科技領域的創新一樣,核電的發展也有一個發育成熟的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一路輕松。航空、航天的先行者,有人為成功獻出了生命;馴服核能,也不免付出代價和犧牲。當然,核電畢竟有它的特點,一旦出現事故,其后果具有擴散性和后效性,因此要格外慎之又慎,安全應該是核電文化的核心。
核電在發展的幾十年歷程中,曾發生過三哩島、切爾諾貝利和福島三次核事故,特別是切爾諾貝利和福島核事故,陡增了對核電安全性與環境后果的質疑和擔心,重挫了核電發展的勢頭;同時,這些事故也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對事故的認真、深入分析,將帶來核電安全技術和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駕馭核能才是核安全的根本之道。
需要意識到,福島核事故后核電的發展已進入“穩中求進”的新的常態:
1)核電發展的速度會適度放慢,“百年大計,安全第一”,對核電安全更多投入,會使核電發展的步伐更穩健。
2)面對資源、環境的制約和能源需求,具有潔凈、高效、穩定、高能量密度等特點的核電,是綠色、低碳能源的戰略選擇之一。人類不可能放棄核能的和平利用。在中國的電力結構中,核能的占比將逐步從小到大,成為一個非化石能源的支柱產業。
3)無論是沿海還是內陸,核電都要切實做到安全。穩扎穩打,核電廠發生事故的概率會進一步降低,在事故工況下,對造成環境和社會后果的可控能力會進一步加強,做到實際可控。經過持續、堅韌、細心的努力,全社會對發展核電的信心會逐步提升。
4)核電的發展方式需要轉型,以適應福島核事故后的新的常態:完善、改進體制機制,使國家利益最大化;核行業內部增強合力,更好統籌、協調、配合;完善科學、民主、信息透明的決策程序,公眾不僅是科普的對象,更應成為參與的主體之一,從頭參與立項的醞釀、溝通和論證。建立政府主導,公眾、企業、專家協同的,責、權、利清晰的發展方式,對項目的科學性及利益與效益達到高度共識,是核電平穩發展的基礎。
5)加強我國核能發展的戰略謀劃,在發展戰略的指導下,制定近、中、長期的發展規劃,其中包括加強我國核電的基礎性和應用性研究,使我國核能科學技術逐步走上國際先進乃至領先水平。
6)認真謀劃核電全產業鏈條(從前端到后端,包括最終核廢物處置)各環節的統籌、協調發展。這不僅是長遠的、全局的需要,也有利于當前“理性謀共識,科學謀發展”,引導我國乃至世界核電進入一個健康發展的新的常態。
創新驅動,創造核能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發現和利用,使人類由農耕文明進入了工業文明階段,而人類從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的過程,也必將伴隨著能源的變革與發展。
百年展望,非化石能源必將逐步成為主導的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將會共同為此作出貢獻。
從核裂變能走向未來的可控核聚變,將是一個科學的發展方向和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要努力加大新概念、新堆型、新材料研究力度,并通過檢驗和選擇,逐步走向成熟和自主化制造后,才能進入實際應用和批量建設。核能將在更堅實的科技基礎、制度基礎、文化基礎和社會基礎之上走向未來。
未來能源應該是體現人類智慧的新形態。中國人有智慧創造安全高效核能發展的中國道路,并為人類能源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Historical View on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DU Xiang-wan
注:杜祥琬,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多哈氣候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本文整理于2013年中國核學會學術年會杜祥琬院士的題為《核能發展的歷史觀》大會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