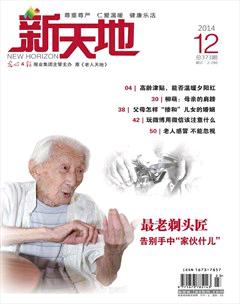大師筆下的“文化大躍進”
張天行
提起大躍進,一些論著對它的進程的描述是: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糧食“放衛星”,最后是大饑餓……
我有時想,在這一過程中,文化學術界除了為工農業生產領域的“大躍進”搖旗吶喊外,有沒有自己的“躍進”呢?
“年產詩一萬首”?
看韋君宜《思痛錄》、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等書和那一時期的新聞報道,驗證了我的一點懸想。
大躍進中,韋君宜下放到張家口地區懷來縣,同全國各地一樣,這里的公社化、大煉鋼鐵等等也在熱火朝天地進行。詩人田間在這里創辦“詩傳單”,不但他寫,而且把所有村干部、社員都拉進去寫詩,韋君宜等下放干部,負責給人們改詩,還得自己做詩,坐在那里,一會兒一首,真正是順口溜,從嘴角順口就溜出來了。什么“千日想,萬日盼,今日才把公社建。七個鄉,成一家,社會主義開紅花”,可謂詩歌泛濫。
“詩傳單后來鉛印了,還編成集子拿到石家莊出版了,并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后來,這一場詩歌運動越鬧越大。鬧到在火車上每個旅客必須交詩一首,鬧到制定文學創作規劃,各鄉提出評比條件。這個說‘我們年產詩一萬首,那個說‘我們年產長篇小說五部、劇本五部……挑戰競賽。最后,張家口專區竟出現了一位‘萬首詩歌個人,或曰‘萬首詩歌標兵。他一個人在一個月里就寫出了一萬首詩!當然,我們誰也沒見過他的詩。只聽說他的創作經驗是,抬頭見什么就來一首詩。譬如出門過鐵路見田野、見電線桿……都立即成詩。寫成就投進詩倉庫——一間空屋。后來聽說這位詩人寫詩太累,住醫院了。說文藝可以禍國殃民,我們常不服氣。而像這樣辦文藝,真可謂禍國殃民,誰也不能說是假的。”(韋君宜《思痛錄》第60頁)
“人們的頭腦好像都發昏了”
基層縣、鄉的情況是這樣,大城市的高等研究機構該理性些吧?也不樂觀。
北京,“各單位都開大會,規定自己的指標,各單位之間互相競賽,看誰的指標定得高。高指標叫‘放衛星。科學院的各個研究所在一塊開會,每個所都報告自己的指標,指標是以字數計算。一個單位說,我們的指標是一年出一千萬字。另一個單位就說,我們一年出一千二百萬字 。那個單位又一合計,說我們再加二百萬字,共一千四百萬字!這樣步步高升,好像打擂臺一樣……真是你追我趕,可惜所追趕的并不是實際上的產品,而是紙面上的數字。有些研究所報的指標,也還有些依據,可是有些指標,完全沒有依據,既沒有積存的舊稿,也沒有在計劃中的新稿,只是隨便報數字,以多為貴。反正無論報多少,并不要當場兌現。”
“有一個研究所報告說,他們的翻譯人員,產量最高,每人每天能翻譯八萬字。大家心里懷疑,要求當面表演。話已經說出來了,只得定期表演。結果證實,無論怎么樣也翻譯不出八萬字,就是抄寫八萬字也是不可能的。”(馮友蘭《三松堂自序》166~167頁)
馮友蘭沒有說自己當時的情況,著名哲學家金岳霖晚年回憶,那時已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規定每天要寫多少多少字,有些緊張。
多么生動的記述!人們的頭腦好像都發昏了,什么創作規律都可以漠視,什么高峰都可以跨越,就是超越李白杜甫李賀又有何難?別以為那時不可能提出這樣的目標,一個地方就提出,“至少要在每個縣涌現出30個魯迅”呢。
當時有位詩歌標兵一上來擺的架子就已超過了李賀,據我所知,李賀是只有一個布袋收藏詩稿,而他開始就備了一間空屋!詩人寫詩太累而住進醫院,實在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
尊重常識就是尊重規律
凡事都有規律,就以種地來說,這是要一锨一鋤辛勤勞作,一畝地有多少收獲,農民的估量八九不離十,再大膽想象,也不會想出畝產上萬乃至十幾萬斤;文化產品,一般來說比物質產品的生產更復雜,需要較長時間的學習積累、潛心錘煉,精品更是不能多產,是不能以人海、金錢刺激等方式來推動的,更不能弄虛作假。
漠視規律,土法煉鋼,得到的是一堆堆廢渣;畝產過萬斤,用不多久等人們餓肚子時,才猛醒那是虛幻的想象和造假;文化產品呢?看什么寫什么,“年產萬首”,先不說目標是否可以達到,得到的也多是類乎于廢渣的東西,留在人們口中心中的有幾句?不用說一個縣,幾十年下來,全國又涌現出幾個魯迅呢?
發動“大躍進”,原本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實現中國經濟的躍進式發展,結果事與愿違,非但沒有達到這樣的目的,反而付出慘痛的代價,延宕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留下了血的深刻教訓。
這些往事過去幾十年了,但仍然可以作為一面鏡子,和現實生活中的一些現象結合起來看,就更耐人尋味。研究“大躍進”的史學家,實可于這方面有更系統的描述和深入研究。重溫一下,會起到一點清涼劑的作用。
我們當然要推動經濟、文化學術的大發展,躍上新的臺階,但一定不要忘記,尊重常識,努力認識并抓住各行業發展的規律,循之而行,才會有我們希望得到的結果。
(責編:蕭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