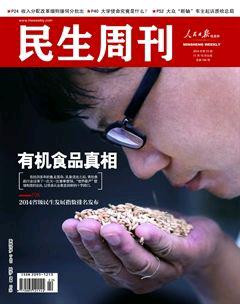“生態第一村”有機種植路
王麗 羅燕

在中國每10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會派出一個代表,來看看留民營是怎么回事。
“歡迎您來到中國生態農業第一村——留民營。”導游孔雪梅以這樣的開場白向來訪的百余名外國游客介紹道,由此“留民營村生態之旅”正式開啟。
28年前,北京大興區的留民營村獲得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授予的“全球人類生態環境500佳”,一躍成為世界生態農業新村的典范。作為國內最早一批自發從事有機農業生產的基地,留民營至今依然保存著鄉村有機農業發展清晰而典型的歷史圖譜。
很少有村莊像留民營這樣與中國生態農業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自今年4月“世界最嚴”的有機產品認證管理辦法實施以來,留民營的情況如何?記者帶著疑問走訪了這個“生態第一村”。
留民營變遷
10月31日,記者來到留民營村,正趕上一群遠道而來的德國農業專家,他們專程來這里參觀生態農業循環系統。村民們對這種場面顯然習以為常了,接待者都操著較為流利的英語。無疑,這樣的場景在今天的中國農村仍不多見。
耕地少、既不耐旱又不耐澇的留民營村,自古就是中國農村貧窮村落的代表。1969年,張占林接任村支書,“集體化的留民營村”顯示出巨大力量。全村千余畝地被分割成百余塊兒,分散在溝壑間。張占林帶領村民將這些溝、坡進行改造,使之連在一起,變成能夠產糧的良田。
老一代留民營人這樣描述那段歲月:天不亮就上工,直至天黑才收工,這樣周而復始,從1969年勞作到1982年。在此期間,這個200余人的小村莊,平坡填溝造地近2000畝,不僅養活了自己,還年年為國家交糧。通過這樣的原始積累,村民們過上了“田成方,樹成行,渠成網,家家住上排子房”的幸福生活。
不僅如此,村里還為各戶配置彩電、洗衣機、電風扇、太陽灶,建起了沼氣池、太陽能浴室。到1982年,其集體固定資產200多萬元,年收入59萬元,人均年收入3000余元。這個華北平原鹽堿地上的“光棍兒村”,變成了京郊有名的“六有村”。
集體帶給了村民們實實在在的優越感。在1982年全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際,留民營沒有響應上級“指示”走“分田到戶”的道路,在張占林的帶領下,繼續堅持走統一經營的道路。
就在那一年,北京市環保科學研究所的專家們來到留民營進行考察。發現這里具備生態農業實驗的樣板價值。就這樣,一次絕好的發展機遇“降臨”到留民營。
此后的幾年中,留民營重點發展林木種植、畜牧養殖,開發新能源。以沼氣為中心,組成了農、林、牧、漁完整的鏈式生態系統。用秸稈喂養牲畜,產出肉和奶,然后用禽畜糞便制造沼氣,沼液、沼渣當肥料再回到農田中去,如此往復循環。
生態農業的樣板效應注定使這個小村莊不會平靜。1987年6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授予留民營“全球人類生態環境500佳”,自此留民營被譽為“中國生態農業第一村”。從這一年開始,留民營先后接待國內游客百余萬人次,也就是說,在中國每10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會派出一個代表,來看看留民營是怎么回事。
作為中國農村生態農業的樣板,留民營“紅火”了13年。進入20世紀的最后10年,全國各地涌現招商引資潮,在這股潮流中,留民營迷失了自己。生態農業的道路被中斷,取而代之的是鄉村工業化。通過招商引資,留民營也辦了幾家村企。然而,這些企業并未給留民營帶來預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有機種植時代
痛定思痛的留民營,2000年前后才又重新回到發展生態農業的道路上來。這個曾經的“生態第一村”,生態農業的發展已被擱置了整整10年時間。
隨著現代社會對食品健康的要求越來越高,確保食品安全成為重要公共衛生議題。在保護環境和食品安全這兩大主題的雙重驅動下,有機農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再次出發的留民營順勢將效益低下的工業化企業成功剝離,組建了北京青圃蔬菜公司,在原有的生態系統基礎上,對1500畝土地進行有機蔬菜的開發和生產。
2002年,北京青圃60多個品種的有機蔬菜通過原國家環保總局有機食品發展中心的有機食品認證。2003年,原國家環保總局印發了《國家有機食品生產基地考核管理規定(試行)》。留民營通過考核,成為國內最早一批自發從事有機農業生產的基地。
在國內有機農業發展的起步階段,北京青圃所獲得的顯然不僅僅是加工利潤,還有“緊俏商品”的市場空間。2006年,留民營有日光溫室180棟,年產有機蔬菜3800噸,年銷售2000余萬元。除此,留民營還是荷蘭阿姆斯特丹“世界有機種植者大獎”的獲得者。
隨著外界熱錢的涌入,中國的有機農業進入到快速發展階段。數據顯示,2006年,私募股權機構投資于有機農業項目的金額僅為0.56億美元;而2007年,這個數字猛然增長至3.96億美元;到2010年,其投資金額達14.89億美元,這一年的投資金額超過了前四年的總和。
與此同時,一些未曾涉獵過農業的大佬們也紛紛進入,中國有機產品的市場份額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長。匯源果汁的朱新禮在京郊密云區運作1.5萬畝的有機區域,聯想控股的柳傳志成立佳沃集團,期冀打造一個全產業鏈的食品加工場,萬達集團的王健林也在京郊延慶布局有機蔬菜種植。
不過,與巨頭們的有機產品相比,以北京青圃為代表的第一批有機蔬菜種植者已占據市場先機。它的有機蔬菜通過70家大型超市進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公司規模一度達400余人。此時,距北京1500公里以外,從事有機蔬菜種植的上海多利農莊也開始嶄露頭角。
2010年前后,有專家宣稱中國農業已經進入“有機種植時代”。2012年8月,為迎接“新時代”的到來,北京青圃與上海多利農莊展開合作,希望在高品質的有機蔬菜市場占得先機。
“北京青圃” 的迷惘
相比于北京青圃和多利農莊提出“雙方攜手,互惠共贏”的設計理想,現實展現出的卻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種走向,雙方合作11個月后就不歡而散。北京青圃一位負責人用“兩敗俱傷”來形容合作失利的影響。
不過,兩者在合作初期有過短暫的“蜜月期”。在多利一系列市場推廣活動后,來留民營購買、參觀有機蔬菜的消費者太多,乘坐的車輛一度要停在村外。
村口一家飯店的老板對于當初的盛況印象深刻。那時,他家店里客人幾乎天天爆滿,廚師由3人增至6個也無法滿足需求。他一度曾想過要開個分店。
飯店老板至今沒有弄清楚兩者是如何走到“分手”的地步,他也不會知道,除了早期涉足有機行業的公司陷入瓶頸期外,巨頭們在有機農業上的布局也并不順利。
匯源集團自2008年注資有機農業近10億元至今尚未盈利,虧損由其他項目的補貼維持。萬達集團打造的有機農業園,所產綠色食品目前沒有對外銷售。
業內人士認為,無農業經驗的企業,只看到了市場的前景,卻忽略有機農業是一個高門檻、投入大、短期盈利不易的產業。而多利與北京青圃合作的失敗,則在于二者在管理模式及營銷理念上沒有融合。
該業內人士舉例,多利農莊在進入留民營后,照搬在上海的“自營模式”。除了土地、工人來自留民營外,其管理團隊、銷售團隊都從上海調配。“這其實需要高成本投入,一旦協調不好雙方的利益關系,整體執行力很容易出問題”。
這一觀點也得到北京青圃技術員孔慶偉的認可,他用“不接地氣”來形容多利農莊在留民營實行的管理模式。“這邊我們種植的黃瓜眼看要出棚,那邊多利的人還繼續從上海空運黃瓜,沒人告訴我們這是為什么”。
除了企業自身的因素外,有機產業面臨的諸多問題也不容忽視。
據中國農科院最新一份報告《中國發展有機農業機遇、問題及對策》認為,國家雖然大力推進無公害食品和綠色食品產業的發展,并向農民提供金融支持以便他們轉變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但對于有機農業的發展并沒有實質性的政策、資金、科研技術投入。
孔慶偉稱,從事種植有機蔬菜近10年,病蟲害和土壤肥力保持是限制有機農業產量提高的根本原因,也是多數從事有機種植企業面臨的突出問題,“有時遇到蟲害,根本就不知道該找哪家科研機構幫助,只能用土辦法”。
與多利農莊“分手”后,北京青圃有機蔬菜種植道路并不順利。因市場遇冷、銷售渠道受阻,其品牌影響力大不如從前,目前只為北京若干家飯店提供產品,規模也縮減到380畝,年均銷售額維持在百余萬元。
市場遇阻,加上國內有機認證復雜,北京青圃打算走出口道路。然而,出口市場競爭激烈,企業想要進入也并不容易。
北京青圃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