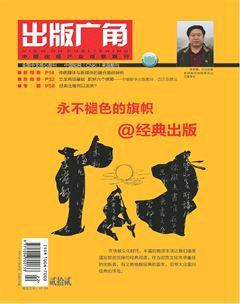經(jīng)典出版何以流失?
王曉生

出版的流失不等于經(jīng)典閱讀的流失。新經(jīng)典的海量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沖擊老經(jīng)典出版的流失,大量娛樂(lè)形式的存在一定會(huì)沖擊包括經(jīng)典閱讀在內(nèi)的紙質(zhì)閱讀,電子閱讀的長(zhǎng)期熏陶也會(huì)造成讀者強(qiáng)烈的“淺閱讀”習(xí)慣,而并非排斥紙質(zhì)的經(jīng)典閱讀。
從理論上說(shuō),經(jīng)典并不是說(shuō)不清楚的事情。“經(jīng)”本為織物之縱線。清段玉裁《說(shuō)文解字》注:“織之縱絲謂之經(jīng)。必先有經(jīng)而后有緯。”從而“經(jīng)”從經(jīng)線引申為“重要”“典范”,又再引申為重要著作。我國(guó)古代圖書(shū)分類(lèi)有“經(jīng)、史、子、集”之說(shuō),“經(jīng)”指儒家重要著作,無(wú)論是漢前《五經(jīng)》《六經(jīng)》,還是后來(lái)的《九經(jīng)》《十三經(jīng)》,都是如此。中國(guó)最早的歷史書(shū)《尚書(shū)》中有“惟殷先人,有冊(cè)有典”。甲骨文中的“典”字像簡(jiǎn)冊(cè)連編之形。《說(shuō)文解字》:“典,大冊(cè)也;典,五帝之書(shū)也。”可見(jiàn),歷史上很早的時(shí)期,“典”就有了“經(jīng)典冊(cè)籍”之義。“經(jīng)”和“典”合在一起,其多重含義之大端是“恒久而重要之典范”,即劉勰《文心雕龍·宗經(jīng)》所謂“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然而,理論歸理論,一旦進(jìn)入具體作品的品衡,何為經(jīng)典,又是一個(gè)讓人頭疼的問(wèn)題。要回答此,首先要認(rèn)真思考:經(jīng)典是一座座凝固的歷史豐碑,還是一條條無(wú)定的奔騰河流?
一、江山代有經(jīng)典出
誰(shuí)都知道《易經(jīng)》《詩(shī)經(jīng)》《論語(yǔ)》《道德經(jīng)》《史記》等屬于中國(guó)經(jīng)典,《圣經(jīng)》《古蘭經(jīng)》《理想國(guó)》《莎士比亞文集》等屬于外國(guó)經(jīng)典。沒(méi)有哪個(gè)時(shí)代的研究者不如此認(rèn)為,也沒(méi)有哪個(gè)國(guó)家的研究者不如此認(rèn)為。從理性的直覺(jué)來(lái)說(shuō),似乎經(jīng)典就是那些“凝固”的經(jīng)典作品。對(duì)于這個(gè)思維前提,必須加以認(rèn)真思考,因?yàn)椤敖?jīng)典出版的流失”這樣的問(wèn)題與此思維前提緊密相關(guān)。只有經(jīng)典是“凝固”的,才有“流失”一說(shuō);如果經(jīng)典本身都是“流動(dòng)”的,何來(lái)“經(jīng)典出版流失”一說(shuō)?是不是果真如此:出版是“鐵打的營(yíng)盤(pán)”,而經(jīng)典是“流水的兵”?要回答這個(gè)問(wèn)題,還需一點(diǎn)歷史眼光。
在中國(guó),《詩(shī)經(jīng)》是經(jīng)典早已是定論,其已成為如今大學(xué)中文專(zhuān)業(yè)必讀的重要經(jīng)典。但其實(shí)古代早有“不學(xué)《詩(shī)》,無(wú)以言”的說(shuō)法。這里的《詩(shī)》就是《詩(shī)經(jīng)》。要知道,《詩(shī)經(jīng)》也有個(gè)搜集整理,以及孔子刪改的過(guò)程。這個(gè)過(guò)程其實(shí)就是經(jīng)典生成的過(guò)程。屈原之《離騷》在漢前并未有大影響,何談經(jīng)典?從兒童啟蒙讀物來(lái)說(shuō),《弟子規(guī)》《增廣賢文》長(zhǎng)盛不衰,《三字經(jīng)》《千字文》默默流傳,而《女兒經(jīng)》《孝經(jīng)》則已失現(xiàn)實(shí)光澤,社會(huì)不斷發(fā)展,經(jīng)典必然不斷更新。俗話說(shuō),一代有一代之文學(xué),唐詩(shī)、宋詞、元曲、明清小說(shuō)不斷更迭,其實(shí)質(zhì)就是新的經(jīng)典不斷涌現(xiàn)。《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巖》等紅色經(jīng)典,只有紅色的時(shí)代才能鑄就。莫言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又通過(guò)一種世界性的評(píng)獎(jiǎng)體制使得其作品獲得更加牢固的經(jīng)典位置。“江山代有經(jīng)典出,各領(lǐng)風(fēng)騷數(shù)百年”,這用來(lái)描述經(jīng)典的生成也許非常準(zhǔn)確,因?yàn)榻?jīng)典永遠(yuǎn)是歷史生成性的。
不光文學(xué)經(jīng)典如此,繪畫(huà)、書(shū)法、戲劇等領(lǐng)域其實(shí)都莫不如是。中國(guó)繪畫(huà),無(wú)論是黃家富貴派、徐家野逸派,還是浙江畫(huà)派、吳門(mén)畫(huà)派、嶺南畫(huà)派,或者是揚(yáng)州八怪、畫(huà)中九友,都是繁花滿枝,經(jīng)典各異;中國(guó)書(shū)法,籀、篆、分、隸、行、草,輾轉(zhuǎn)相變,經(jīng)典互輝;中國(guó)戲劇,南戲、昆曲、京劇、黃梅,諸趣紛登,經(jīng)典遞擅。試問(wèn),經(jīng)典難道是固定的嗎?答案應(yīng)該再清楚不過(guò)了。
有了這種認(rèn)識(shí)格局,就不難回答:《三言兩拍》是經(jīng)典,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悟空傳》也有可能成為經(jīng)典。法國(guó)杜尚將小便兜一放,就成了20世紀(jì)偉大的實(shí)驗(yàn)藝術(shù),被譽(yù)為“現(xiàn)代藝術(shù)的守護(hù)神”。作為挑釁經(jīng)典的小便兜,自己也成了經(jīng)典。經(jīng)典往往是在挑釁中生成的,又何談經(jīng)典的固定?經(jīng)典秩序構(gòu)成的游戲永遠(yuǎn)處于成員的進(jìn)進(jìn)出出之中。老經(jīng)典可以變?yōu)榉墙?jīng)典,新經(jīng)典可以變?yōu)槔辖?jīng)典,而非經(jīng)典也可以變?yōu)樾陆?jīng)典。這種轉(zhuǎn)變的動(dòng)力來(lái)自歷史語(yǔ)境、讀者趣味、現(xiàn)實(shí)偶然三者組成的綜合張力。經(jīng)典永遠(yuǎn)是歷史性的,離開(kāi)了歷史也就沒(méi)有經(jīng)典可談。因此,經(jīng)典也永遠(yuǎn)是當(dāng)下的,離開(kāi)了當(dāng)下,經(jīng)典也就沒(méi)有任何現(xiàn)實(shí)可言。
2009年10月啟動(dòng)的“經(jīng)典中國(guó)國(guó)際出版工程”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腳。這項(xiàng)國(guó)家開(kāi)展的為有效推動(dòng)中國(guó)圖書(shū)“走出去”的重點(diǎn)工程,資助重點(diǎn)包括《中國(guó)學(xué)術(shù)名著系列》和《中國(guó)文學(xué)名著系列》兩類(lèi)。“經(jīng)典中國(guó)國(guó)際出版工程”工作承擔(dān)著“講好中國(guó)故事、傳播好中國(guó)聲音”的重任。自2009年第一期項(xiàng)目評(píng)審和實(shí)施以來(lái),“經(jīng)典中國(guó)國(guó)際出版工程”已累計(jì)資助2000多種圖書(shū)。據(jù)統(tǒng)計(jì),這2000多種圖書(shū)中,基本都是“當(dāng)下經(jīng)典”。經(jīng)典的生命永遠(yuǎn)處于死死活活之中。它的死活不是由自己決定,而是由歷史或者當(dāng)下的藥性決定。經(jīng)典活在他者之中。在這個(gè)意義上,經(jīng)典是卑躬屈膝的,活得非常可憐。這也注定,經(jīng)典俱樂(lè)部永遠(yuǎn)是開(kāi)放性的。如果果真如此,我們又何必?fù)?dān)心經(jīng)典出版的流失?
二、經(jīng)典出版的波浪效應(yīng)
既然如此,是不是就沒(méi)有必要談?wù)摗敖?jīng)典出版流失”這個(gè)問(wèn)題?那也不是。因?yàn)樵谝欢ǖ臅r(shí)空范圍內(nèi),甚至在很長(zhǎng)的一段時(shí)間內(nèi),經(jīng)典還是具有相對(duì)固定性的。否則,何來(lái)中國(guó)古典四大名著之說(shuō)?在一定的時(shí)空中,關(guān)于某事物的概念具有相對(duì)固定的內(nèi)涵和外延,這是概念得以成立的前提。經(jīng)典之概念也是如此。
人類(lèi)有記載的文字歷史只有短短的幾千年,我們文化認(rèn)識(shí)論上的時(shí)空是確定的。生存于這個(gè)時(shí)空中的群體,如果不糾纏于哲學(xué)性的抽象爭(zhēng)辯,而把經(jīng)典定義為獲得廣泛認(rèn)同的具有重大和恒久意義的古典文本,那么“經(jīng)典出版流失”這樣的命題是成立的。雖然我們很難對(duì)經(jīng)典出版流失這樣的問(wèn)題進(jìn)行定量分析,因?yàn)槿狈ο嚓P(guān)的權(quán)威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但是很容易根據(jù)經(jīng)驗(yàn)判斷而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經(jīng)典作品出版越來(lái)越少了,即使上了架,賣(mài)得也越來(lái)越少。是讀者越來(lái)越傻了,還是傳統(tǒng)經(jīng)典越來(lái)越?jīng)]有魅力了?或者兩者都是,或者兩者都不是?面對(duì)這個(gè)“死結(jié)”,我們必須找到新的解釋模式。
經(jīng)典之所以為經(jīng)典,就是因?yàn)槠渲刑N(yùn)含著解答人類(lèi)基本問(wèn)題的價(jià)值觀。經(jīng)典蘊(yùn)含的價(jià)值觀的有效傳播,是經(jīng)典發(fā)揮效用的明證。經(jīng)典讀的人越多,其價(jià)值效用也就越大。對(duì)一個(gè)文化使命感強(qiáng)烈的知識(shí)人來(lái)說(shuō),經(jīng)典的傳播像“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一樣,是最熱盼的事情。然而在當(dāng)下這個(gè)時(shí)代,這一定是不可能的。于是很多人心急如焚,“讀者不古、品位低下”之類(lèi)的咒語(yǔ)就接連不斷。在他們心目中,我們的前輩大概是天天手捧經(jīng)典日夜誦讀。然而,這一點(diǎn)是不是一個(gè)真實(shí)的判斷?在筆者看來(lái),這值得我們認(rèn)真探討。“貴古賤今”式的思維,雖然是人類(lèi)的共同特點(diǎn),但在中國(guó)人身上好像特別嚴(yán)重。但在經(jīng)典面前,當(dāng)今的讀者是不是比百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讀者更加懶惰不堪,我們很難給出有說(shuō)服力的正面或者反面的論證。對(duì)此,每個(gè)人都似乎有自己的事實(shí)判斷。在這里其實(shí)沒(méi)有必要給出一個(gè)“在經(jīng)典面前今人更加勤奮或者懶惰”的答案。退一步說(shuō),即使當(dāng)下我們讀原始經(jīng)典少了,經(jīng)典所蘊(yùn)含的價(jià)值傳播效果就必然差之十萬(wàn)八千里嗎?答案是否定的,這還得從經(jīng)典傳播的波浪效應(yīng)說(shuō)起。
如果把經(jīng)典比作閃閃發(fā)光的寶石,那么其價(jià)值在受眾中的傳播就會(huì)呈現(xiàn)一種多層級(jí)效應(yīng)。這種效應(yīng)的層級(jí)是無(wú)窮的,不過(guò)越在內(nèi)圈影響力越強(qiáng)大,越在外圈影響力越小,最終趨于消失。波浪效應(yīng)是對(duì)經(jīng)典傳播這種特征的最好概括。不過(guò)要特別加以說(shuō)明的是,傳播圈與傳播圈之間構(gòu)成的影響關(guān)系,并不一定要經(jīng)典自身的存在,還可以通過(guò)某種間接物而發(fā)生效用。李零以講課筆記為基礎(chǔ),撰述“我們的經(jīng)典”系列,包括《去圣乃得真孔子:〈論語(yǔ)〉縱橫讀》《人往低處走:〈老子〉天下第一》《唯一的規(guī)則:〈孫子〉的斗爭(zhēng)哲學(xué)》《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對(duì)四大古代典籍《論語(yǔ)》《老子》《孫子》《周易》進(jìn)行解讀。人們閱讀李零的作品,其實(shí)也就是在接受四大典籍的影響。對(duì)于普通大眾來(lái)說(shuō),也許一些人根本沒(méi)讀過(guò)《論語(yǔ)》,但是他們非常喜歡于丹的《百家講壇》,那么《論語(yǔ)》的精神價(jià)值得到傳播了嗎?是不是可以說(shuō),這種現(xiàn)象是《論語(yǔ)》的一種“電視形態(tài)”的出版方式?京劇演員在臺(tái)上演繹傳統(tǒng)劇目可以加入自己的創(chuàng)造而使其成為“自己的作品”,這是經(jīng)典的另外出版形式。經(jīng)典的出版一定是多元形式的。可以說(shuō),經(jīng)典出版流失這樣的問(wèn)題往往忽視了經(jīng)典的新的出版方式。經(jīng)典的出版方式不只“元典”一種,還可以是“改編版”的、“注釋版”的、“演繹版”的、“廣播版”的、“電視版”的,也可以是“網(wǎng)絡(luò)多媒體版”的。這種多元出版之間構(gòu)成價(jià)值相互傳遞的關(guān)系,從而組成多層的波浪圈。現(xiàn)代受眾生活在各種經(jīng)典多元出版的環(huán)境中,接受光怪陸離的經(jīng)典映射,誰(shuí)又能說(shuō)是經(jīng)典的流失?這種現(xiàn)象說(shuō)是經(jīng)典的流失可以,說(shuō)是經(jīng)典的多元生發(fā)也未必毫無(wú)道理。
三、經(jīng)典出版流失的原因
如果我們把經(jīng)典的接受狹義地定義為直接的元典閱讀,那么經(jīng)典出版流失是必然的結(jié)果。那是什么造成了這種經(jīng)典出版流失現(xiàn)象的呢?
首先,造成流失錯(cuò)覺(jué)的一個(gè)重要原因是,非購(gòu)買(mǎi)性閱讀大量存在。非購(gòu)買(mǎi)性閱讀包括兩種形式:電子免費(fèi)下載閱讀和圖書(shū)館免費(fèi)閱讀。中國(guó)讀者缺乏付費(fèi)電子閱讀習(xí)慣,這反過(guò)來(lái)造成電子內(nèi)容提供商盡量提供免費(fèi)電子讀物。免費(fèi)電子經(jīng)典讀物的存在必然造成紙質(zhì)經(jīng)典出版流失的后果。隨著大學(xué)入學(xué)比例的大大提高,很多年輕人可以在大學(xué)圖書(shū)館免費(fèi)借閱紙質(zhì)經(jīng)典讀物,自己購(gòu)買(mǎi)的必要性大大下降,紙質(zhì)經(jīng)典讀物銷(xiāo)量的下降也就成了必然趨勢(shì)。然而無(wú)論如何,這些都不能說(shuō)明經(jīng)典閱讀的大面積下滑。
其次,新經(jīng)典的大量生成,必然擠壓老經(jīng)典的閱讀。批評(píng)者往往喜歡將目光盯著幾本老經(jīng)典,而忽視大量新經(jīng)典的存在。如果把老經(jīng)典和新經(jīng)典相加,無(wú)論是經(jīng)典的出版還是閱讀,都并未呈現(xiàn)遞減趨勢(shì)。同時(shí),由于大量新經(jīng)典的加入,經(jīng)典的總量不斷膨脹,而讀者需要付出的無(wú)論是時(shí)間成本還是經(jīng)濟(jì)成本總量都是有限的,這就造成單本經(jīng)典出版的數(shù)量和閱讀的次數(shù)呈遞減趨勢(shì)。這就是為什么人們會(huì)產(chǎn)生經(jīng)典出版正在流失的印象。
再次,大量娛樂(lè)形式的存在,沖擊了讀者的閱讀興趣。科技的進(jìn)步帶來(lái)了無(wú)窮的娛樂(lè)形式,可以說(shuō)我們已經(jīng)進(jìn)入娛樂(lè)時(shí)代。在太平盛世中,人類(lèi)的娛樂(lè)沖動(dòng)一定會(huì)得到最高強(qiáng)度的喚醒。娛樂(lè)的本質(zhì)是游戲,游戲精神是人類(lèi)的原始本能。在一個(gè)人們不斷慨嘆紙質(zhì)閱讀大量減少的時(shí)代,要求紙質(zhì)經(jīng)典閱讀也許是一種奢侈。
最后,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電子閱讀培養(yǎng)出來(lái)的受眾往往缺乏深度解讀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能力。傳媒理論界一個(gè)公認(rèn)的事實(shí)是:電子閱讀,包括電視和網(wǎng)絡(luò)多媒體,本質(zhì)是一種淺閱讀。這種淺閱讀長(zhǎng)期涵化的結(jié)果往往是造成“傻瓜”受眾。“傻”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不善思考,不愿思考。一個(gè)是腦子不好使,一個(gè)是缺乏閱讀進(jìn)取心。這必然導(dǎo)致一種人們遠(yuǎn)離經(jīng)典的趨向。
經(jīng)典出版流失這樣的問(wèn)題也許是一個(gè)偽命題,因?yàn)槭裁词墙?jīng)典往往不好界定。經(jīng)典的秩序呈現(xiàn)一種時(shí)強(qiáng)時(shí)弱的流動(dòng)性,經(jīng)典的成員有進(jìn)有出。正因如此,經(jīng)典出版流失的問(wèn)題并不好回答。不過(guò)不得不承認(rèn),在一定的時(shí)空范圍內(nèi),經(jīng)典的認(rèn)定還是相對(duì)固定的。從這個(gè)基礎(chǔ)上看,傳統(tǒng)經(jīng)典出版的流失是某種客觀事實(shí)。然而出版的流失不等于經(jīng)典閱讀的流失,新經(jīng)典的海量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沖擊老經(jīng)典出版的流失,大量娛樂(lè)形式的存在一定會(huì)沖擊包括經(jīng)典閱讀在內(nèi)的紙質(zhì)閱讀,電子閱讀的長(zhǎng)期熏陶也會(huì)造成讀者強(qiáng)烈的淺閱讀習(xí)慣,而并非排斥紙質(zhì)的經(jīng)典閱讀。
(作者單位:中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