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shù)字化時代圖書館信息資源版權(quán)使用優(yōu)化創(chuàng)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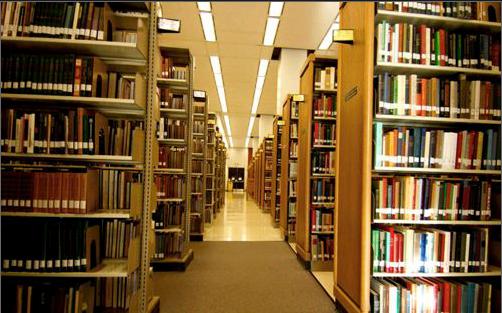
[摘要]作為公益性機(jī)構(gòu),圖書館在傳播信息、促進(jìn)信息公平等方面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大規(guī)模數(shù)字化時代,繼續(xù)沿用傳統(tǒng)版權(quán)管理機(jī)制,無疑會給著作權(quán)人造成實質(zhì)性的損害,不利于著作權(quán)人的創(chuàng)作積極性。如何創(chuàng)新版權(quán)管理機(jī)制,以更為積極和高效的方式使用版權(quán),為讀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wù),是數(shù)字化時代圖書館生存和發(fā)展的關(guān)鍵。
[關(guān)鍵詞]數(shù)字化;圖書館;版權(quán);版權(quán)管理;公共利益
[作者單位]惠青,河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圖書館。
[基金項目] 2014年保定市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研究項目“駐保高校圖書館為保定市弱勢群體服務(wù)研究(項目編號:20140255)”,2013年河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社科基金項目“高校圖書館信息資源整合與利用研究(項目編號:SK201314)”的研究成果。
近年來,屢有圖書館陷入版權(quán)糾紛。為何以公益為宗旨的圖書館,一時間會成為眾矢之的,著作權(quán)人又為何屢屢和圖書館較勁?筆者研究調(diào)查后發(fā)現(xiàn),在大規(guī)模數(shù)字化時代,數(shù)字化突破了傳統(tǒng)版權(quán)作品傳播的極限,給著作權(quán)人造成嚴(yán)重的實質(zhì)性損失。從多數(shù)侵權(quán)案例來看,圖書館并未意識到自己是侵權(quán)人,究其原因是數(shù)字化創(chuàng)造出許多新型的版權(quán)作品,如數(shù)字格式、數(shù)字鏈接等。圖書館應(yīng)當(dāng)認(rèn)識到當(dāng)前版權(quán)性質(zhì)所發(fā)生的變化,同時積極思考更為優(yōu)化的版權(quán)管理機(jī)制,而不應(yīng)盲目開展數(shù)字資源業(yè)務(wù),尤其是涉足一些自身根本不了解的領(lǐng)域。
一、大規(guī)模數(shù)字化與圖書館版權(quán)困境
在數(shù)字化時代,圖書館所要面臨的版權(quán)風(fēng)險,是前所未有的。大規(guī)模數(shù)字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tǒng)版權(quán)的使用模式,從而加劇了著作權(quán)人與使用人之間的矛盾[1]。一方面,著作權(quán)人希望將傳統(tǒng)版權(quán)帶入網(wǎng)絡(luò)。另一方面,網(wǎng)絡(luò)則需要優(yōu)質(zhì)內(nèi)容,并且以最低成本的方式進(jìn)行傳播,由此完成自身的擴(kuò)張。由于雙方利益的焦點始終無法達(dá)成一致,且當(dāng)前立法明顯滯后。數(shù)字資源版權(quán)糾紛主要由兩方面因素造成:
一是版權(quán)歸屬上的不明晰。一般而言,圖書館惡意使用版權(quán)的可能性不大。圖書館開設(shè)數(shù)字資源服務(wù),是為了方便公眾。近年來,圖書館屢屢陷入版權(quán)糾紛,令圖書館在提供服務(wù)時如履薄冰,有些圖書館甚至放棄數(shù)字資源業(yè)務(wù),以避免糾紛。逃避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對于服務(wù)創(chuàng)新、提升服務(wù)質(zhì)量也是極為不利的。筆者認(rèn)為,這是由于當(dāng)前法律制度未能適應(yīng)大規(guī)模數(shù)字化時代所造成的版權(quán)權(quán)屬變化。大規(guī)模數(shù)字化時代,版權(quán)權(quán)屬人的范圍擴(kuò)大了。在傳統(tǒng)版權(quán)權(quán)屬人中,著作權(quán)人是唯一的權(quán)屬人,而在數(shù)字化時代,數(shù)字化本身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數(shù)字格式、數(shù)字鏈接等都是受版權(quán)保護(hù)的。由于圖書館未能意識到這種變化,將一些有版權(quán)的作品視為無版權(quán),從而造成侵權(quán)。隨著數(shù)字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數(shù)字產(chǎn)品的形式更為多樣,參與數(shù)字化的人都有可能成為權(quán)屬人。圖書館如果不能夠區(qū)分清權(quán)屬人,很容易陷入不必要的糾紛之中[2]。
二是權(quán)利流轉(zhuǎn)變得復(fù)雜。數(shù)字化從根本上改變了著作權(quán)人權(quán)利流轉(zhuǎn)的方式。在傳統(tǒng)模式下,版權(quán)權(quán)利流轉(zhuǎn)主要發(fā)生在著作權(quán)人和出版社之間。著作權(quán)在市場上流通變現(xiàn),通過出版社回流到著作權(quán)人身上,因此,版權(quán)糾紛主要集中在著作權(quán)人與出版社之間。大規(guī)模數(shù)字化時代,網(wǎng)絡(luò)、數(shù)字圖書館等替代了出版社,成為著作權(quán)權(quán)利流通的主體。由于復(fù)制、傳播成本幾乎為零,對著作權(quán)人的權(quán)利損害也是極為嚴(yán)重的。正是由于圖書館未能認(rèn)識到數(shù)字化所引發(fā)的這種變化,未能意識到自身所應(yīng)承擔(dān)的責(zé)任,從而在版權(quán)管理、宣傳及教育方面明顯滯后。
二、數(shù)字資源版權(quán)授權(quán)模式之弊端
在傳統(tǒng)模式下,圖書館一般只有幾個副本,以提供給普通讀者。雖然無償使用會給著作權(quán)人造成一定的經(jīng)濟(jì)損失,但是不會很嚴(yán)重。而在大規(guī)模數(shù)字化時代,數(shù)字作品可以無限復(fù)制及傳播,從而造成巨大的實質(zhì)性損害。在這種情況下,仍舊沿用“合理使用”作為豁免,對于著作權(quán)人而言,無疑是十分不公平的。如果不考慮設(shè)計新的授權(quán)模式,必然會進(jìn)一步激化著作權(quán)人與圖書館之間的矛盾[3]。
傳統(tǒng)版權(quán)授權(quán)模式主要包括直接授權(quán)模式、代理授權(quán)模式、要約授權(quán)模式、集體管理模式等。這些模式都存在一定利弊,或是由于一些客觀因素而無法實施。
第一,直接授權(quán)模式。對于著作權(quán)人及圖書館而言,直接授權(quán)無疑明確了雙方之間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但是,從實際操作來看,無疑會增加著作權(quán)人的交易成本,這對圖書館也是十分不經(jīng)濟(jì)的。國內(nèi)外很少采用這種直接授權(quán)模式。
第二,代理授權(quán)模式。代理授權(quán)模式對著作權(quán)人及出版社無疑是有利的,但是對圖書館就未必有利。根據(jù)使用協(xié)議,圖書館只能在合同有效期內(nèi)享有數(shù)字版權(quán)作品的使用權(quán),超過合同期后,圖書館需重新支付使用費用。考慮到我國當(dāng)前的國情,多數(shù)圖書館在經(jīng)費緊張的情況下維持運營,此種模式必然會剝奪多數(shù)圖書館提供數(shù)字資源,或是提供高質(zhì)量數(shù)字資源的機(jī)會,從而造成實質(zhì)性的不平等。此外,以Google圖書館為例,國外專家就擔(dān)心其一旦獲得市場壟斷地位,必然會主導(dǎo)全球數(shù)字版權(quán)作品的定價權(quán)。對于發(fā)展中國家而言,使用版權(quán)作品可能面臨巨額的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
第三,要約授權(quán)模式。要約授權(quán)模式不利于圖書館與著作權(quán)人聯(lián)系,且要約往往不明確,使用不當(dāng),容易造成版權(quán)糾紛。
第四,集體管理模式。集體管理模式是西方國家較為通行的一種做法[4]。著作權(quán)人將版權(quán)作品的使用交由專業(yè)版權(quán)機(jī)構(gòu),由專業(yè)版權(quán)機(jī)構(gòu)與圖書館進(jìn)行協(xié)商。如近期香港地區(qū)的作者以集體形式與圖書館協(xié)商,要求圖書館在超過一定使用次數(shù)后,支付額外的使用費用。集體管理不僅降低了著作權(quán)人和圖書館之間的交易成本,而且減少了中間環(huán)節(jié),防止了數(shù)字出版企業(yè)壟斷市場。但是,由于我國目前還未形成有力的集體管理組織,著作權(quán)人之間也未能達(dá)成共識,因此此種模式尚不普及。
三、圖書館版權(quán)管理機(jī)制創(chuàng)新
傳統(tǒng)意義上的版權(quán)管理主要集中在規(guī)避版權(quán)風(fēng)險上,而未能考慮到如何提升版權(quán)作品的使用效率,未能使其更好地為讀者服務(wù)。在信息化時代,一味思考如何規(guī)避風(fēng)險是相當(dāng)消極的。無論是著作權(quán)人、圖書館,還是讀者,都需要更好的服務(wù),從而實現(xiàn)多贏的局面。因此,創(chuàng)新版權(quán)管理機(jī)制,積極應(yīng)對版權(quán)困境是當(dāng)務(wù)之急。
首先,成立圖書館聯(lián)盟。在傳統(tǒng)思維中,圖書館只是一個紙質(zhì)圖書的實體存儲機(jī)構(gòu),和出版是沒有絲毫關(guān)系的。而在大規(guī)模數(shù)字化時代,圖書館必須轉(zhuǎn)型。國外圖書館為應(yīng)對Google圖書館所帶來的沖擊,實施了圖書館聯(lián)盟戰(zhàn)略,實現(xiàn)了從圖書館向數(shù)字出版機(jī)構(gòu)的轉(zhuǎn)型。從我國的國情來看,成立圖書館聯(lián)盟是非常有必要的。雖然在現(xiàn)行體制下,圖書館很難轉(zhuǎn)型為數(shù)字出版機(jī)構(gòu),但是,圖書館聯(lián)盟形成后,對于推動中西部地區(qū)的中型圖書館無疑具有積極作用。如可以采取總分館的形式,先整合地區(qū)圖書館,在適當(dāng)?shù)臅r候成立全國性的圖書館聯(lián)盟。聯(lián)盟成立后,圖書館在和數(shù)字出版機(jī)構(gòu)談判時,將獲得市場優(yōu)勢地位,可以爭取到更為合理的使用價格。盡管圖書館聯(lián)盟在短期內(nèi)無法轉(zhuǎn)變?yōu)閿?shù)字出版機(jī)構(gòu),但是可以整合聯(lián)盟內(nèi)的資源,推出特色數(shù)字化資源,如古籍善本、文史檔案等,供聯(lián)盟內(nèi)成員使用。對于促進(jìn)信息化以及打破數(shù)字出版企業(yè)壟斷而言,圖書館聯(lián)盟都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其次,提供按需印刷業(yè)務(wù)。按需印刷又稱按需出版。按需出版和傳統(tǒng)出版不同,其主要針對的是已經(jīng)出版的作品。因此,按需印刷不涉及編輯、發(fā)行等環(huán)節(jié),只是提供一個高質(zhì)量的副本。在傳統(tǒng)技術(shù)條件下,由于制版成本高額,很多有價值的書籍因市場銷路不好,最后只能靜靜地躺在圖書館的書架上。隨著歲月的流逝,一些作品保存不當(dāng),最后湮滅在時間的長河之中。在數(shù)字印刷時代,圖書館既可以利用數(shù)字技術(shù)來制作數(shù)字化的副本,也可以為讀者提供個性化的印刷需求。無論是從保護(hù),還是從傳播的角度來看,開展按需印刷都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最后,優(yōu)化數(shù)字資源的使用方式。據(jù)調(diào)查顯示,在一些信息化程度較低的地區(qū),數(shù)字資源的使用率不是很高,從而造成了極為嚴(yán)重的浪費[5]。基于這種情況,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改變當(dāng)前數(shù)字資源的使用方式。圖書館和數(shù)字出版企業(yè)簽訂協(xié)議時,應(yīng)當(dāng)采用更為細(xì)化的方式,如采用免費與收費相結(jié)合的方式。這樣既有利于降低圖書館的成本,而且有利于規(guī)避數(shù)字版權(quán)作品所引發(fā)的風(fēng)險。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管理機(jī)制創(chuàng)新都是建立在一個前提下,那就是圖書館自身的數(shù)字化。筆者認(rèn)為,數(shù)字化不僅僅是紙質(zhì)圖書向數(shù)字圖書的轉(zhuǎn)變,而是整個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的數(shù)字化。對于圖書館而言,如何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數(shù)字技術(shù),更好地為讀者服務(wù),才是在數(shù)字化時代生存和發(fā)展的關(guān)鍵。
參考文獻(xiàn)
[1] 劉茲恒,溫欣. 挪威版權(quán)延伸性集體許可制度探析——以挪威國家圖書館Bokhylla計劃為例[J]. 圖書與情報,2014(3).
[2]申慶月. 數(shù)字資源采訪版權(quán)風(fēng)險分析和防范[J]. 圖書館雜志,2014(6).
[3]韓新月,肖珂詩. 圖書館應(yīng)用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授權(quán)模式研究——挪威“數(shù)字書架”項目對我國圖書館的啟示[J]. 圖書館雜志,2014(6).
[4]邱奉捷,張若冰. 圖書館數(shù)字資源版權(quán)管理戰(zhàn)略規(guī)劃研究[J]. 圖書館雜志,2014(6).
[5]張小松. 關(guān)于數(shù)字圖書館版權(quán)保護(hù)問題的探究[J]. 才智,20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