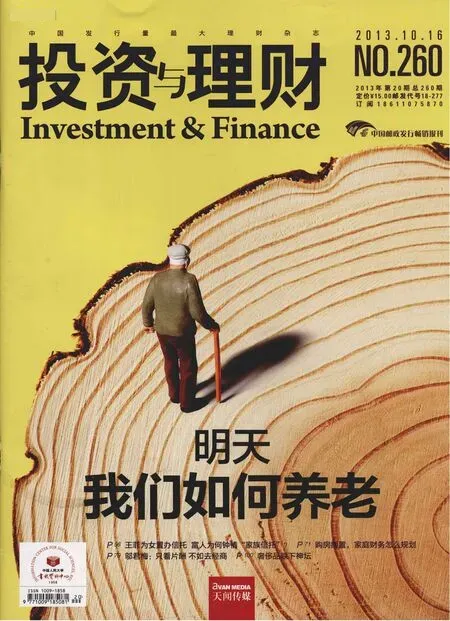關于顏色如何理解董大為的作品
郭成


有些當代藝術的作品讓人看起來不知所措,董大為的作品就算是這個類型。而那些花花綠綠的美好形式又讓人不舍離去。讓我們用“你想告訴觀眾什么?”這樣的問題與他對話,看看藝術家自己怎么說。
藝術與財富:請介紹一下你幾個系列作品的思路。
董大為:總的來說我的實踐有明顯的“藝術史自覺”特征,也就是說我的作品往往并不是從現實題材或者個人情感出發的。比如我的色粉筆系列和水彩筆(馬克筆)系列都是從思考繪畫本身的問題出發的。具體來說,繪畫一般最終要呈現的是繪畫行為的結果,是瞬間性的藝術,而我通過我的實踐要努力提示繪畫行為的過程,繪畫既是瞬間性的更是時間性的。書脊系列中也是,它反思色彩在傳統藝術中扮演的附屬角色:色彩往往是功能性的,服務于造型和象征。而我想讓色彩成為色彩本身,色彩就是色彩本身的主題。
藝術與財富:從形式感出發,尋找形式的可能性,是你在之前的訪談中提到的問題。你的作品又都是粉筆、水彩筆、書脊的顏色分類,這些最有公共經驗的途徑。你希望觀眾從作品中感受到什么?
董大為:藝術的本質要求自身不斷地更新,也就是說藝術是關于不斷拓展自身疆界的藝術,這種自我拓展主要訴諸于內容和形式。從內容上講,怎么樣把那些大眾熟悉的經驗轉化為具有不同尋常的藝術形式正是藝術家的工作。也就是說,我希望觀眾感受到:哦,這個東西我也熟悉,但我從沒有想過可以這樣!也就是說觀眾會得到啟發,日常和藝術之間的邊界是重合的,只需要換個角度去看待。而藝術正是那個提供“從另一個角度看待(事物)”的東西。
藝術與財富: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說到理解作品的方法。在你的作品中,對簡單形式的重復最終指向了什么?
董大為: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說(形式-內容-題材)只是理解藝術的一種方法,確切的說是理解具象“圖像”的方法,它曾經主導了我們理解傳統西方藝術的方式,但是我確定它不再完全適合當下的藝術了,尤其在面對抽象藝術時就顯得更加無能為力了。這也就是為什么許多藝術批評家(更不用說大眾了)認為抽象藝術自掘墳墓,只是“形式的游戲”,沒有給觀眾提供理解的角度的原因了。我想這里你所指的“簡單形式的重復”是指簡單元素的重復。對簡單元素的重復實際上正是得到形式更新和多樣性的途徑。因為在重復的過程中真正被放大顯現的是簡單元素之間的差異,而大千世界是由這些細小的差異構成的。
藝術與財富:如何將觀眾引導向你真正所想要表達的,什么引導方法會是你覺得好的方式?
董大為:觀眾通常會關心你要表達的內容,而藝術要表達的內容是要通過藝術自身的語言去表達的。
我傾向于作品不單有好的想法,而且還要有好的外觀。外觀就是指你創造的形式。觀眾要被你創造的獨特的形式吸引才會進一步感興趣你作品背后的想法。另外就是要通過作品的展示來引導觀眾去理解,作品展示(展覽)是當代藝術的精髓所在:把作品合理布置在空間當中,能夠給觀眾提供感受作品的場域;利用作品之間的結構性關系提示理解作品的語境。因此好的展覽是總是敘事性的,它通過作品與空間的關系,通過背景語境“娓娓道來”,引導并幫助觀眾理解作品。
藝術與財富:杜尚說“觀眾的理解也是作品的一部分”。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董大為:嗯,作品的闡釋是多元的,藝術作品最終要走出產生它的工作室進入到流通領域,而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作品。就像設計一款軟體應用,你要設想用戶不同的使用需求和使用習慣,所以你要盡可能使你的設計具有包容性。藝術家的創作也需要具有開放性,容納豐富的指涉。因此可以說藝術作品應該永遠是測試版的,他吸引觀眾一起來定義和完善。
藝術與財富:你怎么看待市場?
董大為:市場是把藝術轉化為藝術品并使其流通的地方。職業藝術家要依賴這個轉化和流通的反饋來支持他繼續他的職業。
藝術與財富:有沒有與藝術圈之外的人聊到:涂粉筆這個事兒我也能干,你那個還賣那么貴。你是怎么回應這種聲音的?
董大為:技藝只是手段,能用簡單的技術就達到目的不是更好么?其實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利用日常經驗創作藝術正是能產生張力的地方:在看到好的作品時,作為觀眾我會質問自己“我為什么沒有想到”。其實技術在藝術中的作用已經變得越來越低了,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科技異常發達。藝術家的工作不應該再困囿于技術層面,藝術家的“技藝”更多在于觀念層面,他通過實踐訓練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從而把一個想法“轉化”為藝術。而這些技藝對于還不熟悉當今藝術的觀眾來說并不是顯現的。
藝術與財富:家人怎么看待你的作品?
董大為:父輩通常不太理解吧,互相之間也很少溝通。但我想他們一直都試圖理解我的行為,我干的事情吧。這就足夠了。同代人還好一些,他們更能接受藝術作為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他們更愿意嘗試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