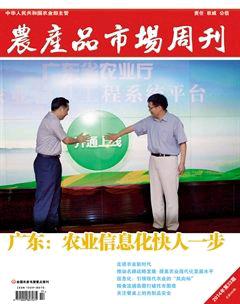逆全球化的新小農主義
文孟君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對全球化投贊成票,也并不是世界上一切都已全球一體化。全球化雖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都已占有絕對優勢,但若說全球化已成鐵板一塊,還是為時尚早。因為,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下,逆全球化的潮流也在不斷推進,成為全球化視域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新小農主義便是其中這樣一種風景。
自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小農是如此地不被人待見,總是與否定詞標簽式地相連:“愚昧”、“落后”、“保守”、“僵化”,其命運也總是被歸結為“沒落”而“衰亡”。從工業化的角度看去,任何不符合工業化原則的都是阻礙其進程的障礙物,都將被無情地邊緣化,并拋棄進工業化主導書寫的“歷史的垃圾堆”。
然而事實是否如“工業化”之愿呢?據學者研究發現:“在現實世界中,小農的數量甚至比以往任何時候還要多。全世界目前約有12億小農。擁有小型農場的農戶始終占據著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二。在這些小農戶當中,有上百萬歐洲農民仍然保留著濃郁的小農特色,其小農性程度要比我們大多數人所知曉的或愿意承認的還要高。”“歐洲越來越多的農業人口正在將自身重塑為小農。他們通過積極創造新的回應來面對并對外部強加的邊緣化境地予以還擊……同時,他們還通過對景觀、生物多樣性和食品質量等的精心投入來創造并強化與整體社會的新的相互關聯。事實上,正在使歐洲鄉村發生轉型的草根式的農村發展過程或許最好被理解為再小農化的多種表現形式。”
這種“再小農化”,或者稱之為“新小農主義”,業已通過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來“創造并強化與整體社會的新的相互關聯”。
新小農主義
“新小農主義”,首先在由龐大的食品帝國(foodempire)控制的全球一體化的世界農產品生產流通市場夾縫中,創造出一方獨立的空間,這就是新生的“巢狀市場”(nestedmarket)。其以反撥和疏離的策略,以建構“巢狀結構”形態的市場。“去中心化”,顛覆和解構了主流市場層級分明的金字塔結構,改變了主流市場規制的農產品生產及消費的理念和方式。
在“巢狀市場”情境下,農產品生產者和消費者有著鮮明的“獨立”品格,“獨立”于一個個巢狀單元組織結構中,保持著自主的地位,掌控農產品生產銷售整個過程。“安全”“有機”“營養”“利益自主”成為雙方一致的訴求。同時,崇尚“在地”的文化理念。生產者回歸自然,將農業生產植根于當地自然資源,有機生態生產,保護地方資源持續發展,農產品體現地方鄉土特色。銷售實行“地產地銷”,服務當地市場,既節約運輸費用,減少能源消耗,又有利于保持產品新鮮度。還充分利用農業資源的自然景觀,開發景觀農業、休閑農業等非農活動,增加農業的附加值,發展“新型多功能農業”。
在“巢狀市場”活動中,農產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建構了一種基于農產品的“面對面”的社會網絡,越過超市、農業公司等一體化主流市場中間環節的區隔。在這種社會網絡中,生產者、消費者、農產品的“成長過程”,都是“可見”、“透明”的,不再是“匿名”的。
正是由于迥異于主流市場的個性,“巢狀市場”在全球化的強勢推進下,以一種新型市場的力量,煥發了農業生機,塑造了一個個充滿活力的“新農村地區”。
在這些“新農村地區”里,其特點優勢在于:經濟方面,農業生產效益高、就業機會增加、服務完善等;自然方面,景觀美麗、無污染、方便、生態持續等;社會方面,社會資本存量大和可持續生產,凝聚力強,有自豪感,互信互惠,有共同目標等。“新農村地區”,業已成為農村居民愿意居住的地方。
“新小農主義”的勃興,還得益于來自城市“土食主義”的呼應。2007年5月23日,美國《新聞日報》刊登了專欄作家西爾維婭·卡特撰寫的一篇題為《本地食品全球最佳》的文章,文中倡導以食用當地生產的食物為宗旨的“土食主義”。這場“土食者”(“locavore”,也稱“本土膳食主義者”)運動,由歐美波及全球,人們逐漸遠離超市,拒絕超市食品,轉而食用當地或住所周邊50-150英里范圍內出產的食物。許多家庭、餐館、團體都直接和當地農場聯系直供新鮮蔬菜肉蛋奶等農產品。“土食主義”理念日漸深入人心。
伴隨著“土食主義”,應運而生的是圍繞著城市(城鎮)周邊的大大小小的“社區農場”、“家庭農場”、“市民農園”等的興盛,這些農場與社區形成一種“社區支持農業”(CSA)的組織聯系,更加固化了農產品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建構起獨立于主流市場之外的一種穩定的社會網絡,成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持有的社會資本。
合作社之路
面對食品帝國(foodempire)控制的全球一體化的世界農產品生產流通市場,小農生產及其利益實現的途徑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美籍華人著名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就此提出:“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是,怎樣保護面對大商業資本的小農戶的利益。一個可行途徑是,由農民組織代表其自身利益的合作社,配合政府引導和建設基礎設施,借此來提供連接小農戶和大市場的‘縱向一體化(即從生產、加工到銷售的一體化)服務。那樣的話,可以為小農戶保留其產品利潤的更大部分,借以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并逐步縮小今天的城鄉差距。”
農產品流通市場的事實已充分證明,將小農生產者的發展嵌入在“大商業資本”的鏈條中,也就是平時說的“公司+農戶”的形式,并不是一個共贏的模式,因為小農戶與“大商業資本”之間的關系是不對等的,農戶沒有生產銷售的話語權,只能按照公司的指令去生產,而且在利益分配上也只能由公司說了算;從公司角度來說,公司由于對農戶生產的管理成本過大而疏于管理,而且,由于在“公司農業”鏈條中,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匿名”的,二者之間互不知曉,客觀上消解了生產者農戶所承擔的責任。如此責任權利的不對等,就造成了公司與農戶之間的信任危機,社會資本關系網絡的不穩定。加之,“大商業資本”的逐利本能,與農民生存生產環境的持續發展,形成矛盾對立,往往是公司農業在“竭澤而漁”之后逐利而去,留給農民的只是一片又一片貧瘠的土地和仍然窮困的生活。
而真正由農民自己自愿組建、自我管理、共享利益的合作社,卻造就了許多實踐者的發展。其中,“被稱為合作社的搖籃”的丹麥,其農業合作社完善的服務體系,保護了農民社員的利益,改善了社員生活,創造了就業機會,使得丹麥農業獲得巨大成就,可以說,沒有合作社就沒有現代化的丹麥農業。
丹麥合作社組建、運作乃至成功的核心理念就是:保護合作社每一個成員的利益。
合作社組織目標訴求,就是為了組織起來、共同面對市場之需。丹麥合作社源自社員的需要。一家一戶弱小的農民,無力面對市場,為保護自己的利益,需要組織起來。獲取經濟效益不是合作社的追求,保護社員的利益,才是合作社的真正目的。
合作社的合作原則,強調自愿入社原則、一人一票制表決原則、限制資本報酬原則和回顧返還原則(按對合作社利用程度進行利潤返還)。尤其是“一人一票制”,充分關照了每一個社員的利益訴求。
合作社的管理,實行代表大會和董事會制度,經營管理層由董事會聘任。合作社重大事務的最終決策權還是社員,于管理體制上保護社員利益。
合作社的經營服務,實行產業化經營、系列化服務,延長產業增值鏈條,將中間成本環節留在社員自己的生產鏈條內,其目標還是為了社員的經濟效益。
可見,這種合作社,完全不同于“公司+農戶”的模式,也不同于以合作之名、行牟利之實的“偽合作社”。是一種由小農自己內生的、自下而上的組織行為和經濟活動,不是外來資本、自上而下的行為活動。是保護謀求“社員利益”,而非“資本利益”。
俄羅斯“小農經濟”理論家恰亞諾夫早在1925年就曾說:“一旦取得了對銷售與技術上加工的控制,農業合作社就以一種新的、更高層次的形式實現了對農業生產的集中與組織。它迫使小生產者依據合作組織的銷售與加工政策來制定本農場的生產組織計劃,改進技術,采用先進的耕作與畜牧方法,以此確保獲得完全合乎要求的產品,使其適于精細分類、加工、包裝和制作,從而能夠符合世界市場的要求。”
這些關于農業合作社的論述可謂真知灼見,可惜事過近一個世紀,歷史論述似乎仍是針對當前的現實問題而言的,這的確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