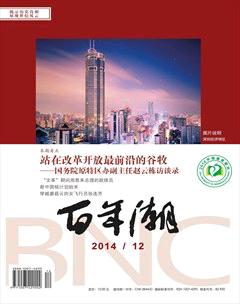“文革”期間周恩來總理的聯絡員
許人俊
“文革”中周總理設聯絡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各地學生熱烈響應號召停課鬧革命,紅衛兵運動風起云涌,高舉造反大旗,踢開黨委鬧革命。全國黨政領導機關相繼癱瘓,指揮功能喪失,國家政治經濟陷入混亂。黨和國家一些領導人憂心忡忡,紛紛為國計民生和國家前途命運擔憂。
共和國大管家周總理為防止糧食供應在運動中出問題,9月19日,他指示主管糧食工作的副總理譚震林、李先念,召農墾部蕭克副部長到中南海布置任務,讓蕭克火速赴黑龍江省會同省委書記楊易辰,研究把黑龍江墾區豐收的糧食搶收入庫,并迅速調往遼寧鞍山、沈陽等工廠集中的城市儲備,確保工廠職工有飯吃、能干活,防止“文化大革命”影響工人順利完成工業生產任務。
好在當時“文革”運動剛開始,墾區運動暫時尚未出現混亂局面。加之蕭克過去經常到墾區幫助農場辦實事、辦好事,作風平易近人,很得人心,群眾威望高,所以他召集墾區一些群眾組織頭頭開會、傳達國務院指示時,大家都痛快給予支持。蕭克在哈爾濱很快就完成糧食收集和調運使命。然而當他返回北京時,首都“文革”運動已開始大混亂。周總理讓蕭克暫住北京飯店躲開風頭,聽候他的下一步指示。可是不久,國務院陳毅、譚震林、李先念等幾位副總理先后被紅衛兵造反派打倒或靠邊站。國務院第一線只剩周恩來總理孤身一人主持工作,他百般無奈晝夜拼命工作,應對當時“四人幫”挑起的各種無政府主義矛盾和糾紛。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并不就此滿足。他們趁機攬權,在釣魚臺國賓館安營扎寨,組建、擴充“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辦公機構,利用“《解放軍報》記者”、“《紅旗》雜志記者”的名義,不斷增加手下工作人員。同時打著毛主席“精簡機構,減少官僚主義”的旗號,讓國務院總理辦公室減少工作人員。林彪、江青一伙雙管齊下的做法,讓周總理處境困難、尷尬。周總理清醒地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是毛主席寵愛的“新事物”,任何人不得觸犯和反對,但“文化大革命”運動帶來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和行動,又必須加以有效控制,否則會后患無窮。
用什么辦法才能減少風險和損失?周恩來最終想出設聯絡員的辦法。因為“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毛主席就曾經選擇女兒肖力(李訥)和侄兒毛遠新擔任聯絡員,幫助自己了解基層運動情況。這樣既不觸犯“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組”和“紅衛兵”,又可以及時了解“文革”運動的情況,采取相應對策,減少運動帶來的不利影響和損失。
周總理選擇的聯絡員個個精明能干,對黨忠誠,辦事謹慎。他們不占國務院總理辦公室的編制指標,但人人都身處中央機關各個領域,熟悉“文革”各個方面的新動向,能向周總理如實反映情況,供他及時正確決策。
總理聯絡員——在“文革”中是神秘職務,當年在中央機關功能特殊,影響深遠,在實際工作中有著許多鮮為人知的寶貴史料。我根據自己熟悉的情況和掌握的資料整理出來,拋磚引玉,希望了解情況的同志加以充實。
1966年9月初,在外交部指定余湛為聯絡員
余湛是湖北人,新中國成立前長期在部隊工作。新中國成立后調外交部蘇聯東歐司供職,擔任過司長,協助周總理及陳毅副總理管理蘇聯東歐國家的外事事務,多次陪同國家領導人出國訪問,熟悉外交工作。“文革”中除擔任過周總理的聯絡員外,還擔任過駐外大使,“文革”后任外交部副部長。
周總理讓他擔任聯絡員的起因是:1966年8月底,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不久,北京54中的20多名紅衛兵小將就利用大串連的機會,長途跋涉經過黑龍江哈爾濱、內蒙古呼倫貝爾到達邊境小城滿洲里,他們熱烈響應毛主席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號召,滿懷革命激情,佩戴紅衛兵袖章,集合在火車站的站臺上,高舉毛主席像和紅旗、標語,準備采取行動攔劫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
火車一到站,他們就不顧我方站臺工作人員阻攔,迅速沖上國際列車爭先恐后刷糨糊,張貼標語和毛主席像,散發“反蘇修”傳單。蘇方列車員遭遇突然襲擊,起初茫然不知所措,清醒后紛紛惱怒地動手撕下標語和毛主席像,驅趕紅衛兵。紅衛兵受到阻礙,怒火沖天。于是雙方形成推搡、扭打、叫罵的混亂局面。此時,紅衛兵立即在火車站用俄語高喊反蘇口號,并發表“反蘇修”演說,號召蘇聯乘客回國后起來造反,推翻蘇共叛徒集團。
國際列車上的乘客,對紅衛兵的突然舉動奇怪、驚訝,有些人還拿照相機拍照記錄現場。列車在海拉爾車站受阻停駛兩個多小時,大大超過了10分鐘的正常停車時間。
我方站長及工作人員十分著急,好言規勸紅衛兵不要這樣搞。他們反而氣勢洶洶,理直氣壯地聲稱:你們應該支持我們同蘇修堅決斗爭!隨后就紛紛拿起紅油漆,在國際列車上狂熱地涂刷反修標語。
那時,紅衛兵膽子很大,竟然要在車站給北京周總理打長途電話通話。北京話務員拒絕他們的要求,而紅衛兵則聲稱:自己有重大國際問題向總理請示匯報!如果耽誤國際大事你們能承擔責任嗎?口氣很大,在他們威脅下,話務員被迫無奈,只好接通線路。
當時,總理正在中國科學院處理辯論會問題,聽說紅衛兵有緊急長途電話,他立即接聽。北京紅衛兵紅濤通報姓名后,接著報告說:“我們攔截了蘇聯的國際列車,搞了革命行動,造了蘇修的反,現在大家正在車廂上刷標語……我們打算再搞一次攔截行動,大家讓我請示你,下一步怎么辦?”
此時,總理早已通過當地黨委匯報得知這一信息。總理起初也有些驚訝、愕然,“外交工作歷來無小事”,但還是溫和地說:“我的意見,你們可以在車站上貼大字報、喊口號,但不要到人家的列車上去。因為那是他們的列車,你們一闖,人家會說你侵犯他們主權,從而引發國際糾紛、提出抗議,甚至還會發生綁架事件。中央很重視你們這次行動,上午還討論了你們的事情。你要把我的意見轉達給大家。”
紅濤膽子很大,他竟然隨口問總理:“你說的話是否代表毛主席?如果是,我們就撤下來。”總理在電話里耐心地說:“我可以告訴你們:我說的話完全代表毛主席。為了預防蘇聯派出軍隊綁架事件,我剛才還派出一些解放軍趕到你們那里的鐵路沿線警戒,保護你們。你們看到了嗎?”(紅濤說看到周圍有大批部隊站崗)總理接著說:“好了,你們最好在10日前趕回北京,我要歡迎你們。”
在總理苦口婆心勸導下,北京紅衛兵終于撤下國際列車,允許火車繼續行駛。局勢有了緩和,總理這才松了一口氣。
9月9日,54中的20多位紅衛兵返回北京。國務院派車馬上把他們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總理在政協禮堂會議室接見小分隊成員,逐個詢問姓名和學校,大家回答說:我們是北京54中的紅衛兵,隊長是李建中、紅濤。總理笑著對紅濤說:我們在電話里早就認識了。你很厲害啊,用俄語和他們辯論了兩個小時。
總理接著聽取情況匯報,紅衛兵起初是匯報攔截國際列車的經過,接著就匯報沿途看到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如:紅衛兵一直認為黨內“走資派”只有極少數人,可是這次沿線串聯眼看各省市領導都統統成了“走資派”,大家說這樣一來,我們黨豈不是完全變質了嗎?隨后,他們都直言不諱談了一些對東北、內蒙古“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看法……
周總理聽了這些情況后,面部表情逐漸凝重、嚴峻起來,他沉思一會兒說:“你們反映的情況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況我們中央還不知道。現在運動剛剛開始,各地發展很不平衡,對于有些問題,我們還要繼續看一看,你們不要急于下結論,不要在外邊隨便發表議論。你們可以把有些情況寫成材料向中央匯報,交給余湛同志,由他轉給我。”
當時,總理指著坐在身邊的外交部余湛說:“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我就讓他來擔任你們和我聯系的聯絡員吧。你們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他,讓他轉告給我。”余湛司長站起來和紅衛兵們相識,大家熱烈鼓掌歡迎。總理接著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讓新華社洗印后發給每人一張留念。
9月15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總理辦公室通知紅濤等參加,毛主席在觀禮臺親自接見并笑著同他們握手。他們在天安門觀禮臺受到毛主席接見的消息一傳出,北京54中紅衛兵小分隊的聲譽馬上達到頂峰,許多紅衛兵紛紛趕來打聽他們在海拉爾反修的情況。
此后,他們按總理指示經常與外交部保持聯系。
有一次,紅濤到外交部打聽蘇聯對他們攔截列車的反應,外交部蘇聯東歐司的干部老劉同志直言不諱、實話實說:“你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給我們帶來的麻煩大了!事情沒有過幾天,蘇聯大使就來提抗議。我們絞盡腦汁,答復說,這次事件是民間所為,而不是我國政府所為,為此我國政府不能接受貴國政府的抗議。蘇聯大使氣得不得了,‘啪的一聲把抗議照會摔在桌子上走了。你們不是想了解蘇聯的反應嗎,來看看這份《真理報》吧!”
紅濤拿起報紙一看,蘇聯塔斯社在醒目標題下赫然報道了中國紅衛兵攔截國際列車的消息,罵中國紅衛兵是“暴徒”、“流氓”、“一批反蘇小丑”,還附了一張紅濤與蘇聯女列車員辯論的大照片。
“文革”運動千變萬化,變幻莫測。“文革”初期曾經受到毛主席、周總理接見的老紅衛兵紅濤,到了1967年間,意想不到由于初生牛犢不怕虎,大膽起來反對陳伯達、江青、謝富治迫害革命老干部而被打成“反革命”,慘遭關押、監督勞動,11年后才予以平反。他和一些紅衛兵最早大紅大紫,最后不幸又成了“文革”的犧牲品。
1966年底,在河北農村指定王振揚為聯絡員
王振揚是山東人,當年50歲。他原是部隊軍人,曾在廣州空軍政治部擔任主任,1964年被調任中央農業部政治部主任。不久中央機關機構調整,他到中共中央農林政治部擔任副主任。1965年,內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發生嚴重干旱,農業生產受到威脅,周總理親自出馬擔任抗旱組長,國務院農機部長陳正人、中央農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揚任副組長。王振揚身強力壯,肯吃苦,有文化,思維敏捷,每到一地都能把旱情寫成簡報及時送總理閱看,深受總理青睞。王振揚對華北六省抗旱情況和抗旱先進典型了如指掌,河北沙石峪的先進典型就是他向總理推薦的。
1966年冬天,我國遠在歐洲巴爾干半島的“親密戰友”、“歐洲明燈”阿爾巴尼亞,派出以國防部部長巴盧庫為首的黨政高級代表團,來華參觀訪問河北農村先進典型沙石峪。毛主席指示周總理親自接待,當時68歲的周恩來年邁體弱,重病纏身,但仍以國家利益為重,親自陪同巴盧庫等乘直升機前往河北沙石峪。這已是周總理第二次陪同阿爾巴尼亞黨政高級代表團訪問沙石峪。
因為當年4月28日,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曾經率領黨政領導人出訪我國。當時,我國實行“左”的路線,國際朋友為數不多,只有阿爾巴尼亞這個巴爾干半島的“山鷹之國”,堅定支持我們反對蘇聯修正主義,被列為“親密戰友”。按照毛主席指示,我國高規格接待他們的來賓,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等都出動全程陪同,一些省部級干部隨行,而且對訪問路線做了精心設計和安排。比如阿爾巴尼亞方面表示山西大寨已經去過,那里的抗旱經驗不適合本國,因此要求另選河北沙石峪參觀訪問。而沙石峪地處山區,交通不便,我們再次動用空軍直升機運送參觀訪問。同時,安排河北黨政領導人在沙石峪帶領群眾熱烈歡迎,由沙石峪的支部書記張貴順,詳細介紹黨支部發動群眾在山區艱苦奮斗,筑水庫蓄水和修建梯田,引水灌溉農田,種植莊稼和果樹,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富裕山區農村的先進經驗。謝胡等客人對沙石峪的成功經驗很感興趣,當時確定將沙石峪作為阿爾巴尼亞干部的培訓基地。
由此出現阿爾巴尼亞第二次派出黨政高級代表團訪問沙石峪的問題。
然而,此時我國因為出現了“文化大革命”,政治局勢已經發生急劇變化,陳毅副總理被紅衛兵打倒、批斗。周總理只能不顧病痛和勞累,帶領我軍副總參謀長彭紹輝、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中央農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揚等,一起陪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乘直升機前往沙石峪參觀訪問。
那一天,恰逢春節前夕,天氣奇冷,華北上空淺灰,寒風颼颼,沙石峪的群眾雖然奉命舉著紅旗,冒著寒風,喊著口號歡迎兩國領導人。但是一個個情緒低沉,遠不如上次周總理、陳毅副總理陪同阿爾巴尼亞謝胡來訪時,人人那樣歡天喜地,意氣風發。
在歡迎人群中,周總理已經見不到沙石峪原支部書記張貴順的身影。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狂風刮到山村后,造反派奪了大隊的權,造反派把張貴順作為“走資派”和“階級異己分子”打倒,還開除黨籍,實行群眾專政監督勞動。得知消息后,周總理十分驚訝、納悶,他關心張貴順,特地讓隨行的王振揚找張貴順來見一面。只見張貴順低著頭,氣色灰暗,滿臉憂傷,有一肚子委屈的話。但在群眾專政的壓力下,又不敢明言。總理理解他的心情,讓他暫時離開后,問王振揚這是怎么一回事?王振揚也莫名其妙,說不清楚。
總理帶著滿腦子疑問離開沙石峪,繼續陪同巴盧庫為首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乘直升機飛往另一先進典型西鋪村訪問。
那里情況同樣一片混亂。因為搞“文化大革命”,先進村的群眾分成兩派奪權,爭斗不休,各不相讓。全國勞動模范、老支部書記王國藩等領導人全部靠邊站,黨支部班子陷入癱瘓,農業生產無人過問。周總理目睹此景此情,憂心如焚,擔心全國長此下去,農業減產,群眾生活遭殃,如何向人民交代?
思考再三,在陪同外賓訪問沙石峪和西鋪村剛剛結束后,他在飛機場要登機返京時,突然臨時決定將王振揚留下,并當眾宣布:王振揚同志作為我的聯絡員留在沙石峪,了解農村“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有關情況。大家有事可以找他反映,由他直接向我的辦公室匯報。
當時,機場上人們都把目光轉向王振揚。王振揚原先是奉命陪同阿爾巴尼亞外賓訪問沙石峪的,現在總理任命他擔任聯絡員,他毫無思想準備,覺得自己穿一身陪外賓的呢子大衣留在農村活動,既不相稱又不方便,因此要求回北京換一套棉襖再來。總理當即親切安慰道:“你不必回去了吧,我回到北京會馬上派人到你家里取棉襖送來的。”
果然,周總理剛回到北京就讓國務院農林辦公室派人,到王振揚家里取棉襖送到沙石峪。第二天,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干部劉銘西(原河北水利廳廳長)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就將棉襖送交王振揚,王振揚馬上穿著棉襖在沙石峪農村開始活動,了解有關情況,當時正逢春節,王振揚和劉銘西住在大隊部空房子的炕上,吃著農民包的餃子,聽著村里的鞭炮聲,度過了難忘的除夕之夜。正月初一,他們開始在村子里了解情況,后又轉往西鋪村繼續執行周總理交給的任務。
當時,鑒于農村出現派性斗爭,附近部隊已經奉命派出兩位干部到該村“支左”。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也開始派人介入農村運動。農村運動更加混亂。村里兩個群眾組織,都自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斗爭很激烈。部隊“支左”干部知道王振揚原是部隊的領導人,懷有一種親切感,特地悄悄告訴他:這里農村在“四清”運動期間有一些恩怨, 如今“文革”運動紅衛兵又挑起新矛盾,情況十分復雜。你遇事不能輕易表態。
王振揚感到“文革”運動局勢嚴峻,作為總理的聯絡員,他在農村活動時,態度更加謹慎。找干部群眾談話時,往往只聽不說,如實記錄,絕不輕易表態。
這次王振揚按總理指示在河北農村認認真真待了一個多月,收集了許多有關農村運動的情況,正準備返回北京向總理匯報時,當地兩派群眾將他團團圍住,非要他明確表態,宣布自己是革命派,否則不予放行。他處境困難,幸虧后來有解放軍派人保護,幫助解圍,他才得以脫身,安全回京向總理如實匯報農村運動的真實情況。總理對他的工作表示滿意,隨即要他重返沙石峪和西鋪村傳達總理如下指示:1.肯定北京農業大學紅衛兵下農村的革命熱情;2.勸說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趕快撤回北京就地鬧革命,不要干擾當地農村的生產。
周總理是人民的好總理,在紅衛兵中享有崇高威望。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聽了王振揚的傳達和勸說后,迅速撤離河北農村。
王振揚在河北沙石峪陪同外賓參觀訪問時,臨危受命擔任總理聯絡員數月,他的辦事能力和水平再一次受到考驗,并獲得了總理和總理辦公室的肯定和欣賞,他也由此與周總理及辦公室結下深厚情誼。
有一次,周總理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見農林口群眾代表時,曾經詢問王振揚等人的情況,并且稱贊說:王振揚這個人不錯,河北沙石峪那個抗旱典型是他向我推薦的,他曾經兩次陪同我與阿爾巴尼亞貴賓參觀訪問過沙石峪。
但是,總理卻始終沒有提及他擔任過自己聯絡員的事,王振揚一直守口如瓶,從未向外人透露此事。這是因為“文革”期間,農林口各派群眾受“文革”思潮影響很大,都有派性作怪。總理想讓王振揚遠離派性糾紛。可是1967年12月,農林口派性泛濫,造反派先是將國家氣象局政治部副主任亓盾綁架、活活打死,接著農業部造反派深夜又將王振揚用麻袋蒙頭,從家中綁架到郊區農村監禁、拷問、審訊,情況險惡,驚動中南海,周總理大為震怒,馬上讓辦公室給農業部造反派打電話:限其在當夜12點前將王振揚安全送回家,否則以土匪罪論處。口氣十分嚴厲,造反派害怕了,隨即把王振揚送回家中。周總理在危急時刻救了王振揚,曾經成為農林口的重要新聞,但人們卻不知“文革”初期,王振揚曾經在河北農村擔任總理聯絡員之事。
1967年1月后,中央農林口機關的“文革”運動進入高潮,引發的派性斗爭日益激烈。各派組織不斷到國務院接待站,向周總理寫信告狀反映情況。人們并不知道自己身邊的王振揚曾經擔任總理的聯絡員,曾經舍近求遠跑到國務院接待站去告狀。周總理不愿讓農林口領導干部卷進運動,增加問題的復雜性。所以,總理收到人們的告狀信后,一直沒有讓王振揚繼續擔任聯絡員,而是另從財貿口選派干部擔任聯絡員。
1967年4月,選調武博山為中央農林口聯絡員
武博山是財貿口的干部,當年40多歲,山西人。他長期在地方政府從事財貿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在李先念副總理領導的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工作,也擔任過財政部司長,他平時與國務院農林辦公室聯系較多,熟悉農林口的情況。他為人勤懇,忠厚低調,富有工作經驗,辦事謹慎,故而被總理挑選為聯絡員,負責了解農林口的運動情況。
那時農林口的“文革”運動十分復雜,由于有農大紅衛兵的參與,機關兩派斗爭極為激烈,大字報滿天飛,一度貼到天安門、王府井。
從1967年3月底起,武博山和總理秘書孫岳按照周總理的指示,經常來到農林口機關和農林口各部調查研究。他們二人不聲不響到處暗訪、看大字報,在眾多人群中聽取各類反映,向總理如實匯報,前后有兩個月。當時農林口機關相當混亂,紅衛兵很多,天天人來人往。總理聯絡員和秘書往往徒步走來,從不坐小汽車來機關大院,毫不引人注目,屬于微服私訪性質,所以人們根本不認識他們。
當年5月,他們突然約農林口機關經常給總理寫信告狀的吳文平、劉子兵及我,一起到中南海附近的國務院秘密信訪室談話,亮明他們叫武博山、孫岳,是周總理的聯絡員、秘書,我們才得知他們是周總理派來的,非常高興,詳細訴說中央農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龍遭受政治迫害的前因后果。武博山、孫岳認真記錄,只聽不表態。答應將如實向總理匯報,一旦總理有指示,會通知我們。
一星期后,武博山通知我們和農林口各部及農林口院校紅衛兵代表到中南海勤政殿等待總理接見,我們無不歡呼雀躍。
那天深夜,我們來到中南海北門,由武博山和孫岳按名單,領我們進入勤政殿大廳,有百人左右。會議主題是秦化龍問題,我們既是農林口領導機構的代表,又是秦化龍問題的知情人,而且我是秦化龍的秘書,所以聯絡員和秘書將我們安排在大廳總理接見的顯著位置落座,便于匯報情況和總理提問。
一會兒,周總理來到會場,我們起立熱烈歡迎,他向大家頻頻招手致意,隨后同我們坐在他身邊的幾人握手相認。他開門見山地說:當前農林口問題較多,有譚震林問題,還有秦化龍問題。我現在繞開譚震林問題,先抓秦化龍問題。今天只談秦化龍問題。接著他讓我們匯報。盡管他早就熟悉秦化龍的情況,但他仍然仔細聽取匯報,而且邊聽邊記,邊提問題向我們詢問。工作認真,態度隨和、親切,我們絲毫不感到拘束,可以暢所欲言。
當他聽出我匯報時有江蘇口音,就特地問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江蘇泰興。他笑著風趣地說:哈,我們離得不遠,是老鄉啊!
為了證明秦化龍是好干部,會上我宣讀了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不久前寄來的證明:“秦化龍同志在部隊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作戰勇敢,立場堅定,表現出色,工作優秀,多次當選軍區黨委委員……”我隨即將證明信呈送總理閱看,他不斷點頭說:哈,這么好啊!
為說明“文革”初期有人妄加罪名打倒秦化龍將軍,我們特地把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印發的《關于撤銷秦化龍中共中央農林政治部主任職務的通知》呈送總理過目。指出:秦化龍是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任命的高級干部,用國務院農林辦公室文件列舉莫須有的罪名“1.在我國追隨蘇修搞農業黨;2.執行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3.參加編寫湖南平江史為彭德懷翻案:4.與反黨黑幫高登邦、張子意、楊之華過從甚密”宣布撤銷他的職務,內容荒唐,組織程序上也不對頭。
總理看了文件十分驚奇。讓秘書孫岳立即到中央機要室查閱:國務院農林辦公室是否有請示報告?孫岳查閱后匯報,國務院農林辦公室有過報告,但中央沒有任何領導人有批示。周總理生氣地說:顯然不像話。
總理看了這些文件,聽了匯報后,已經心中有數,他建議讓我們兩派召開辯論會,統一思想。
不久,周總理又讓聯絡員通知我們單位兩派代表9人,深夜到中南海小會議室開會,等待總理接見。我們屬于多數派,5人出席;對方屬于少數,出席3人,另有1人中立。我年紀最輕,是秦化龍的秘書,又被聯絡員安排坐在總理身邊。總理記憶力特強,一進會議室看到我就風趣地說:小老鄉又來了!
總理精神煥發,滿面笑容,看得出他胸有成竹,早已有預定方案。剛剛坐下來就指示:秦化龍是你們單位的領導,你們最了解情況,最有發言權,可以開個辯論會,心平氣和,擺事實,講道理,不要吵架。辯論雙方就是你們,其他單位和院校紅衛兵可以派代表聽會,但不參與辯論。會議名稱定為“秦化龍問題辯論會”。譚震林、秦化龍、王振揚、楊煜、梁步庭等領導干部不必出席,實行回避辦法。你們回去協商一下,定了時間告訴聯絡員和秘書。
我們熱烈鼓掌,一致擁護總理的指示。會上,對方突然提出我們單位不是兩派,而是三派。總理聽后笑笑說:任何事情、任何時候,從來都只有兩派,中間派歷來是變動的。總理說的是實話,也是他的歷史經驗。我們大家都紛紛笑著點頭佩服總理的指示。
回機關后,我們兩派很快達成開辯論會的協議,向總理聯絡員匯報。周總理十分高興,再次召我們9人進中南海開會,聽取總理的進一步指示。時間依然在深夜,地點依然是中南海小會議室,我依然被聯絡員安排坐在總理身邊,而且成為慣例。
這次總理情緒更好了,他聽說我們已經協議開辯論會,很開心,笑著連聲說好。辯論會如何開,他指示很具體。當時,雖然秦化龍已經被打倒、受批判,但他剛從軍隊選派到機關,作風民主、正派,群眾關系密切,支持者多、影響力大、處于優勢地位,總理故而讓我們負責籌辦辯論會,印發入場券,維持會場秩序,同時提醒我們務必將準備工作做好,把辯論會開好,會上不要強勢壓人、搞小動作,努力在國家機關開創求同存異的好風氣。總理甚至表示,他要出席我們的辯論會,聽大家辯論會發言,他指示我們支持秦化龍的一方先發言、反方后發言。總理態度非常認真,他說如果自己工作忙,不能到會,他將派聯絡員和秘書出席。同時,要我們每天搞好辯論會的錄音,交聯絡員和秘書帶回中南海供他聽。
總理工作周到細致,無微不至。當時是夏天,他說:現在夏天炎熱,你們互相辯論容易冒火、吵架,而上午天氣較涼快,我的意見是你們可以上午開會,下午休會,第二天上午繼續辯論。
8月初,北京驕陽似火、暑氣逼人。秦化龍問題辯論會在西郊萬壽路我們機關大院如期召開。會議氣氛熱烈,大院擠滿了人。總理因另有要事未能親臨現場,但派聯絡員和秘書出席。
按總理指示我首先發言,以40分鐘時間系統陳述為秦化龍辯護的觀點和理由,對方也陳述反秦化龍觀點和理由。雙方唇槍舌戰,交鋒激烈、尖銳,情緒對立,各不相讓。但因總理聯絡員和秘書在場,又有現場錄音,雙方都比較克制、文明,辯論會秩序井然,沒有出現沖突。總理聯絡員和秘書高高興興將辯論錄音帶回中南海。
那時,我們在辯論會橫幅上寫的是秦化龍同志問題辯論會,對方提出抗議,但并未影響會議進程。
辯論會連續開了一周,總理聯絡員和秘書天天出席。辯論雙方各執一詞,都以革命派自居,想把對方壓倒,根本無法求同存異。我們理由充分,掌聲不斷,志在必勝。總理聯絡員和秘書天天按時出席,靜心觀察會場動向,從不表示任何意見和態度,只是按時拿回辯論錄音。
辯論期間,有一次總理在中南海召見我們了解辯論情況時,對方突然向總理舉報說:秦化龍有利用小說反黨的問題。總理詫異地問我:“秦化龍還會寫小說?”我最了解情況,當即報告說:過去軍委政治部要求軍隊領導干部寫革命回憶錄,秦化龍響應號召,在上海寫了一本《泉源滔滔》,回憶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群眾熱情支援紅軍的故事。對方不懂說是寫小說反黨,純粹是胡說八道。遭我嚴厲批駁后,鑒于對方不再吭氣,總理只是淡淡一笑,沒有繼續追問。
9月份北京已經進入秋天,一個深夜,總理聯絡員通知我們再次到中南海等待周總理接見。聯絡員告訴我們:那一期間總理工作日程安排得相當緊張,輪流安排接見各單位代表商談問題。我們十分理解總理的忙碌,故而在深夜12點前,就提前按聯絡員通知到達中南海。
我們一直在總理會議附近的走廊里靜靜等待,不時看看手表。那時,首都群眾已經進入夢鄉,北京城萬籟俱寂。此時此刻,只有中南海的會議室里還亮著燈,周總理和秘書、聯絡員在聽取中央七機部“九一五”和“九一六”兩派代表匯報情況,兩派代表都是干部子弟,他們不像我們有紀律、守規矩,在總理面前無所顧忌,相互爭吵,斗爭激烈,聲音很大。爭吵什么問題,聽不清楚。但我們在走廊里遠遠都聽到兩派的爭吵聲。
直到凌晨爭吵才告結束。周總理好不容易才把他們勸說平靜、送大家走出會議室,接著又不顧勞累繼續接見我們。
當我們進入會議室時,周總理居然懷著歉意說了一聲我們意想不到的話:“對不起,因為處理七機部的問題耽誤時間,讓你們久等了。”
總理已是近70歲的老人,同前幾次接見相比,我們看出總理明顯地消瘦、憔悴,臉色蒼白。即使這樣,他依然強打精神,堅持耐心傾聽我們匯報辯論會的情況,時時記下我們的發言。他畢竟是高齡老人,因長期超負荷工作,不時疲倦地打起哈欠。為了不讓人發現有倦意,他巧妙地用左手捂著嘴部。我因緊挨總理而坐,這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楚。
那次接見時,我機關另一派突然向總理提出:秦化龍1940年從蘇聯返回新疆時曾經被捕過,有叛徒問題。總理當即說:“新疆問題我最清楚,當時是我親自處理的。黨中央委托我通過張治中把他們營救回延安的,中央早有結論。”接著,他又說你們如有新材料,也可以交給我。同時聲明他不會看,而是直接轉送中央文革。
我們機關的秦化龍問題辯論會,原本進行正常。后因受林彪、江青一伙干擾,在9月間,總理不得不讓聯絡員召我們到中南海宣布:辯論會結束。
那次接見我們時,他神情沉重,無可奈何地對我們說:“你們的辯論會錄音,我都聽了,各說各的,很難統一。”他嘆了一口氣,又說,“辯論會不必再開了,到此為止吧!你們雙方就秦化龍問題各寫3000字的報告,我交中央研究。”
總理精心策劃安排的秦化龍問題辯論會,突然宣布匆匆收場,顯然不是總理的本意,他有難言之處。我們不解其意,甚感驚奇, 但又不便細問。總理看出我們迷惑的神態,沉默片刻,終于露出一句話:“秦化龍問題,中央文革有材料。”
時隔不久,江青在北京紅衛兵大會上公開宣布:“秦化龍是叛徒,我們中央文革有材料,你們不要保他,要反戈一擊!”其矛頭實際直指周總理,因為秦化龍等100多人是周恩來營救回延安的。
盡管如此,周總理在自身遭遇林彪、江青一伙種種非難時,依然派聯絡員和秘書,設法從紅衛兵“反戈一擊”的瘋狂揪斗中,把秦化龍救出并安排到北京衛戍區監護,從而保護了他寶貴的生命。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林彪、江青一伙對秦化龍的迫害并未就此罷休,他們接著又把秦化龍當作“新疆叛徒集團”、“五一六反革命黑后臺”關押秦城監獄。直到1975年3月,中央專案組經過復查寫出復查報告否定“莫須有”的罪名。周總理當時病情加重,但在病床上仍然抱病將“復查報告”改為“平反報告”,體現了他對同志的細心和高度負責精神。粉碎“四人幫”后,秦化龍冤案獲得平反昭雪,因獄中受傷致殘,被黨中央安排擔任農業部顧問,他生前一直深情懷念敬愛的周總理。
1967年9月,在國防科工委指定劉西堯為聯絡員
劉西堯是湖南長沙人,1936年參加革命。入伍后,歷任新四軍5師軍分區政委、地委書記、湖北省委副書記、國防科委副主任、二機部部長,“文革”期間曾經擔任西北核彈實驗基地現場副總指揮。
周總理選調他擔任聯絡員的原因是:那一時期,林彪、江青一伙經常在群眾運動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鼓動群眾組織互相爭斗,嚴重干擾總理的正常工作程序。國防工業系統七機部深受其害,是“文革”中的重災區。
1967年間,七機部的群眾組織“九一五”和“九一六”兩派,經常舉著旗幟和標語口號,在首都主要大街游行示威,社會名氣很大,其派性大大超過我們農林口機關,是國家機關影響很大的單位,也是周總理極為關注的重點。兩派組織在領導人王秉坤、張愛萍問題上意見分歧,加之有林彪、江青一伙插手,雙方爭吵不斷,既有文斗,也有武斗,斗爭激烈復雜,直接影響國防工業系統下屬單位科研試驗項目的開展。
劉西堯在“文革”前就在國防科工委系統擔任領導工作,而且參與過原子彈、氫彈試驗基地的工作,熟悉國防工業系統各方面的情況。所以,周總理專門指派劉西堯擔任聯絡員,深入七機部調查研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調解矛盾。
在周總理眾多聯絡員中,劉西堯感受最多、對總理感情最深。因為在“文革”斗爭最尖銳、復雜的期間,他在周總理身邊擔任聯絡員工作時間最長,盡力最多。劉西堯晚年在回憶錄中曾經敘述,他當年是被周總理借調在國務院辦公室從事聯絡員工作最早的人,他參加的會議最多,所見所聞也最多。那時他常常目睹林彪、江青一伙在中央會議上,對周總理胡攪蠻纏,故意找茬。尤其是江青趾高氣揚,目空一切,她往往以第一夫人自居,在會議上有恃無恐,提出一些古里古怪的問題向周總理發難。他們對周總理心懷不滿,但懾于總理在黨內的崇高威望,又不敢直接挑戰周總理本人。
江青知道劉西堯是總理身邊的人,深受周總理器重,所以常常借他參與處理七機部一些問題故意找茬、做文章,挑起事端。表面上是拿劉西堯說事、責難,形成圍攻態勢,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目標是想搞垮周總理。有時江青在會上發言,常常旁敲側擊,含沙射影,暗中帶刺。她不敢明目張膽攻擊周總理,只好拿劉西堯借題發揮。而陳伯達、康生、謝富治一伙站在江青一邊,往往溜須拍馬幫腔附和,搞得劉西堯處境十分尷尬。
周總理心明眼亮,看出江青等人的用意,遇到這種情況,他馬上打斷江青等人的發言,直言不諱鄭重聲明:這件事是我讓劉西堯同志按我的意思去辦的,事情與他無關,你們不要冤枉他!這樣一來,江青等人立刻啞口無言,不敢再說三道四,會場緊張氣氛頓即云消霧散,恢復安靜。
在“文化大革命”政治風浪里,周總理和劉西堯心心相印。劉西堯十分理解周總理的難處,因此總是盡心、盡意、盡力配合國務院的秘書們做好服務工作,提前做準備,幫助周總理開好各種會議。劉西堯往往吃住都在中南海西花廳總理辦公室。有時甚至一連十幾天也不回家。他有一張簡易單人床,就擱在西花廳總理秘書辦公室旁邊。他在西花廳里同總理的秘書及總理夫婦天天見面,同吃、同住、同工作、同開會,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有著深厚的革命情誼。“文革”期間,周總理積勞成疾,需要做手術,保健醫生和身邊工作人員勸他住院治療。周總理也知道自己病情日重,但他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連續13次放棄住院手術治療。
可是,江青等人對周總理還是不松手,江青的戰略戰術是輪番進攻,整不垮他,也要累垮他。1970年周總理曾經對劉西堯等身邊人員說:“文化大革命”中,因為睡得少,我的健康減弱了,近四年心臟有毛病。在身體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1976年1月8日,敬愛的周總理逝世了,他為黨和國家盡心、盡職、盡力后終于可以休息了。他雖然離開人世,安眠于九泉之下,但卻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十分湊巧,粉碎“四人幫”若干年后,有一次我在萬壽路大院附近街上,突然巧遇周總理的聯絡員武博山、秘書孫岳。多年不見分外親切,他們都住在附近,我就到他們那里做客,大家談起周總理“文革”期間的種種往事都肅然起敬,潸然淚下,我們這些被他接見過的人,也深情懷念黨和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
(編輯 黃 艷)
(作者是農墾經濟研究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