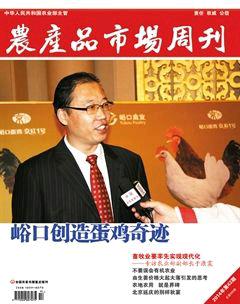種業新鮮人的選擇與成長
李飛+王瑜

“感覺這幾年種業界里的人才越來越多,必須堅持學習、不斷進步才能跟上。企業也在向服務型轉變,只有更優秀的企業才能在行業里生存下來。”
“科研院所做的更多是研究,偏理論,企業所做的更多是研發,要出產品,創造利潤。對于成長而言,不同崗位對能力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做種業、做農業的人都很淳樸,很直,不繞彎子。現在行業處于轉型期,有些企業業績不太好,但是很少有人想過跳槽,大家想的是如何渡過難關。”這是現代種業對從業人員的要求。
選擇——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
張愛斌,甘肅天水人,學的是生物技術專業,現任山東登海道吉種業有限公司技術部主管,做種業已經10年了;王堯,北京人,學的是金融專業,去年到中種集團洞庭分公司工作,做的是市場營銷。
兩個看起來毫無相似之處的種業人,在擇業時,卻有著同樣的堅決——到企業去。
“家里人就是農民,上學又在農業大學,學的也是農業,做種業是水到渠成的事。”2004年,張愛斌畢業時,因為成績優異而獲得了一個選調到家鄉某事業單位的名額。盡管親戚留、師長勸,但是早就有了明確目標的他,堅決選擇了到種企去工作。
2013年,金融專業畢業的王堯同樣認準了種企。盡管身邊的同學很多都去了銀行,但在他看來,做種業更有價值,也有更豐富的人生經歷。
靳鳳是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與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聯合培養的博士生,就業首選是穩定一點的科研院所。“自己心里很清楚,想進去并不容易,而且也不太想純粹做科研。”在導師的推薦下,她選擇了與自己專業十分契合的中玉金標記(北京)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有很好的研究平臺,又有現代企業的特色,我挺喜歡我們公司的。”
靳鳳的同事,中國農業大學博士畢業的高玉峰表示,他的同學中男生大多去了企業,現在基本上都可以獨當一面,女生普遍傾向更穩定的職業,但也有到企業的。高玉峰自己也是畢業后直接到一家外企工作,做的是轉基因性狀鑒定,但是心里放不下從上學時就一直在做的玉米遺傳育種研究。在外企工作5年之后,他還是選擇來到中玉金標記做田間育種,“能選擇時,還是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
采訪靳鳳時,中玉金標記正在中國農業大學召開第二場招聘會。“總共計劃招15-20人,今天一天收了近30份簡歷。”她說。
成長——與企業、民族種業在一起
“剛做這份工作時,我只知道小麥是直的,水稻是彎的。”去年來到中種集團水稻事業部工作的郭向榮樂觀開朗,“不懂咋辦啊,就看書唄。”
在學校學的是經濟管理專業,書里的“親本”、“不育系”、“恢復系”可難住了她,好在企業安排她去海南省三亞市輪崗一年。“三亞分公司育繁推一體化,我能完整、系統地學習。”如今,已經結束輪崗的郭向榮正在武漢出差,工作已經完全上手了。
與郭向榮同一批被招聘進中種集團的王堯,也在中種集團張掖分公司輪崗期間通過了“農作物種子檢驗員”考試,專業不對口并沒有對工作造成太大障礙。
與郭向榮、王堯相比,已經工作10年的張愛斌,對“成長”二字有更多的感觸。到企業來時,心里非常堅定,工作氛圍也很令自己滿意,張愛斌一直干勁兒十足。“三四年前,有那么一兩年時間,覺得很困惑。”張愛斌說,那個時期覺得自己遇到了成長的瓶頸,一直在做同樣的工作,不知道該從哪里突破,“沒想過跳槽,只想突破自己。”
而對中玉金標記的高玉峰、靳鳳而言,“成長”更多地意味著思維方式的轉變。高玉峰說,他上學時需要一個人做完從實驗室到田間的整個育種過程,而現在則集中精力做田間試驗。“每個人都有最擅長的事,不可能面面俱到。”在他看來,企業現在以分組模塊化為基礎做“流水線育種”,大家分工合作,能避免很多重復工作。
靳鳳是在和同學在一起時,發現自己的思維方式已在不知不覺中轉變了。“工作才兩個半月,總會時不時跟學校的情況比,時不時冒出些科研思維。”今年8月份初入職的她,很清楚要迅速轉變思維模式,培養起職業精神。一次,與在某科研院所工作的同學在一起聊天,不自覺地想要介紹公司的業務和服務,那一刻,靳鳳意識到自己已經是一個“企業人”了。
“種業新鮮人”在成長,種企、民族種業也在成長。北京中農種業有限責任公司品種資源管理主管潘巧雁有著切身感受:“公司成立兩年多了,我是初創時期來的,可以說是與企業一起成長起來的。”
企業初創,工作既有挑戰性,又很繁雜,但是潘巧雁覺得特別有成就感,看著工作平臺一點點搭建起來,企業一步步向前發展,“忙是忙了點,但心里踏實”。
“如果有一個主題講座,你最希望了解什么話題?”
對這個問題,潘巧雁不假思索地說:“中國種業未來的發展空間以及我們的成長道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