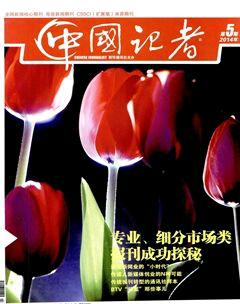“專業”讓新聞評論走得更遠——以《南方日報》“法律評論”專欄為例
□ 文/洪 丹
(作者是《南方日報》評論員)
編 輯 梁益暢 46266875@qq.com
一、對專業法律知識有系統認識,善于捕捉新聞由頭
與專業司法人員不同,寫新聞評論的人不大可能掌握所有法律條文,就像不可能掌握其他所有知識一樣。新聞評論的認識與表達,也不可能是“法條+新聞”這么簡單。關鍵在于評論者對專業法律知識要有系統認識,一方面對法治精神理解完整,另一方面要掌握我國法律整體結構、分類門徑。前者可以帶來基本的新聞敏感,后者使評論者能夠迅速找到相關的法律條文,以印證自己的新聞觸覺。知識體系構造完整,才能更善于在紛繁復雜的新聞中捕捉新鮮由頭,使得評論從選題之初便能區別于他人。
好的評論選題,應該暗合社會公眾可能尚未清醒意識到的思考期待。在法律新聞領域,捕捉由頭的選擇項有許多,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熱點判決或者重要司法審判過程。2013年,“李某某強奸案”曠日持久地吸引眼球,但在司法審判未最終蓋棺定論之前,由于涉及新聞規范紅線,新聞選點便最為關鍵。《南方日報》評論部沒有選取整個面的題目,而選擇了某個引發關注的新聞點。以《李家申請公審的要求過于荒謬》一文為例,2013年7月28日下午,李某某代理律師“蘭和律師”通過微博發布了一條消息:“(李母)夢鴿將向法庭提交申請,要求公開審理,讓所有的事實、證據和辦案過程一律公開化,消除公眾對其家庭和司法的雙重誤會。”次日,海淀法院依法駁回了申請。
事實上,于情于法申請公開審理的要求都是荒謬的。但從這個新聞由頭卻能看出李某某案之所以一直奪人眼球的根本原因——在監護人行為干擾下律師角色定位的偏差。在這種訴求下,“辯護律師不僅不勸阻當事人遵守相關法律規定,相反還公開發布這樣的言論。律師的言論自由除了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還應受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約束。”顯然,在熱點司法審判過程中,選取一個突出的評論切入點,可以起到以點帶面的作用,把新聞事實置于綱領性的論點中,逐個予以明理、辨析,這使得評論可以擺脫千人一面的尷尬。
第二,熱點事件引發輿論對于法律實施的關注。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可以發現這樣的現象,即國家已經有明文規定,但是由于行政部門沒有積極推行,或者沒有合適且合理地推行,使得法律條文施行與人們的常理認知發生沖突,從而引發輿論的普遍質疑。這時法律新聞評論有必要在法律條文的實施上發出聲音,為社會造就正本清源、健康向上的輿論環境。
2013年2月,鄭州市民吳某因在鑰匙鏈上隨身攜帶一把小水果刀,即被行政拘留3日。這一新聞不大,卻引發輿論嘩然,如果帶把小刀上街就要被拘留,整個社會恐怕人人自危。事實上,警方的處罰并未超過法律規定的上限,但關鍵在于行政部門在施行法律時并沒有遵循“合理行政原則”,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行為要做到合情、恰當和適度。這樣的新聞事件與正常人對于正常行為的基本判斷相沖突,即便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新聞”,也能成為有理可講的專業評論由頭,并以此選題為切入點適當引導輿論,為法律實施正本清源。毫無疑問,這樣的評論是有力度的。
第三,社會治理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立法動態。法律新聞評論區別于專業性的學術論文,就在于它的新聞由頭是否足夠吸引輿論關注。有些話題本身極具學術探討意義,學術界有多番討論,但是具體到現實生活中卻因為理論較為艱深難懂,不太為受眾所關注,這類話題便不適宜成為新聞評論的由頭。相反,在社會治理過程中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立法動態則往往可以成就好的新聞評論。
比如,繼“廣場大媽”成為網絡熱詞后,廣州立法擬對噪音過大的“廣場舞”說“不”。這則新聞幾乎牽涉社會上每個人的利益,不論是跳舞者抑或是被擾者。“廣場舞”現象的特征是公共產品和私有產品之間邊界模糊,共享資源和公共集體行動缺乏規則。《立法層面為“廣場舞”劃出界限》一文提出,從立法層面為公共資源與私人權利、商業行為劃出界限,應是上策。事實上,法律的發展過程便是民智逐漸開闊的過程,當一種行為獲得大部分民眾的贊同或否定,該行為便納入法治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從立法動態中發掘民生相關的新聞是一個不錯的選題選項。
二、法律新聞需要有前瞻性的視野與思維
法律與立法的問題表面上看來只是法官、法律學者和人大代表的問題,但因為新聞評論人“話說天下大勢”,法律問題往往成為新聞人“前瞻性”思考的重要話題。我國的法治進程處于不斷完善和健全之中,新聞評論作為以觀點見長的文體,可以為法治建設建言獻策,以前瞻性的視野與思維提升法律新聞的深度。
近些年有關于“醉駕入刑”、如何入刑的新聞始終吸引眼球,就在民眾陷入打擊“醉駕”的狂歡之際,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出面澄清,各地法院具體追究刑事責任,應當慎重穩妥,不應僅從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也就是說,并非醉酒駕駛都一律構成刑事犯罪。事實上,他只是說了一句公道話、一句大實話,但在當時一片狂歡的背景下,卻遭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質疑、批評。
《認清“醉駕并非一律入刑”的價值》一文具有前瞻性地指出,“社會危害性”決定了一種行為為何要“入刑”,又為何要“出刑”。如果圖一時酣暢淋漓的打擊,把醉駕統統入刑,顯然損害的就是危害性原則這個絕對標準,傷害了刑法的根基。2013年12月,兩高一部聯合發布醉駕刑事案件司法解釋,全文精神便是以“社會危害性”為標準對“醉駕入刑”予以區分,醉駕并非一律入刑。2011年的法律新聞評論觀點能在2013年被證實,顯然需要對法治進程有足夠的前瞻性視野與思維。法律的制定往往具有滯后性,是對現實社會的反映與規制,但法律新聞評論卻可以為社會作出充分預判,為法治進程添磚加瓦,也使得評論更能以專業的深度見長,具有核心競爭力。
三、觀點為王:以獨特視角對新聞事實進行深入論理,避免人云亦云
新聞評論與新聞報道一個重要不同是,評論寫作不僅追求價值判斷,而且還追求觀點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近年來媒體偏向于以理性、建設性的角度看問題,新聞評論便順理成章成為一種觀點為王的文體。當然,評論要具有獨特視角,要以觀點致勝,并不意味著特立獨行,反其道而行,凡是別人批判的我就認可,凡是別人贊同的我就反對。這些年也有一些評論者在觀點上喜歡劍走偏鋒,以期寫出博人眼球的評論文章。事實上,文章只要能自圓其說,觀點本無所謂高低,但是別有目的的觀點往往經不住時間的檢驗,在一段時間內便被證偽,這也就離評論所應具有的基本價值越來越遠。
避免人云亦云是一種姿態,支撐這種姿態的是評論者本身所應具有的專業功底與新聞視野,而非其他。2013年,曾經轟動全國的許霆案主角時隔幾年后稱要回廣州向銀行還錢。媒體蜂擁而至,輿論多有褒揚。得益于其之前的經歷,許霆這次回來更清楚知道媒體要的是什么,怎樣才能吸引媒體關注。《南方日報》評論部認為,將一個具有道德缺陷與法律責任的人硬生生塑造成衛士模樣是顛倒黑白之舉。于是推出《還要為許霆喝彩嗎?》一文,文中指出“申訴是許霆的權利,對于自認為司法不公的案子都可依法提起申訴。但是,像看待英雄一樣不吝美言,像追捧明星一樣閃光燈籠罩,那么最終出現偏差的便會是整個社會價值觀。至此,還要為許霆喝彩嗎?”這一評論在當時可謂是逆著輿論發聲,因為不少人此前還爭前恐后地為其喝彩,但文章刊發后獲得強烈反響,也引起不少媒體人的反思。這正是因為觀點致勝,不為博人眼球,堅持我手寫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