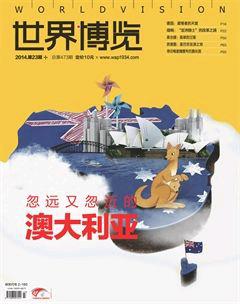德國:避難者的天堂
馬堯
導語:二戰后的聯邦德國,通過寬松的難民政策吸收了大量戰爭難民,不僅為戰后國家的重建提供了勞動力,也逐漸改善了德國在歐洲的形象。
人類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是一部災難不斷的歷史。戰爭、饑荒、大屠殺等大規模的災難都會制造同一個產品:難民。難民是有流動性的,為保住性命,必定要遷徙到另外一個安全的地方去。在伊拉克戰爭和迄今激戰猶酣的敘利亞內戰中都產生了大量的難民。這些難民逃離炮火紛飛,儼然成為人間地獄的家園,奔向他們認為可以安身立命的他鄉。
在這些難民的目的地中,德國是最受歡迎的。德國2013年接收了10.96萬份避難申請,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的避難申請接收國。德國既不是世界上領土最遼闊的國家,更不是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為什么能成為這樣一個避難者的天堂?
俄國著名作家托爾斯泰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曾經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爾斯泰這句話的意思是,為了得到幸福,婚姻必須在許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兩性的吸引、對金錢的共識、對孩子的管教、宗教信仰、三親六眷,以及其他重大問題。在所有這些基本方面只要有一個方面出了問題,就可使婚姻毀掉,即使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樣不少。這個原則推而廣之,可以用來了解婚姻以外的生活的其他許多方面。在德國何以成為避難者天堂這個問題上也是可以適用的,歷史的傳承、國家的經濟結構、國內的立法以及地理位置等諸多方面的因素都是促使德國成為避難者天堂的原因。
歷史原因
二戰中大批猶太人被納粹迫害致死,也有大批猶太人到國外避難。1949年美英法占領區的德國政治家吸取了歷史教訓,在起草建國的基本法時,專門在16條上寫“受政治迫害的人享有避難權。”德國聯邦政府遂對蘇聯、東歐和東南歐地區采取寬松的避難政策,大量接納來自蘇東地區和東德的逃亡者。對于逃離蘇東集團的人,當局都視其為“逃離獨裁政權”的政治難民,并給予寬厚的救濟,同時也利用蘇東難民外逃現象反面宣傳和打擊蘇東政權。在當局的慫恿下,國內民眾大力支持當局敵視蘇東政權的難民政策,有些西德居民甚至主動協助東德人逃亡。在1956年對匈牙利難民和1978年后對印支難民的接納問題上,聯邦政府也宣稱這些人是“不堪忍受而逃離獨裁政權”的政治難民。
600多萬外籍人(包括大批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外籍勞工)為德國的繁榮作出了貢獻。他們每年創造的產值高達200億馬克,他們所交的各種稅收和保險費900億馬克遠遠超過用在他們身上的福利費。外籍勞工所從事的工作大多為本國人不愿從事的低酬勞的臟活累活。二戰后的聯邦德國,通過寬松的難民政策吸收了大量戰爭難民,不僅為戰后國家的重建提供了勞動力,也逐漸改善了德國在歐洲的形象,這符合了戰后德國的歐洲和解戰略的需求。冷戰結束后,世界局勢仍不太平,難民的產生有增無減,德國及時調整難民政策,將接受避難申請的難民重點從東歐轉向中東及中亞等熱點地區,接納了大量伊拉克及阿富汗難民。
德國此舉可謂一舉兩得,既獲得了豐厚的經濟紅利,還大大改善了因迫害猶太人而臭名昭著的國際形象,從“難民輸出中心”轉化為“避難者天堂”,并成為二戰戰敗國中改善國際形象成功的范例,與同樣戰敗卻死不悔改而遭到中韓唾棄的日本形成了鮮明對比。
國內立法
德國有一個長期的、公開的和寬松的避難法,其基本法關于避難權的限定很寬泛,對外國難民進行庇護的法律,主要基于德國的《庇護法》和1951年《日內瓦難民國際公約》。德國《庇護法》存在于《德國基本法》第16條中。這項法律在1949年被確認為一項具有憲法和法律保障的普遍的主觀性權利。
在經歷納粹法西斯主義的獨裁統治之后,德國社會各階層在道德上取得了共識,普遍認為難民有避難的權利。同時也主張,新建的德國應該是對全世界自由和開放的。德國庇護法的發展歷史本身就經歷了一個從政治到法律的轉變過程,這表現在給予庇護的依據從個人要求難民地位的權利,逐漸轉變為行政性的要求庇護的法律,批準庇護的決定性標準也相應地從相信對迫害的主觀恐懼轉變到了客觀的“出逃環境”。
除了德國基本法第16條以外,聯邦德國還簽署了《日內瓦難民國際公約》,該公約于1951年被聯合國難民委員會確認為難民待遇的國際法基礎。但和德國庇護法不同,該項公約沒有界定個人對國家的權利,而是界定為“自由和生命在其本國受到威脅”的個人被驅逐時要求得到保護的權利。相比之下,德國制定的庇護法比國際法的規定更加明確。從1945年到1973年,每年有數千主要來自東歐國家的移民取得了難民身份和居留許可,并合法在德國居留。由此可見,德國的避難政策向來寬厚,向德國申請避難也更容易獲得批準。例如德國行政法院針對阿富汗的局勢變化而擴大解釋基本法第16a條關于“政治迫害”的定義范圍,給予了在德國境內申請避難的阿富汗人以難民身份。2002年2-10月中,超過60%的阿富汗的避難申請者獲得了難民身份,次年申請人數有所下降。
截至2004年,德國接收了約5萬名阿富汗的尋求避難者,是歐洲區域內接收申請最多的國家。此外,2007年德國內政部發布一項新的命令,允許批準少數宗教成員的避難請求。根據這一政策,當年約有三分之二的伊拉克難民的避難請求獲得德國政府的批準。
“德國制造”
德國貨向來是高品質的代稱,德國工業也因此享譽全球。大眾、奔馳、寶馬、保時捷、蔡司、博世、萊卡等享譽世界的品牌就是德國的名片。克虜伯、亨舍爾、威廉港造船廠等品牌固然映射出殺戮的武器,卻也使人類的工業文明實現了跨越式的進步。進入新世紀后,德國工業發展的勢頭不減,2002年,德國在研究型密集工業中新建的企業數量達到2250家,其中尖端技術領域950家,高附加值1300家。當第三次工業革命剛剛在中國流行時,德國提出“工業4.0”——基于信息技術下的人、產品與機器之間的互動,將是一場真正的工業革命。endprint
可以說,工業就是德國產業的核心。這種產業結構使德國對勞動力的需求較大,其原因很簡單——工廠對于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是巨大的,小型工廠員工動輒上百人,大中型工廠招收成千上萬的勞動力不足為奇,而且在工廠建立之后,需要消費,需要服務,又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可以說,以優勢工業為基礎的德國產業為國家能夠消化更多的外來難民提供了基礎。此外,德國一直引領工業革命發展的先進國家。一次工業革命是在一個新的空間、新的領域出現用機器造機器的生產力指數增長,每次工業革命之后,基本零配件都會增加一個數量級,相對應地對工業人口的需求也會增加一個數量級,更多的就業機會,自然會讓大家都找到自己的歸屬,讓社會變得昌明繁榮。
說到底一個國家要維持工業體系持續升級,必須要有足夠的人口。每當一種更復雜的機器出現,只有能招募到足夠的工人和技術員,產業升級才能進行下去。在一次又一次產業升級中只有人口足夠多的國家才能甩掉所有對手。對此,德國了然于心。然而只有8000萬人口的德國雖是歐洲人口大國,但是在未來的工業升級中工業人口還是顯得不足。美國和日本已經是億級人口的工業國家,而中國這個世界上工業產值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已經儼然是一個十億級人口的工業國家,與其相比,德國顯得相形見絀。在這種情況下,外來移民,特別是青壯年難民的進入將會緩解這一困境。
地理位置
德國位于歐洲中部,東鄰波蘭、捷克,南接奧地利、瑞士,西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北接丹麥,瀕臨北海和波羅的海,是歐洲鄰國最多的國家。就地理位置而言,德國處于一個四通八達的歐洲樞紐位置,從各個方向進入其境內都比較方便。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處于陸權與海權勢力之間存在著一條危機頻發的破碎地帶。破碎地帶以中東為中心,向東沿著歐亞大陸南岸延伸到巴基斯坦和印度,在那里分為兩條岔路。北線經過阿富汗到中亞五國,南線經東南亞、臺灣海峽到朝鮮半島。以中東為中心,向西也分為兩條岔路。南線沿著非洲大陸北部向西,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北的所有國家;北線經土耳其到巴爾干半島。歐亞大陸的南邊是破碎的地緣政治地帶。在該地帶中,國家、民族、宗教、部落矛盾此起彼伏,且自然災難不斷,可以說是難民的最大來源地。德國恰恰是毗鄰破碎地帶的發達國家。
世界上接納難民最多的國家有兩個,就是美國和德國。對于身無長物的難民來說,橫跨萬里大西洋顯得既危險又不現實,而向北進入歐洲大陸抵達德國才更具有可行性,且進入德國的交通也是比較便利的,無論是陸路、水路(受財力制約,難民較少通過航空途徑進行遷徙)都可以到達。
但是,成為避難者天堂的德國也有自己的煩惱。那就是隨著避難者的增加,新移民與本地居民之間因文化背景、生活習慣,特別是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可避免地發生一些摩擦。隨著近年來歐洲經濟的不景氣,部分本地居民認為難民搶了他們的飯碗。但是筆者認為德意志民族是誕生了現代哲學的、充滿智慧的民族,一定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畢竟,憐憫與寬容是人類共同的美德。
(作者為浙江大學環境與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