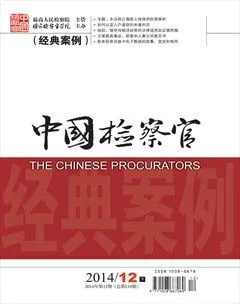受委托非法跟蹤并提供個人信息的行為的法律適用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初,馬某因懷疑丈夫劉某出軌在外包養了“二奶”,但苦于無證據予以印證,故四處尋求可以幫助自己的人員。后找到張某某,經協商張某某答應為其進行調查。馬某首先支付了現金1萬元,且答應視獲取到的調查錄像向張某某支付相關的費用及報酬。張某某找到與自己相熟的王某某,兩人遂攜帶錄音筆、望遠鏡、攝像機、密拍器等器材,一起駕駛一輛轎車對馬某的丈夫劉某所駕駛的轎車在A市所行駛的路線、停車地點進行跟蹤和記錄,并將所獲取的所行駛路線、停車地點等材料交給馬某。2012年12月份,為了便于跟蹤,張某某、王某某在網上購買了兩個通過互聯網使用的汽車定位器,然后來到A市劉某所居住小區地下停車場內,將上述汽車定位器用保鮮袋包裝好,然后秘密安裝在劉某轎車的底盤處,同時使用筆記本電腦通過互聯網查詢汽車定位器的實時位置,達到對劉某轎車在A市每天所有行駛路線、停車位置的即時跟蹤效果,2013年2月12日下午14時許,當張某某、王某某在跟蹤過程中發現被害人劉某與一妙齡女子到某賓館開房后,即刻向馬某通報,馬某立即帶領家人趕到該賓館“捉奸”,被堵在房間里的劉某被抓了現行,馬某的哥哥及多人對劉某進行了毆打。經鑒定,被害人劉某傷情為輕微傷,上述汽車定位器屬于竊聽專用器材。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王某某受委托非法跟蹤獲取并提供公民個人行蹤信息的行為確屬侵犯了公民的個人隱私,但尚不構成犯罪,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追究其民事責任。
第二種觀點認為,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王某某受委托非法跟蹤獲取并提供公民個人行蹤信息,其間非法使用了汽車定位器等竊聽、竊照專用器材,其行為是未經過國家安全機關的非法行為,應構成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
第三種觀點認為: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王某某受委托非法跟蹤獲取并提供公民個人行蹤信息的行為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其跟蹤他人所獲取的他人行蹤應屬于公民個人信息,兩人的行為已經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應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三、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上述第三種觀點,認為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王某某受委托非法跟蹤獲取并提供公民個人行蹤信息的行為構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現分析如下:
(一)本案不構成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
首先,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王某某受委托非法跟蹤獲取并提供公民個人行蹤信息的行為確屬侵犯了公民的個人隱私,但尚不構成犯罪的觀點不成立,因為,兩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不僅侵害了被害人劉某的合法權益,而且侵犯了社會公共管理秩序法益,故應追究其刑事責任。其次,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王某某受委托非法跟蹤獲取并提供公民個人行蹤信息,其間非法使用汽車定位器等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取被害人劉某的行蹤情況以便讓劉某的妻子馬某知曉而獲取酬金,雖然其在跟蹤過程中確實使用了未經過國家安全機關批準使用的竊聽、竊照等專用器材(根據《國家安全法》和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均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竊聽、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因此在我國,竊聽、竊照專用器材是一般禁止持有、使用的物品,除非法律特別授權,持有、使用即為非法),但其目的不是為了獲取涉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安全的秘密信息,也不是為了獲取涉及企業商業秘密的技術經濟信息,而僅只是單純為了獲取公民的個人信息,此行為侵犯的客體是公民的個人權利而非其他客體。由此而言,其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行為只是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主行為中的從行為,按照刑法基本理念,從行為僅是主行為的附隨、從屬行為,即應以主行為認定其觸犯的罪名予以認定,故爾,該案應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予以認定。
(二)關于《刑法》第253條之一的規定
1.第1款中“公民個人信息”的理解。關于該款中公民個人信息,由于我國目前尚未制定出臺《個人信息保護法》。因而如何確定個人信息的概念和范圍,是《刑法修正案(七)》頒行以來的一個重要問題,引起了相當多的爭論。對此,國家立法機關的有關專家認為是“可以實現對公民個人情況識別”的信息[1],而有學者則認為是“體現個人隱私權”的信息[2]。筆者認為,一般指專屬于某一自然人的一切能用于識別其特定身份的重要信息,其不為一般人所知悉,且具有保護價值,具體包括姓名、職業、職務、年齡、婚姻狀況、種族、學歷、學位、專業資格、工作經歷、住址、電話號碼、網上登陸姓名及密碼、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社會保險卡號碼、醫療保險卡號碼、駕駛證號碼、銀行卡號碼、指紋、聲音印記、DNA、書寫的簽名和電子簽名、手機定位動態信息等。
此處的“公民個人信息”,是指公民個人不愿為一般其他普通社會公眾所知,并對公民個人有保護價值的信息。在刑法語境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意指侵犯了公民的隱私權,即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搜集、利用和公開的一項人格權。[3]該條文規定的公民個人信息即為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雖然個人手機定位不是刑法條文所列舉的單位所掌握公民個人信息,但從信息的內容看,其涉及公民的個人隱私權。盡管《刑法修正案(八)》在條文中僅列舉了國家機關、金融、電信、交通、醫療五類單位所獲得的信息,但筆者認為如果機械地理解此條文的立法意圖是不夠確切的,盡管擁有公權力的國家機關單位或工作人員,更加容易獲取個人信息,但并不排除其他自然人,法人獲取信息的機會。特別是在網絡技術發達的今天,惡意的人肉搜索以及黑客入侵,使得侵犯人即使沒有掌握公權力,依然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得他人信息。在市場經濟發展高度發達的社會,信息已經衍變成為一種重要的資源,專門從事信息收集的企業或個人在合法的獲得信息的同時也導致個人信息容易受到侵犯。因此,在適用法律之時,不能機械理解,而應從立法的基本旨趣上加以適用。首先,法律條文中的“等”表明立法者并未在形式上嚴格限定以上五類單位,已經給予了司法者一句立法原意及現實社會發展進程中進行合理裁量的相應空間;其次,應當進一步從實質層面去理解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在存在侵害他人利益的人的情況下,利益持有人會對自己的利益繼續存在感到不安,就會有希望國家保護自己利益的欲求。當這種希望保護自己利益的欲求達到一定規模時,作為國家來說,就感到有必要保護該利益,就會有制定刑法的動機。這種關系,特別在對個人法益的犯罪中,更為明顯。”[4]“法益是法所保護的利益,所有的法益都是生活利益,是個人的或者共同社會的利益;產生這種利益的不是法秩序,而是生活;但法的保護使生活利益上升為法益。”[5]我國刑法將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規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其保護的則是普通民眾自身信息的私密性。而現實社會中存在著大量與普通民眾生產生活和社會正常運轉密切關聯的重要場域或單位,如保險、房產、郵政、物流等行業的單位,甚至電視購物公司、汽車銷售、技能培訓、招聘網站、獵頭公司、市場調查公司等服務性行業的單位,這些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在日常營業過程中也會掌握大量顧客的個人信息,此類顧客信息也正是當下較易受到不法分子侵害的公民個人信息類型。如果將“單位”的范疇限定在金融、電信、交通等刑法列舉的行業場域,則不利于對普通民眾個人信息的保護,亦不符合立法者打擊目前一些行業中濫用公民個人信息、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現象的立法目的。
由是觀之,公民在某個特定時間內所處的具體位置在一般情況下并不具有明顯的隱私性或者權益性,但公民從事某些活動不希望被他人獲悉時,因其所處具體方位與所從事的活動之間具有直接聯系,一旦被他人獲悉,其所從事的活動也就相當程度被暴露,損害其利益,故其所處的具體位置就具有明顯的隱私性和權益性,屬于刑法所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此時,對公民的手機進行定位,就屬于侵犯公民隱私的行為。從本案來看,手機定位信息由犯罪嫌疑人掌握后發布給被害人之妻馬某,則已經造成相應之法律后果,對此,作為接受委托開展“商務調查”的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王某某是明知的,但其為了“誠實守信”以獲取一己之利,而將其獲取到的信息提供給了馬某,導致了被害人劉某個人權益遭致損害的嚴重后果。正是基于手機定位存在侵犯公民隱私和權益的危險,當前電信部門把手機定位作為一項特殊業務來開展,有較為嚴格的辦理手續。
采用秘密跟蹤、定位、竊取、竊聽、拍攝等諸手段獲得大量公民個人信息,并未取得公民本人同意,侵犯了公民的個人隱私權,且情節嚴重,即符合“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數量較大、獲利較多、手段惡劣、對信息所有人的名譽、財產等權利造成了嚴重損害”等要素[6],即應構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
2.第2款中“上述信息”的理解。對第2款中“上述信息”的理解,實踐中有兩種觀點:第一種意見認為,根據文義解釋,該款中的“上述信息”應為第1款規定范圍內的信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刑法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二款有關內容理解問題的研究意見》認為,“上述信息”,應當是指刑法253條之一第1款規定的國家機關、金融等相關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7]第二種觀點認為,“上述信息”指一切“與公民個人密切相關的、其不愿該信息被特定人群以外的其他人群所知悉的信息。”[8]即不限于第1款中所說的個人信息,還包括其他符合條件的各種信息。[9]否則實踐中利用網絡技術、跟蹤等手段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一概不能處罰,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成立范圍明顯過窄,不符合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立法精神。刑法就是為了有力規制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以達到保護公民個人合法權益的目的。這種理解與理論和學術界的觀點是一致的。從嚴厲打擊犯罪和最大限度保護公民個人權益等方面考慮,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依筆者管見,在司法實踐中依據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也應秉承謙抑性原則,適度運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即對一般意義上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未造成嚴重后果的,可不予刑法評價,應依據《刑法》第13條“但書”予以除罪。
3.第二款中“非法獲取”的理解。“非法獲取”中“非法”方法至少應當具備以下特點:一是違背了信息所有人的意愿或真實意思表示;二是信息獲取者無權了解、接觸相關公民個人信息;三是信息獲取的手段違反了法律禁止性規定或社會公序良俗原則。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非法”并非指獲取手段或者方法行為的性質,而是指行為人的獲取行為在本質上是非法的,即行為人不符合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法律或者法規的規定。不能單純以“獲取行為違背法律禁止性規定”的觀點[10]來予以認定,即行為人只要沒有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法律依據或者資格而獲取相關個人信息的,就可能構成犯罪。
對于“獲取”之方式,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尚關注不多,筆者認為,無論以何種方式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只要超越了公民的個人相應授權,即沒有獲得資格或者根據的人以竊取或者其他方法獲取公共服務提供者在服務過程中收集或者發布的公民個人信息即可認定為“非法獲取”。易言之,刑法既要制裁公共服務提供者將自己保有的公民個人信息非法提供給他人的行為,又要處罰他人侵犯公共服務提供者對公民個人信息之保有狀態的行為。[11]從這個層面上看,非法竊取等諸方式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之行為,公民在接受公共服務時相關單位也應對所享有的個人信息予以保密,如其擅自提供給他人或單位,只要造成相應的嚴重后果,也應追究其刑事責任。
4.關于“情節嚴重”的理解。目前,尚無司法解釋對此作出明確規定。有觀點認為:對刑法修正案七中刑法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款,“情節嚴重”是指出售公民個人信息獲利較大,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多人信息,多次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以及公民個人信息被非法提供、出售給他人后,給公民造成了經濟和精神上的重大損失,或者嚴重影響到公民個人的正常生活,或者被用于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及致使公民個人信息流向境外的等諸情形。[12]就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而言,在立法者看來,即便沒有出售、向第三者提供,其行為本身就已經直接威脅到公民個人信息的安全,更給公民個人生活帶來隱患,因而主要應從行為手段是否惡劣、時間長短等方面綜合來判斷情節是否嚴重,而行為動機只應視為量刑情節。司法實踐中,一些地方對于私家偵探等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均以此罪予以認定。
據此,可依次考慮三個因素:一是只要該信息被用于實施犯罪活動,均可認定為情節嚴重;二是看是否嚴重危及本人的正常生活,或者給本人帶來較大經濟損失或導致其他后果;三是在無法認定前二者的情況下,根據出售、非法提供或者非法獲取信息數量的多少、次數的多少,其中,在出售的情況下還包括獲利金額,在非法獲取的情況下還考慮手段的惡劣程度或者支付的對價金額等等。
(三)關于本案的法律適用
通過以上分析,結合本案的具體案情,筆者認為:
第一,本案兩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侵犯了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王某某受人指使采取駕車跟蹤及使用定位器跟蹤被害人,及時掌握被害人的日常行動軌跡和活動地點,該信息顯然屬于公民個人隱私范圍;而且,被害人每天的日常生活被“無形的雙眼”盯住,時刻處于被監控的狀態,嚴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因此,該案中被害人的行蹤理應屬于刑法所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
第二,本案兩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屬于情節嚴重。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王某某受人之托跟蹤他人,且在他人乘坐的汽車上安裝定位器跟蹤,并將所獲取的汽車行駛路線、停車地點等信息材料交給他人,前后達3個多月,且其提供的定位信息導致了被害人劉某個人權益被侵犯的嚴重后果,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顯然屬于情節嚴重,依法應予懲處。
綜上分析,犯罪嫌疑人張某某、王某某受委托非法跟蹤獲取并提供公民個人行蹤信息,致使被害人遭致侵害,其情節嚴重,應以構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注釋:
[1]參見朗勝:《〈刑法修正案(七)〉立法背景與理解適用》,來源: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ProgramID=amp;pkID=22113amp;keyword=%D0%CC%B7%A8%D0%DE%D5%FD%B0%B8%A3%A8%C6%DF%A3%A9,2014年8月2日訪問。
[2]蔡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立法的理性反思》,載《現代法學》2010年第4期。
[3]張新寶著:《隱私權的法律保護》,群眾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頁。
[4][日]西原春夫著:《刑法的根基和哲學》,顧肖榮等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頁。
[5][日]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有斐閣1992年改訂增補版,第83頁。轉引自張明楷:《新刑法與法益侵害說》,載《法學研究》2000年第1期。
[6]周海洋:《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理解與適用》,載《中國審判》2010年第1期。
[7]參見趙秉志主編:《刑法修正案(七)專題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頁。
[8]葉靈賢:《周娟等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案——非法獲取大量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如何定罪量刑》,《刑事審判參考》2011年第4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
[9]張磊:《司法實踐中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疑難問題及其對策》,載《當代法學》2011年第1期。
[10]王昭武、肖凱:《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認定中的若干問題》,載《法學》2009年第12期。
[11]趙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法益研究》,載《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12]郝家英:《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理解與適用》,載《中國檢察官(經典案例版)》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