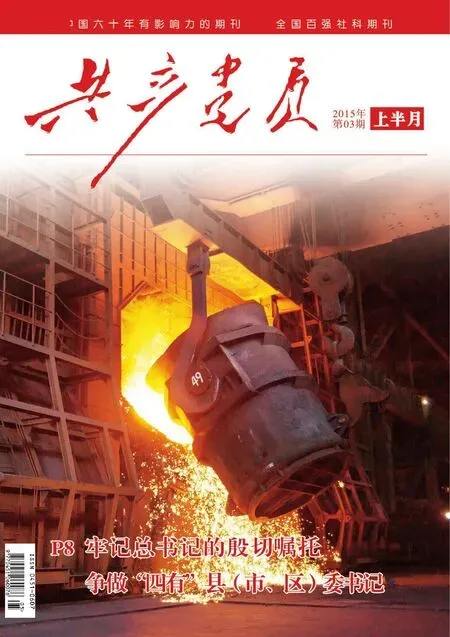出生性別比失衡及其治理
文/楊菊華
出生性別比是一個簡單的人口學指標,但其失衡不是單純的人口問題,而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是社會轉型、經濟轉軌、人口轉變時期面臨的一個事關全局和事關未來的現實問題。其潛在后果具有極大的危害:可能威脅21世紀的全球形勢,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民主化進程。

出生性別比反映新生兒的性別結構,通常是指在1年內,每100名出生的女嬰總數所對應的男嬰總數,正常范圍大約是每102-107個男嬰對應著100個女嬰。雖然出生的活產男嬰多于女嬰,但由于男嬰和男性青少年的死亡率高于同齡女性的死亡率,至結婚年齡段的性別比將大致平等,形成均衡的性別結構。在未受到干預的自然生育狀態下,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種族的出生性別比相對穩定。任何較大程度的與正常范圍的偏離都暗示著某種形式的人為干預,也都將產生不利的社會、經濟后果。
由于依舊強烈的男孩偏好,中國同許多周邊國家和地區(韓國、臺灣、越南、印度等)一樣,在生育觀念轉變的過程中遭遇了嚴重的出生性別比的失衡。中國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遭遇該問題的國家,但延續的時間之長、波及的范圍之廣、失衡的程度之深在國際上都是獨一無二的:1982年,中國的出生性別比超過108,開始失衡;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生性別比不斷攀升,大大超出正常范圍的上限值;盡管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治理措施,但2013年依舊高達117.6。
出生性別比是一個簡單的人口學指標,但其失衡不是單純的人口問題,而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其潛在后果具有極大的危害:不利于女性婚姻的穩定和安全,可能造成大量的非意愿性獨身男性(即“光棍兒”),破壞家庭的生、育、養功能,增大家庭不穩定性風險,破壞人口的安全與發展,危及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一、男孩偏好、生育擠壓、便捷技術與出生性別比。中國和他國的實踐經驗一致表明,出生性別比失衡源于三個要素:一是男孩偏好,二是生育擠壓,三是便捷技術。其中,男孩偏好是本源性因素,生育擠壓是催化性因素,便捷技術是可行性因素。雖然不同地區各有自己獨特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但各地學者達成的共識是,沒有性別偏好(或性別偏好尚不影響生育行為),出生性別比通常不會失衡,即便技術可及、生育擠壓等條件都有呈現;同樣,當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上下且男孩偏好并未得到有效緩解時,出生性別比似乎總會失衡,已經失衡的比率也難以復歸平衡。中國的情況因為嚴格限制性生育政策的存在而顯得更為特殊:政策不僅帶來生育擠壓,而且暗含無意識的性別歧視或短視,故而使得中國出生性別比的失衡程度在各地區之中是最深的。
二、治理出生性別比的現實誤區。緩解出生性別比就需要針對這幾類要素,多管齊下、綜合治理,既要堵住出口,也要掐斷中間,更要疏導源頭,而關鍵在于疏導源頭。的確,針對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的情勢,中國政府采取了綜合措施,一方面嚴厲打擊“兩非”,另一方面大力推進“關愛女孩行動”等旨在保護女胎生命權、保障女孩生存權、促進女性發展權的多項措施,這些措施無疑是受歡迎的,且出生性別比持續攀升的勢頭得到了遏制。2009年和2010年,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出現了令人欣喜的微降趨勢。如果普遍的二孩生育政策能夠得到推行,將不僅緩解生育擠壓,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夠消除隱藏在1.5孩政策中的性別盲視,將會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降低出生性別比。
然而,雖然當前政府、社會和學界對出生性別比問題十分關注,但現存的學術研究、政府治理措施仍存在以下幾大誤區,從而降低了治理措施的效果:其一,從男性立場出發,忽視性別失衡對女性群體的不利影響。目前,在討論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后果時,主要考慮“失蹤女性”對男性婚姻擠壓的影響,很少涉及該現象對女性及其家庭、社會、經濟等多方面的不利后果。出生性別比失衡雖然是一種個人、家庭生育行為的選擇,但它是社會性別發展失衡和兩性文化發展失調的結果,可能進一步加深女性經濟社會地位的弱勢。不僅不少女胎的生命權被剝奪,而且反復的選擇性流產還會對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傷害——出生性別比失衡犧牲的是女性的心理與生理健康;大量女性的缺失還會導致女性早婚、早育、性侵犯、家庭不穩定等不利于女性發展的后果;此外,男性多于女性等于間接增加了勞動力資源的供給量,加重社會的就業壓力,可能打破經濟秩序與格局,造成勞動市場的紊亂和社會不穩定,挑戰產業結構的合理性,并最終沖擊女性的就業機會和職業地位的獲得。然而,雖然有大量的研究分析、預測“失蹤女性”將可能造成多少“光棍兒”,但該現象對女性的潛在不良后果卻幾乎沒有深入研究。這一特點本身也表明,目前,我們對該問題的認識帶有明顯的性別盲視,從男性本位視角出發,體現了男性中心和男權文化。
其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輕視從女性生命歷程視角進行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衡雖然是出生之前的問題,但反映的卻是在整個生命歷程中,兩性地位的失衡和女性權利的貧困。然而,雖然方方面面意識到從生命歷程視角進行綜合治理的重要性,且也有所行動(如關愛女孩行動、利益導向),但目前的治理政策、措施、項目主要還是針對孕婦。但是,對個體和家庭而言,與兒子的有無相比,利益導向機制的效用十分有限;而且,隨著教育“兩免一補”制度的推行,對女兒戶家庭的關愛亦顯得微不足道;同樣,隨著國家養老保障政策的出臺,計劃生育家庭的養老補助也黯然失色。相反,在市場化過程中,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弱勢地位越發明顯:就業困難、職業的性別隔離明顯、“主內”的身份得到強化,等等,這些時時刻刻發生著的日常現象反復提醒人們,兒子比女兒好。因此,只有在生命歷程的全過程中兩性地位趨于平等,男孩偏好才可緩解,出生性別比也才有望回歸平衡。這意味著,失衡的治理措施必須著眼于整個生命歷程。
其三,從政府和學者的視角出發,忽視婦女及家庭對出生性別比失衡后果的認識。目前,不管是學術研究、國家干預項目,還是基金支持項目抑或是其他項目,多是從學者、政府或社會的立場進行,所言所做的都是非直接當事人認為是對的東西,難免自說自話、自娛自樂。實際上,群眾對未來可能有多少“光棍兒”并不關心,更不認為這會影響到他們的家庭和兒子的婚育。
我們在多個地點的定性訪談中發現,不管是婦女還是家人,都沒有人認為男孩多了會有問題。這里有幾種情況:一是沒有意識到婚姻擠壓問題。部分被訪者的兒子很小或將要生孩子,當下只是希望家里添上男丁,娶妻之事太過遙遠,尚未考慮,也不知婚姻擠壓問題。二是雖然知道男孩比女孩多,也聽說過婚姻擠壓的說法,但不足為慮。部分人認為,現在人口流動頻繁,年輕人接觸的圈子大了,找對象的機會也就多了:外出打工的男孩可以從外面帶媳婦回來,去經濟稍差的地方找(如山區),或去國外找洋媳婦。因此,他們亦未將娶媳婦之事當作是難題,何況現在人們看到的主要是“剩女”而不是“剩男”。三是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人們多從家庭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認為孩子個人條件(如長相、學歷、未來從事的工作)和家庭經濟條件(如給即將娶妻的孩子蓋一幢像樣的樓房或者去城里買一套商品房、置辦像樣的家具)才是能不能找到對象的關鍵。只要這兩個條件都好,兒子就不會娶不到媳婦,娶不到媳婦之事“落不到自己兒子頭上”,無需擔心。“找不到媳婦?怎么可能?只要我兒子優秀,哪能找不到媳婦呢?”
三、治理出生性別比的有效出路。為更有效地綜合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除繼續推行現有項目外,還須針對上述困境,采取相應的措施。
其一,加快成果轉化,喚起人們對出生性別比失衡對女性及其家庭的潛在危害的認識。
其二,同時推進短期和長期項目,關注女性的終身發展。
其三,拓寬宣傳視野,糾正目前對出生性別比失衡后果認識的誤區。最后,調整生育政策,取消1.5孩政策以頭胎的性別為二孩生育條件的限制,消除政策的性別短視與盲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出生性別比回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