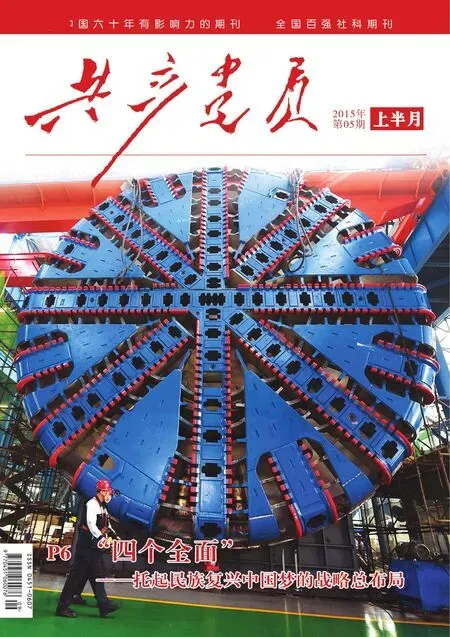左手理論右手輿論的侵華教父(下)——日本軍國主義野心家福澤諭吉
文/周力
如今,福澤諭吉仍然被日本右翼勢力奉為“靈魂導師”和“精神教父”。誰能相信一個有著300年侵華之夢,行70載侵華之實,此后又70載高調反華的東洋鄰國,會在一夜之間就改弦更張,鑄劍為犁,變成一個福澤諭吉自詡的“文明之邦”“日新之國”呢?

福澤諭吉的頭像被印在日本最大面值的鈔票上
領銜學術團體,手握自辦媒體,依托慶應義塾陣地,
福澤諭吉是明治維新時期名副其實的知識界、教育界、新聞出版界要人。從1882年創辦《時事新報》到1902年去世,他以幾乎每隔一兩天就發表一篇社論、評論、隨筆的持續節奏,議論政治,臧否時事,闡述觀點,影響政府和社會。
脫亞論惡鄰國
1885年3月16日,福澤諭吉拋出著名的《脫亞論》,否定和抨擊中國,闡述他關于亞洲的外交觀、戰略觀,引起強烈反響。
福澤諭吉在文中叫囂,“支那朝鮮實行古老專制”“不知科學為何物”“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鮮恥”“朝鮮行刑場面殘酷”等等,都會被西方誤解為日本也是這樣,這就“間接地成為我外交的障礙,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解決的對策就是“脫亞入歐”,“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而且態度要堅決鮮明,“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它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
這些論點,是福澤諭吉“智慧”的“結晶”。
《脫亞論》問世三年前,朝鮮發生了動亂,清政府應朝鮮請求,派兵前去平定。福澤諭吉發表了一篇題為《日支韓三國的關系》的文章,認為日本應乘機干預,將朝鮮由中國藩屬改為日本控制,甚至不惜一戰。
《脫亞論》問世兩年前,福澤諭吉發表了《到支那去應獎勵》和《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兩篇文章。前者鼓勵日本人把“支那的四百余州”當作闖蕩事業的地方,“大至國權擴張,小到一身榮華”,都可以“積極進取”,表現出日本擴張主義者共有的貪婪。后者則詆毀中國為“一潭死水”,“支那人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開始從國格和文化的角度否定中國。
《脫亞論》問世前一年,福澤諭吉又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題為《有支那色彩的東西應該摒棄》,認為中國對西方“不究其主義而單采用其器,認識只限于表面”,“沒有進步的希望”,因此“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知識上的交往應一律斷絕”。另一篇題為《東洋的波蘭》,認為尚在進行中的中法戰爭“是支那滅亡的伏線”,預言中國會像波蘭一樣被西方列強瓜分。他在文章后面附上一張來路不明,用漢字標注的《支那帝國未來分割之圖》,叫囂日本應乘勢“占領臺灣全島和福建的一半”,“在故地(明末倭寇騷亂中國之福建、浙江沿海地區)插上日本的國旗使之飄揚”。
福澤諭吉對中國資源的覬覦窺伺,對自己得以教益的儒學文化的否定詆毀,對中國應對西方文明舉措的歪曲和中國與西方列強軍事沖突中意欲分肥的貪婪,已兇相畢露。他在偽善的假文明外衣下,包裹著一顆思慮臻熟的軍國主義擴張野心。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觀點,對歷史上藤田信淵和吉田松陰的侵華設計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突破。如果說,藤田信淵和吉田松陰尚局限于領土資源上的貪欲、侵略路線的規劃、“失之歐美,取之中國”的卑鄙,福澤諭吉則通過對中國、對東亞的國別歧視、文化詆毀和全民族的否定,增加了日本社會蔑視亞洲的盲目自信和侵華侵朝的“合理性”,以至后來日本侵略軍一直自欺欺人地以占領鄰國、解救亞洲的“遠東憲兵”的姿態實施侵略。正是由于“脫亞”的國策,促使日本踏入太平洋戰場后加入德意日二戰軸心國,在狂妄中走向徹底失敗。
“脫亞論”的出現,其實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日本近代中國觀的分野,是日本與中國斷交的另一種方式的聲明。從那一刻起,它的巨大影響,使日本與中國實際上進入了戰爭前的非常時期。
主侵華 鼓與呼
福澤諭吉信奉強權武力,視其為日本的生存之道。他認為,“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箱彈藥”,各國交往的途徑只有兩個,“或滅亡他國或被他國所滅”,因此日本要與“禽獸世界”看齊,走一條“內安外競”、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國家之路,即法西斯軍國主義擴張之路。而他謀求消滅并借此保存自己的對象,則是近鄰中國和朝鮮。為此,他不僅在理論闡述上不遺余力,還通過具體規劃、直接指導和社會發動等方式,沖到侵華一線直接作戰。
福澤諭吉別有用心地美化戰爭,著文宣傳“和外國的戰爭未必是兇事危事”。隨后,他又著文告訴日本社會,戰爭的目光要聚焦中國,因為“日本在東洋立國,與支那有極大的利害關系,必須高度予以注意”,方法是借機下手,趁火打劫。
——1882年朝鮮內亂,福澤諭吉蠱惑日本政府派兵干預,遭到中朝聯合抵制,沒能如愿。此后的幾年里,他屢屢煽動日本政府對兩個國家作戰,并規劃出一個詳細的侵華路線:
首先應該派一支軍隊赴朝鮮京城與支那兵鏖戰,讓朝鮮政府答應我正當的要求。同時,我軍從陸海大舉進攻支那,直搗北京,皇帝若退到熱河,那就跟到熱河。
這條侵華路線,與吉田松陰當年規劃的思路如出一轍,一脈相承。福澤諭吉瘋狂地為日本政府打氣:“為了實現這一希望,我們的身家性命不足貴,愿進軍北京決一死戰;我們的財產愿全部充作軍費……日本必然勝利。”為了讓日本繃緊對華戰爭的弦兒,他撰文呼吁,與談判的準備相比,日本“更應該作開戰的準備”,甚至“希望的是御駕親征”——天皇親自率軍侵華!
——中日甲午戰爭前后,福澤諭吉更是密切關注,隨時煽風點火。戰前,他就對李鴻章與朝鮮政府往來電文中,斥責日本干預朝鮮內政的語句不滿,呼吁日本政府“一刻也不要猶豫,要與支那為敵,斷然開戰”,同時不放過朝鮮這個與中國“同一個洞的狐貍”。
甲午戰爭爆發后,福澤諭吉欣喜若狂,著文疾呼:“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簡直不知道說什么才好,我活到今天,才看到如此光榮的事”。他給日本國民和軍隊鼓氣說,“我軍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銳的武器,打他腐敗國的腐敗軍隊,勝敗結果本是明明白白的”,而“野蠻不開化的中國人”,“應當向文明的引導者日本國三拜九叩,感謝其恩”。戰爭中,他建議日本政府驅兵“直入北京可也”,讓中國承認日本“是東亞先進文明的代表”,“甘心俯首于文明的腳下”。他在1894年8月11日至16日接連發表文章,呼吁日本軍隊“趕快攻略滿洲(中國東北)三省”,滅亡中國,否則,“曠日持久,會上支那人的當”。他還著文《支那龐大,但不足懼》,進一步分析日本打敗中國的理由:中國政府腐敗,人民不團結,中國人“喜歡虛張聲勢……出動一兩萬的兵力就聲稱幾十萬,古來筆法即如此”。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痛哭流涕,組織了“報國會”,帶頭募捐,支援戰爭。僅他自己就捐出名列全國第二的1萬元巨款(這也是后來他的頭像被印在1萬元面值日元上的原因之一)。他不僅要求日軍瘋狂掠奪,還再次鼓吹天皇御駕親征:“越遙遠之大海,大纛(天皇旗)迎韓山之風飄揚之事,亦可考慮。”他建議,在靖國神社,由天皇“親任祭主……招待全國戰死者之遺族,使其得到臨場之榮譽”,借以鼓舞士氣。
日本兵攻占中國旅順后,瘋狂屠城,造成6萬多人被殺害。當這一獸行被國際社會譴責時,福澤諭吉一反以“文明人”自居的虛偽,狡辯說“不能把這些人當普通人看待”,因為中國人“不講信義”,“這些人是軍人偽裝成市民的”云云,虛偽的面孔不攻自破。日軍在甲午戰爭中取勝后,他積極建議內閣借談判之機逼迫清政府將旅順、威海、盛京、山東和臺灣等地割讓給日本。一時間,福澤諭吉的侵華表演甚囂塵上,影響巨大!
——1900年,在福澤諭吉的生命降下帷幕的前一年,中國爆發了義和團運動。福澤諭吉立即建議日本政府派兵加入八國聯軍,在英美不能派大量軍隊來華的情況下,借機進軍中國,進一步獲取領土和權益要求。結果,在32000人的八國聯軍中,竟出現12000人的日本軍隊。作為主力,日軍不僅打到北京,獲得賠款,還一度進兵廈門,企圖單獨占領福建。自此,日本把自己定位在“遠東憲兵”的強權位置上,不斷戰爭,不斷侵略,直至1945年在二戰中舉國慘敗。
往事并不如煙。回首當年,由于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國權擴張論”和“武力侵華論”在“倡導文明進化”的外衣下流毒甚廣,不僅對當時的日本社會輿論具有極大的偏激誤導,也在慶應義塾的課堂上不斷植入學生的頭腦之中。他所謂“文明”和“野蠻”之分的地域文化歧視,日漸成為日本蔑視鄰國、武力稱霸世界的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理論依據和思想基礎。他集路線設計、理論輿論和教育于一身的文人侵華模式,更加強化了日本侵華的內在理念和外在成效。
如今,卷帙浩繁的福澤諭吉全集仍大行于世,慶應大學的“杰出校友”小泉純一郎之輩在日本右翼勢力中的影響與福澤諭吉的侵華設計還在遙相呼應,福澤諭吉仍然被日本右翼勢力奉為“靈魂導師”和“精神教父”。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了解日本,知曉近代中日關系的歷史,掌握日本侵華的理論脈絡,仍是今天國人的必修課。誰能相信一個有著300年侵華之夢,行70載侵華之實,此后又70載高調反華的東洋鄰國,會在一夜之間就改弦更張,鑄劍為犁,變成一個福澤諭吉自詡的“文明之邦”“日新之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