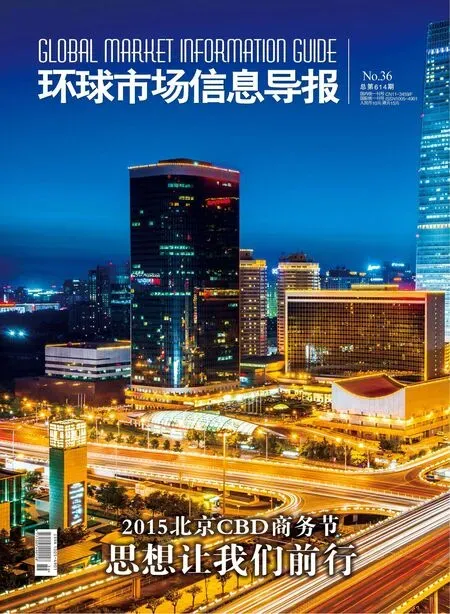我與她的《空白格》
(文/張子墨)
(一)
在萊茵風情門口,她說,你來吧,就不下去接你了,四樓。
站在樓下,仰望燈亮的四樓,怎么你竟讓我這樣銷魂?
敲門,她在里面喊說門沒關,我說怎么不警惕?她說,你來了。我問她今年為什么沒有回家,她說不想回去。我說,為什么?她說,兩年了,一直不好意思!我說他不是已經走了嗎?高升了!
她說,已經不聯系了。我說這樣也好!
她說,你跟我說過喜歡吃糖醋排骨,我今天做了,參照美食書做的。還有你喜歡的油燜茄子,還有紅燒魚。我說你這樣會讓我愛上你的。她笑了笑。
明知道不可能,但是還是會撕心裂肺地開始。
吃完飯,下樓陪她散步,走到縣委大門口,指著大樓,她說,真不想在那間辦公室了。我說,熬吧,都是熬出來的。
走到主題廣場的大劇院門口,她用右手牽我的左手,我躲避,但是還是一起牽手走到河邊。
沉默加上沉默,變得更沉默。
她開口說,我這種女人你會娶嗎?我說你誤會了,我們只是朋友。她沉默了。
一個逞強,一個勉強。
我說,今年陪你過春節吧。她沉默的臉上,多了些笑容。牽著我,一直沿著路走。奢望愛情的女人,真的要求不高,有時候只是一句她想聽的話。
(二)
她姓凌。
不知不覺,已經晚上十點,我說把你送回去吧,她說,你把我送到小區門口。
到了小區門口,她說,上去坐會吧。
開門,關門的那一刻,她從后面摟住我,我說,別這樣,話還沒說完,她說,我喜歡你,我說你只是喜歡,她說我會深深愛上你的。
其實,對于我來說,她只不過是我的紅顏知己,我充其量也就是她的藍顏知己。這是我這么認為的。我喜歡跟她在一起,她也喜歡跟我在一起,我想喜歡的都是在一起的感覺了。
上次跟她在一起聊國家政策,聊哪些領導人好,哪些有缺點。我們也聊到民主黨派,她說她有個妹妹想加入民盟,我說縣級沒有機構也沒有權力,區級別的有吧,區政府的法人是市長,你有空去市委統戰部看看,民盟這塊屬于他們協調管理。
她說,我只是提一下,你干嘛說這么多。我說鐘情你唄,愿意為你服務,她笑了笑,是那種綻放燦爛笑容的樣子。
她讓我留下,她說我們認識兩年了,把愛我藏在心底,我說別這樣。我們真的愛不起。
她執意讓我留下,我說我睡沙發,她說夜里受涼會凍著的。
說完,她緊緊地抱住我,她說,我真的不想讓你走,我想你陪。
我的心此刻跳得很快,這是不是太快了,她好歹是個有級別的某機關的領導。不能這樣,不要這種偏畸形的愛。雖然我們在年齡上一樣。
我的心此刻跳得很快,她說,我想吻你,我嗯了一下,其實我是本能反應。
她吻我了。
我緊緊摟住她。
她說,我們談一下。
凌雪跟我所談的,是你們所想不到的。她談到她的母親,她也談到她的父親。
當她談到她的父親,我也落淚了。
大前天,她的父親去世,誤診,應該說醫生無醫德。
她說,她父親上午十點到醫院,一直拖到下午四點,醫生都是很不耐煩的。五點十七分宣布死亡。
她母親跟她說,這是痰多導致的窒息死亡。
因為痰多,呼吸時候給人的感覺是在打呼嚕,醫生當時也很不耐煩地說他在打呼嚕,其實是窒息導致的呼吸問題。
我說,你不要說了,這純粹是醫德問題,醫術水平問題。
她說,她在機關,一個女子,醫鬧絕對不可能,走正常手續,市區關系不是太到位。我說,我幫你,其實最后,我幫她不少,她說,她一輩子記住我。
她還說,就算嫁給我一百次,就當是一種盡孝。我說,感謝。
(三)
昨晚她打電話給我,站在陽臺打給我的,說她往下看感覺自己很飄渺。我說我現在就去找你,真的擔心她出事。
我有她家鑰匙,那天特意讓她配一把給我。
打開門,飛快地跑到她面前抱住她。連我都覺得自己不可思議。這種行為是不是代表已經愛上一個人了?擁吻過后,她捧著我的臉看著我,看我的眼神有點詫異。
她說,為什么這樣?
她說那個老男人出事之前又來找她了,我說你找個熟悉的人帶話給他,讓他給你安寧。她說她曾經愛上過這個已婚的老男人的。
權力與財富真的會讓一個女人瘋狂的,瘋狂地愛,畸形地愛。
她說她那會兒很小,真的不懂什么。
昨晚在她家沒走,摟著她入眠,醒來之后,總想說點什么。我側著身體,她從后背摟著我,就這樣她入眠。
愛情對于孤獨寂寞的女人來說,真的是個奢侈品。
(四)
2015年1月13日。
我打電話給她,我說,你在哪?
她說,在老家。
電話里傳來平時她喜歡聽的那首《空白格》。
掛下電話,我開車到她樓下,萊茵風情的春節顯得比平時更蕭條。
我仰望四樓,燈亮著,我的直覺是正確的。
我有打電話給她,我說我在你樓下,她愣了好長一段時間,吐出一個字,哦。對于我來說,她愣的這段時間很長。
她說,對不起,這并不是她想要的,她說她想生活,她想認真地在這個世界上活。她說,我不想要這種生活方式,但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行為。
事實上,那個老男人每次去,她都會在客廳播放這首歌,這首歌曲讓我知道,那個老男人那天晚上在她家。
第三天,老男人落馬了,受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