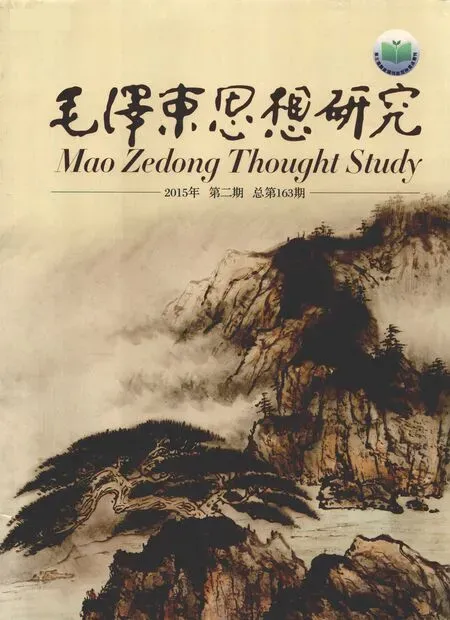社會資本與經濟學分析范式研究評述
鐘 君,曹 陽
(1.華中師范大學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武漢 430079;2.興義民族師范學院,貴州 興義 562400)
社會資本與經濟學分析范式研究評述
鐘 君1,2,曹 陽1
(1.華中師范大學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武漢 430079;2.興義民族師范學院,貴州 興義 562400)
對社會資本的定義各種各樣,概括起來其內涵主要有“資本”屬性,社會網絡關系,以及嵌入在網絡關系上的互動互惠、合作、信任、規范等特征;社會資本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及嵌入網絡關系內的文化認同、價值判斷等被納入了經濟分析的范式內,使得傳統的以價格為中心的供給需求分析范式向以微觀主體行為為中心的分析范式回歸;社會資本與非正式制度存在信任、規范、習俗特征的交集,但在它們的形成動機上有區別。
社會資本;經濟學分析范式;非正式制度
一、社會資本理論研究評述
社會資本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其原因正如殷德生教授(2001)說的源于三個方面:一是20世紀70年代末自由主義的盛行,弱化了公民與國家、個人與共同體的內在和諧關系,引發人們對自由主義思潮的反思,將研究重點轉向了社會內在結構及其社會關系網絡中的道德、文化、制度的分析上。二是東亞經濟的發展,很多學者把東亞經濟的崛起歸結為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倫理觀和社會關系結構,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相對和諧的關系。這為社會資本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證資料。三是社會資本理論把社會環境中的文化、理性、網絡關系的參與、互惠共享等納入了經濟分析的變量中,在資本、勞動力、土地、文化制度外又增加了一類生產要素。社會資本理論在分析消費、風險分擔、勞動力流動、金融借貸等經濟活動方面有極強的解釋力。社會資本理論最先是來源于社會學,后來在政治學、經濟學領域得到了推廣運用。“社會資本”一詞最先是漢尼芬(Hanifan,1916,1920)提出,旨在說明它對教育和社群社會的重要性,但他對社會資本的概念表述得不清晰。而對社會資本理論研究貢獻最大的是法國的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 1997)、美國的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和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普特南(Putnam)。
上世紀80年代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 1997)在《社會學研究》上撰文定義社會資本:“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這些資源與對某種持久性的關系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這一關系網絡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認的,而且是一種體制化的……集體的每一個成員擁有這些資源”。社會資本僅次于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從這一闡述來看,社會資本不同于人力資本、貨幣資本、物質資本。它是資源的集合體,該集合體和社會關系網絡是聯系在一起的。社會資本存量的高低又和關系網絡的規模有關。這種關系網絡就形同于行為主體所賦有的經濟資源一樣,能給其帶來利益。布迪厄還進一步論述了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的關系,社會資本是隸屬于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得益于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交往而產生和維持。布迪厄社會資本的概念強調的是微觀個體(組織)的層面,后來的學者在此基礎上也給社會資本下了一些定義,如佰特(Burt)、福山(Fukuyama):“社會資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聯系,通過他們得到了使用資本的機會……企業內部和企業間的關系是社會資本……它是成功的最后決定者”。布迪厄和佰特(Burt)、福山(Fukuyama)等看到了社會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以及社會資本存在的載體形式為社會關系網絡,然而他們沒有深究社會關系網絡里嵌套的內涵,如社會資本的“互惠”、“信任”、“規范”等。
在布迪厄的文章發表后,科爾曼(Coleman)在《美國社會學學刊》發表的《作為人力資本發展條件的社會資本》一文,用社會資本理論分析美國的經濟行為,目的在于說明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的關系,同時他從社會資本功能角度定義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它不是單一體,而是有許多種,彼此之間有兩個共同之處:它們都包括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處于某一結構中的行動者——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者,和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是生產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實現成為了可能,而在缺少它時,這些目的不會實現。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不是某些活動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與某些活動具體聯系在一起”(科爾曼,1990),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有五個表現形式:一是義務與期望,也即是社會結構網絡中的“相互服務”,科爾曼把它比喻成“義務賒欠單”,這種情形的社會資本存在于可信程度高的社會環境中。二是信息網絡,當關系網內的信息對個體(組織)行動有益時,這種社會關系也就產生了社會資本。三是規范和有效懲罰。四是權威關系。“當某位行動者有權控制另一位行動者的某些行動時,他和后者之間就存在著權威關系。”這種以控制權為特征的權威關系也應當是社會資本的表現形式。五是多功能社會組織和有益創建的社會組織。在這五種形式的社會資本中,前面的四種是社會資本的基本形態,而第五種帶有很強的目的性。科爾曼還進一步說明,社會資本具有兩個性質,一是社會資本的不可轉讓性,二是公共產品性質,這是社會資本不同于金融資本、人力資本的一點。
布迪厄和科爾曼以及同時代的社會學家豐富了對社會資本的理解,認識到社會資本對個人和集體的作用,而真正將此理論運用到經濟學、政治學的是哈弗大學的教授羅伯特·普特南。他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績效的時候,發現南北政府的績效差異除了歸結于經濟現代化的程度上,還與公民生活的差異有很大的關系。他發現在意大利中北部地區公民活動的網絡和規范充滿活力,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紡織品和服裝、家具、農業機械、制鞋設備、優質陶瓷等“集群”(cluster)產業,這些產業在專業化上獲得了規模經濟利益,整個區域充滿著活力。而在南方地區則是一種垂直的政治結構、零碎且孤立的社會生活,以及企業之間、個體之間充滿著一種互不信任的社會文化環境。據此他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解釋這一現象。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組織特點,如信任、規范和網絡等,像其他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它使得實現某種無它就不可能實現的目的成為可能”。普特南在他的《使民主運動轉起來》一書中以博弈論和理性選擇理論為基礎,分析信任、互惠、規范以及網絡等的作用及相互關系。他認為信任是社會資本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互惠、規范、公民參與網絡又能促進社會的信任。最后強調發展社會資本是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有效路徑。
除了布迪厄、科爾曼和普特南這三個旗幟性人物,對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還有大量的社會學家如福山(Fukuyama)、奈克(Knack)、伯特(Burt)、武考克(Wooleock)、林南(Lin)等。同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對社會資本也給出了定義:社會資本是一種自覺形成的社會規則,它體現于社會各組成部分的關系中,體現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之中。它只有建立在民間團體和組織所達成的協議的基礎上才可能是穩定的。聯合國的這一界定內容包含了很多和政治、經濟有關的內容。國內學者楊雪東(1999)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資本是處于一個共同體之內的個人、組織(廣義上的)通過與內部、外部對象的長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認同關系,以及在這些關系背后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價值理念、信仰和行為范式。周紅云(2007)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體中的以信任、互惠和合作為主要特征的參與網絡。程民選教授(2006)從經濟學的視角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人們在社會性相互作用中彼此合作而產生的資源存量。李曉紅(2007)從經濟學角度定義社會資本是嵌入到關系網絡中的歷史傳統、價值理念、行為規范、認知模式和行為范式以及網絡成員獲得資源的能力的綜合。
從布迪厄的社會資本是一種“體制化的關系網絡”,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到普特南社會資本的信任、規范和網絡特點,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實現了一個從微觀到宏觀的過程。從這些定義當中我們可以發現社會資本內核有三方面。
首先,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本”,這種資本與其他資本有共同屬性——對擁有者的“回報”,這種回報體現在對社會產生效益,降低集體的行動成本,有利于行動者達成目標。但它與其他資本的第一個不同點在于突出強化社會關系性和非物質性。傳統的土地、勞動、資本這三者是通過市場媒介交易而得到,有具體的物質形態,在生產中轉化到商品中去而減少。社會資本不會減少反而在生產過程中增加,社會資本的使用其實就是社會關系網絡的互動互惠過程,這樣會增加網絡關系的共識,增強網絡關系的粘度,因此具有規模效應。社會資本跟一般“資本”屬性的第二個不同是“公共性”,只要是網絡關系的參與主體都能使用,具有非排他性。第三個不同點(科爾曼)是“不可轉讓性”或者叫繼承。社會資本的擁有主體不能將其擁有的資本轉移給其他非“網絡關系”的成員或者繼承給自己的后代。對公共性和不可轉讓性,有學者認為(張廣利、桂勇,2003)中西方社會資本理論存在差異,西方社會強調關注“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感性世界”、“人類世界”,“把人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社會資本在西方應該為“個人擁有”或者“為個人得到榮譽”,是屬于私人物品。而在東方對社會資源的分享開始于一個家庭或者一個家族,然后層層推開,正如費孝通說的“差序格局”,在生活環境的圈層中擴散開來。
其次,社會資本存在于一種特定關系網絡(社會結構),或者如普特南說的公民參與網絡(civic engagement network),這種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參與主體源于某種特定的共性,如共同的血緣、共同的職業、共同的地域或者基于某種共同利益訴求,該網絡關系(社會結構)是社會資本存在的“載體”。所以根據“載體”中的成員性質,我們可以把社會資本分為同質的,如以熟人為主體的鄰居、民族、宗教或家庭關系,可細分為家族型社會資本、宗族型社會資本、親族型社會資本、鄉土型社會資本、情感型社會資本等,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封閉性和內聚性。異質性社會資本往往基于現代法理因素而建構,如基于業緣或趣緣關系建構的同事型社會資本、同學型社會資本、戰友型社會資本、興趣型社會資本,也有基于某一公益目的或行業利益目的而形成的,如現代公民型的各類社會團體組織、社會中介組織、各類行業協會、社區共同體等法理型社會資本。Nahapiet& Ghoshal(1998)根據社會資本的結構(結構式嵌入、關系式嵌入、認知性嵌入)將社會資本分為結構型社會資本、關系型社會資本和認知型社會資本三種類型。
第三,社會資本的特征是“信任規范”、“互惠合作”、“網絡參與互動”,這是判斷一個社會關系網絡組織是不是社會資本的重要依據,對于一個市場主體他所參與的異質性網絡的多少及其規模,或者公民參與網絡的“信任”、“互惠合作”、“參與”的互動程度高低是判斷社會資本存量大小的標準。且這里的“信任”、“互惠合作”等特征具有外部性,體現出對社會的正效應,關系網絡的參與主體都可以共同分享信任規范。前面分析的關系網絡是社會資本的“載體”,而對于信任、互惠合作、網絡參與是鑲嵌在社會網絡關系上的“珍珠”,是社會資本理論最有價值的地方。信任共享、互惠合作、網絡參與互動的社會資本特征在經濟活動中,能起到媒介潤滑劑的作用,減少交易的監督成本和信息搜索成本,在公共治理方面,能使得個體的行動與集體的行動達成一致,提高集體行動的協調性。國內學者張可中教授(2005)將社會資本作為外生變量與物質資本、勞動、人力資本共同納入到生產函數中去,分析社會資本期望的生產率是正、零、負三種情況,人們可以根據其效率的情況進行社會資本的投資。這也說明社會資本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有積極的也有負面的,正如陸銘教授說的(2008),假如私人關系與政治權力紐帶連接加強,將會使中國即使有法治,那也算是“人治下的法治”。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社會資本可以這樣定義:社會資本是社會經濟主體參與的網絡關系以及鑲嵌在其上的信任共享、互惠合作、規范特征的一個整體,能給經濟主體帶來經濟利益或者達到其行為目的的資源。
二、社會資本理論與經濟學分析范式
1.社會資本理論的引入,改變了人們對古典經濟學“見物不見人”的批評。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以價格為中心,市場主體在交易過程中是匿名的,交易過程中交易主體的互動行為關系往往被忽略。供給需求定理在經濟學中占據重要的地位,而在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理想預期、公共選擇、博弈論等的興起,使得傳統供給需求分析模式逐漸向經濟主體的微觀行為分析模式轉變。根據亞當·斯密“經濟人”理論,在經濟活動中,各自經濟主體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為中心,市場會自動地趨于均衡。從微觀經濟學分析的范式來看(肖殿荒,2002),(在兩部門經濟條件下)簡記為:C+F。其中C代表消費者,F代表廠商,“+”表示C和F相互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有廠商與消費者的互動和博弈行為,消費者與消費者的互動,廠商與廠商的互動。這三者的互動前提是各種主體相互獨立不存在依附關系,他們是平等的。而馬克思經濟學的分析是從屬范式:L∈K。這里L代表工人,K代表資本家,“∈”表示“從屬于”,工人與資本家分屬于不同的階級,工人依附于資本家,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剝削”關系。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工人、廠商之間的互動博弈行為,是產生社會資本的基礎,也即社會資本在經濟分析范式里是存在的,埃里克森(Rober Ellickson)和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通過多次的經驗研究驗證了社群互動產生規范合作。布斯肯斯(Vincent Buskens)在他的專著《社會網絡信任》中論述“行動者經常交流其他行動者的可信任性,那行動者會限制不信任方式的行動,如果行動者經常了解其他行動者的信任行為,那么信任將在他們之間生長”,他得出社會關系網絡互動交流促進社會信任產生的結論。但傳統的西方經濟學分析框架里存在的供求平衡范式:QL(P)=QS(P),需求QL(P)(消費者:MaxU(X),s.t:P(X)=I)可以看成消費者在一定的收入約束下實現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供給QS(P)(生產者:Maxπ(X),s.t:F(X)=C)是廠商在成本約束下,實現利潤最大化,最后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相互博弈互動實現了整個市場的均衡,這種傳統的分析范式忽略了在達到均衡前生產者內部、消費者內部的互動博弈行為,這一切被放到了約束集合外面。社會資本理論強調“網絡參與”、“信任”、“規范”對行為主體經濟行為的影響,其實是將這一切社會關系網絡特征納入了消費者、生產者行為約束的集合里。
2.社會資本理論將經濟行為主體“價值判斷”、“文化認同”作為內生變量引入到經濟生產函數。社會資本“網絡關系”的基礎就是要網絡參與和網絡互動的個體(組織)對網絡關系價值、文化、理念的認同。傳統經濟學理論在“經濟人”假設、“收益成本”的影響下,對經濟行為的分析更加實際,利益最大化是其行動的目的,忽略了對人性的關懷。這種批評的聲音在古典經濟學里也早就有了(楊雪東,1999),亞當·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論》中就說道,市場還需要道德情感的支持,大衛·休謨認為“道德情操”、“同情心”會支持經濟行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團結”,齊美爾的“互惠交易”,迪爾凱姆和帕森斯的“價值融合”,韋伯的“強制性信任”都強調經濟活動的互動能產生共同的價值認同,而價值認同能促進經濟目標的達成。傳統的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價值認同能減少交易成本,減少信息的搜尋成本,有利于交易的達成,社會關系互動結果產生了價值判斷、信任、規范、文化認同,而這個互動的結果又有利于經濟活動,這也是一些學者對社會資本到底是經濟活動的結果還是內容所存在的爭論。
3.從現有的文獻資料看,社會資本理論從微觀到宏觀,強調個體的選擇行為對集體行動的影響,這是新制度經濟學一直所追求的分析范式,社會資本在理論上完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夙愿。在經濟分析中(殷德生2001),如何實現個人的理性與社會集體的理性協調,以及制度能否實現集體行為的一致,這不僅取決于制度和微觀主體,還取決于連接雙方的媒介(社會資本),在經濟活動中,個體不僅要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還要獲得集體認同,這兩個需要往往由于制度的滯后或者斷層無法調和,而社會資本可以起到潤滑、媒介、緩沖的功效。
在現有的制度經濟學理論里,對制度變遷、產權的界定,實際上是把制度作為供需雙方的經濟產品來分析。一般來說制度的供給者是當權者,需求者則是受約束的大眾,而社會資本從經濟學的供給需求(社會資本的“資本屬性”來看)視角來看,橫向連接的社會資本網絡,網絡參與的主體既是供給者也是需求者,對于縱向的科層組織的社會資本,帶有強制性,供給者是網絡結構的權威,需求者是在這種科層組織下的每個節點。據此很多學者將社會資本歸納為一種非正式制度,或者說社會資本是通過非正式制度形式作用于經濟發展。這樣簡單粗略的對社會資本進行屬性判斷是有待商榷的。
三、社會資本理論與非正式制度
社會資本與非正式制度屬于不同的范疇,兩者應該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1899年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寫道:“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生活方式所構成的是在某一時期或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通行的制度綜合,因此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可以概括地把它說成是一種流行的精神態度或一種流行的生活理論”[13]139,凡勃倫的“一般思想習慣”、“流行的精神態度”其實暗含了制度是人類生活的積淀。后來康芒斯認為制度是“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14]87,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中寫道:“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的一系列約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約束(道德的約束、禁忌、習慣、傳統和行為準則)和正式的法規(憲法、法令、產權)組成的”[11]3,從制度的表現形式來看,諾思將制度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從以上對制度的定義(產生)來看,原始制度(非正式制度)是置身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行為方式或習慣,而這種方式和習慣通過實踐的積累推廣開來為更多的人認同遵守,隨后以法律法規的形式確定下來成為正式制度,這里的社會關系(或叫生產關系)又是產生在特定的生產力的基礎上,這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法律法規制度或者是生活習慣都是上層建筑的內容。它來源于生產關系又作用于生產關系。從社會資本對經濟行為的作用來看,是屬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范疇,一方面它直接作用于生產關系中的經濟活動,給社會資本的擁有主體帶來利益回報,另外社會資本所形成“規范共識”又會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作用于經濟活動。這正如陸銘教授(2008)所說的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兩條路徑,一條類似于物質資本直接作用于經濟增長,另一條表現為非正式制度影響參與人的激勵、預期和行為間接作用于經濟增長。歐曉明、汪鳳桂(2011)認為社會資本與非正式制度存在信任、習俗、規范等交集,社會資本對企業的發展通過三條路徑,一是影響企業的管理理念,二是對企業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發揮增效作用,三是對非正式制度激勵與約束影響,最后影響企業的發展。據此有的學者(李曉紅、黃春梅,2007)將社會資本分為制度屬性的與資本屬性的。
社會資本個體“共同”關系網絡與非正式制度所處的社會關系網絡是有區別的。諾思所定義的非正式制度是指在某區域或一定的網絡組織中被廣為認同和接受的習慣習俗、倫理道德、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梁碧波,2010),由于這種信念已內化為行為主體的行動指南,故某一區域或族群內的人們在決策或選擇行為中自覺地接受這種非強制性的約束,或在行為過程中體現出某種“共同的傾向性和相似性”。顯然,這種“共同的傾向性和相似性”就是民族文化、民風習俗的投射或沉淀,是在長期生產交往中形成的,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并且作為下一代的民眾,無論你是自愿還是不自愿都要認同于這種約束。社會資本特征是關系網絡參與,關系網絡個體之間的信任互惠,從其產生來看,構成社會關系網絡不同個體是源于某種“共性”,這種“共性”在中國可能是緣于血緣、學緣、同鄉、同族等,或者是緣于共同目的(如社會組織),是出于某種“利益”或者為了達成某種行動目標而結成。因此從產生的動機來說社會資本與非正式制度存在著差異。
[1]殷德生.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一個理論綜述[J].南京社會科學,2001(7).
[2]黃銳.社會資本理論綜述[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7(6).
[3]楊雪冬.社會資本:對一種新解釋范式的探索[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3).
[4]肖殿荒.勞動價值論研究的三個課題[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5).
[5]沈昊駒,肖殿荒.微觀經濟學基本范式的轉變[J].金融教學與研究,2009(4).
[6]陸銘,李爽.社會資本、非正式制度與經濟發展[J].管理世界,2008(9).
[7]歐曉明,汪鳳桂.社會資本、非正式制度和農業企業發展:機制抑或路徑[J].改革,2011(10).
[8]李曉紅,黃春梅.社會資本的經濟學界定、構成與屬性[J].當代財經,2007(3).
[9]梁碧波.民族文化的制度含義[J].青海社會科學,2010(1).
[10]周紅云.社會資本與中國農村治理改革[M].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07.
[11]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2]盧現祥.新制度經濟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13]凡勃倫.有閑階級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14]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15](美)普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6](美)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17](法)布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責任編輯:龍會芳;校對:盧艷茹)
F035
A
1006-3544(2015)01-0019-05
2014-12-31
鐘君(1985-),華中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興義民族師范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農村經濟、發展經濟學、金融學;曹陽(1955-),男,華中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農村經濟、勞動經濟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