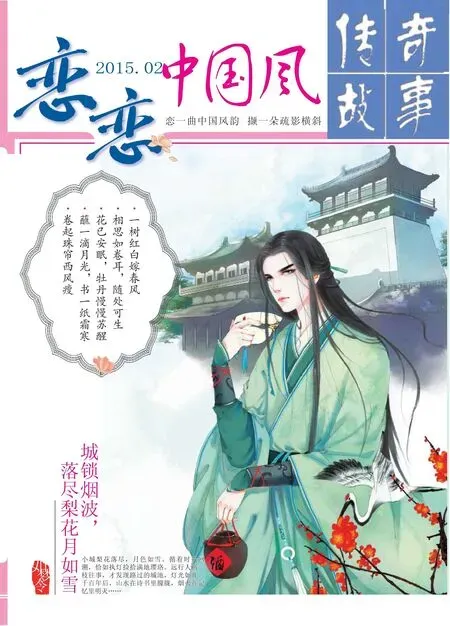匆匆一瞥,年華似水
◎張溪琳
匆匆一瞥,年華似水
◎張溪琳
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
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
往事后期空記省。沙上并禽池上暝。
云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
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張先《天仙子》
張子野寫這首詞時,已經52歲了,在浙江嘉興做判官。從整首詞中并沒有看出張子野“病”在何處,所以,與其說是病,不如說是一種倦怠與憂愁。
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紀,看著春天匆匆而去,一切屬于年輕的繁盛美好,都隨之靜靜流走,突然發現自己已送別了無數個相同的此時。一個暮春的午后,在家中安靜地坐著,想念著,許多過往如潮水般不期而至。翻開已泛黃的時光,閱讀那些遙遠年華里的歡樂與沉重,生命畫面里停留的瞬間,只是匆匆一瞥,竟已幾十年。
春日深處,百無聊賴地聽著水調樂曲,旋律悲怨凄苦。自斟自飲間,伴隨著纏綿憂傷的曲調,心尖的愁緒洶涌而至。“送春春去幾時回?”今年的春天又走到了盡頭,不知明年春天是不是還在這里為我逗留,也不知道我還要為她的到來等候多久?可是,不管她要走多遠多久,總會再回來的,可是我走失的青春和遠行的華年,卻再無音訊。我為此已等待了半生,也許它們已經回歸到時光的另一個盡頭,如今正與我遙遙相望,卻再不能相逢。
杜牧曾說:“自悲臨曉鏡,誰與惜流年?”他就是這樣悲傷著自己的悲傷,看著鏡中已暗暗改變的容顏,尋找時光在臉上行走時留下的細微痕跡,恍然間才發現已遺失了多少流年。鏡子是最真實也最殘酷的事物,不管你是青春少年,還是白首衰顏,都毫不隱藏、真切地映在眼前。天涯倦客,心像孤單小船,因為漂泊太久,揚起的風帆已殘破不堪,遠景不見,船艙里只存放著不可留守的昨天和無法擺脫的思念,在煙波浩渺的時光里懷想當年,追悼從前。
起身走到窗前,薄紗般的月光在水面蔓延,漾起一層清輝,一雙鴛鴦在上面依偎著閉目而眠,它們不懂寂寞,因為每一次輪回都是相伴。時間在它們身上變得緩慢而安閑。晚風是黑夜沉沉的呼吸,很多白晝里不可抒發的紛擾情緒,在這細微的吐納中得以蘇醒。它撕破云朵的籠罩,回轉在每個不可知的角落,于是還沒來得及睡去的花朵,就在其中輕輕起舞,微風時時撩撥著它們晃動的身影,安靜的夜幕下生命有聲有色。
站在小樓里,透過重重的簾幕看著遠處若隱若現的燈火,在風聲中飄搖不定。它們恍恍惚惚徹夜地亮著,亮得讓人心碎。仿佛已經過了幾個世紀的變遷,只剩下我孤孑一身,在容顏盡改的今天。殘紅無數,雖然是明日之景,卻又是那么凄涼而真切,落花飄零,綠肥紅瘦,酣眠之中,雨打梨花深閉門,夢里花落知多少。
一個人追憶年華,太過寂寥,就讓所有周遭的事物同悲同樂。張子野在一個時間的轉角處,沒有找到寂寞的出口,卻讓世間萬物產生了懷舊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