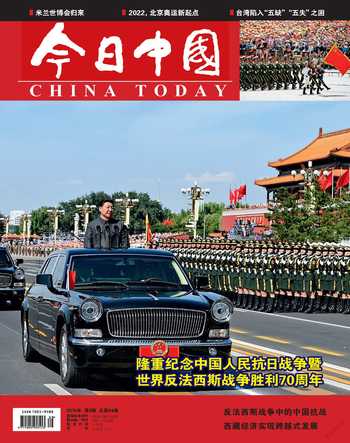導演誰都能當嗎
文|唐元愷
導演誰都能當嗎
文|唐元愷
電影界大可不必“拿破侖”:不想當導演的不是好影人。但“導演”意味著啥,想必圈內誰都清楚,于是爭當導演者前仆后繼。如今,作家歌手主持人經紀人等也紛紛“新血”來潮,搶導筒搶飯碗。高群書等影人則發炮:現在中國影壇怪現象之一就是—誰都可以當導演,“只要有人給你運作”。
曾經,當上導演可非易事。1955年,國家電影局以文件形式公布提拔謝晉(時年32歲)等4位年輕副導升任導演,當時屬轟動事件;到了1983年,電影廠大都還在論資排輩,應屆科班生就算一帆風順,一般也要當助手十年八載后才有望獨當一面,直至廣西廠破格批準成立全國第一個“青年攝制組”,使幾位剛畢業不久的幸運兒不用執行“少林寺規則”(從掃地干起),“獨立”創作《一個和八個》(中國電影“第五代”開山之作)。而該片攝影張藝謀又過了幾年才在37歲時首當導演
而在手機相機都可“拍片”的時代,票房為王、電影“賤賣”的當下,導演的門檻越來越低,被一些影迷諷刺為“只要你能賣,賣什么都行—賣資源、知名度、影響力、營銷點或什么都沒有,你爹是煤老板也行”。事實也許沒這么極端,但《青年電影手冊》主編程青松就曾“聽說”一些事,如片場一跨行新導不是在導片子,而更像探班,很多導演在幫(替)他工作。當然,這屬于“周瑜打黃蓋”。程主編認為,跨行新導的涌入從表面看繁榮了電影創作,但實際上卻是近年圈內太過急功近利的表現,“這些人有粉絲,大家覺得只要掛他們的名字,就能一下子撈到很多錢,這對那些真正有才華卻苦無機會的青年導演很不公平!”還有專家指出,此類怪象背后是粉絲經濟取代觀影文化、明星效應掩蓋導演藝術、營銷思維勝過片場耕耘的反映,均有損電影發展與精品創作。
電影界大可不必“拿破侖”:不想當導演的不是好影人。但“導演”意味著啥,想必圈內誰都清楚,于是爭當導演者前仆后繼。

不過不管怎樣,電影圈不論出身不講血統畢竟是件好事。觀眾“吃了好吃的雞蛋”,也不會追究是哪個“母雞”所下。導演只是最體現創造力與執行力的“職業”之一,并不分“白貓黑貓”。臺灣新電影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楊德昌當導演前,是赴美留學生,獲得的是電子工程碩士學位;懸念大師希區柯克并沒受過正統電影或戲劇訓練;鬼才塔倫蒂諾則是一家錄像租賃店店員今已110歲歷經7代以上的中國電影急需新鮮血液,亦需跨界沖擊,而“英雄何問出處”,應樂觀其成頭腦中無框框心里無清規束縛的新“勢力”不斷涌現。事實上,每年登上影壇的新導演為數不少,只是總體上佳作不多,盡管其中不時有跨行導演讓處女作票房輕松過“億”。曾任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秘書長的何平導演舉2013年的例子說,當年國產片產量700多部,第四代導演作品只有1部,第五、第六代則分別只占不足6%和4%,剩下600多部全是年輕人執導的。
“年輕導演機會不少,卻沒有真正誕生出優秀人才和作品。”何導演直言,中國電影不缺導演,但確實又缺導演,既缺30多歲就能拍大電影的走市場路線的導演,也缺賈樟柯、王小帥那樣始終堅持藝術理想的導演,“我們缺這兩頭,盛產的是中間的部分,所以才會把一些電視節目變成電影。”數字時代,拍電影變得越來越“容易”,這導致不成熟作品的早產,以前膠片時代,拍片成本很高,一位導演要覺得“準備”得很好了才會去做,投資人才可能給他投錢去拍。
準備,其實是導演的常態,包括專業的準備,或者說儲備,許多優秀導演并非科班出身,但并不代表導演無需“專業”。還有人生積累與體悟,技術打磨與試驗等等。即便天才也非一蹴而就。中國臺灣著名導演李安當家庭煮夫的幾年,“業余”時間幾乎全用在了寫劇本和拉片子上(他通讀世界電影史,并按書中片目反復研習經典影片)。
俄羅斯名導薩金塞夫在任2015年上海電影節評委會主席期間,告誡年輕人別急著當導演,“應多做些積累,尤其是技術層面上的,這對年輕人是最重要的。”其本人2003 年從演員轉型為導演,執導第一部長片《回歸》便拿下威尼斯電影節最高獎“金獅”,卻已39歲“高齡”。他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如果自己年輕10年,很可能拍不出這樣厚度的影片,“太年輕的人,他們的生活沒犯過太多錯誤,沒有失去什么,也無法體會到一些人生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