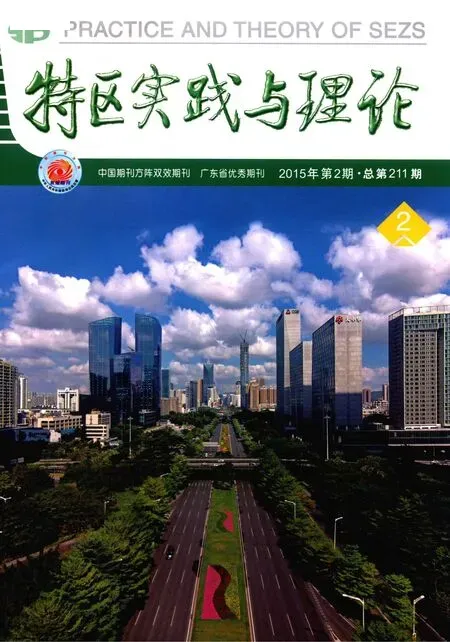論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
范宏云
香港基本法賦予提名委員會獨立的憲制地位,提名委員會不隸屬于任何部門,它是一個單一政治職能的機構,就是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會是一個委員會制的機構,委員會制不同于首長制,委員會制是一個代表機構,它的組成應該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同時委員會制的決策原則也要求具備充分的民主性。香港基本法第45條規定普選行政長官要先由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但是基本法對該“民主程序”沒有作進一步的細致規定。在首輪政改咨詢期間,香港社會各界對于“民主程序”的具體含義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社會主流意見傾向認為“民主程序”是指提名委員會內部民主的議事決策規則。民主雖然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問題,但是,民主的本意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程序的本意就是方法和步驟,故民主程序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和步驟,這一點已經構成國際社會的共識。因此,多數決定制是提名委員會決策的基本原則。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民主程序”就是提名委員會按照少數服從多數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方法和步驟。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程序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多數制投票表決是貫徹落實該基本原則的必要方法和機制。選擇什么樣的投票表決機制來貫徹落實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不僅是民主程序設計中的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政治與法律問題。
一、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的基本原則
民主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原則)。羅伯特·達爾在其《論民主》一書中指出多數原則體現了人民主權和政治平等,和其他決策機制相比,多數原則更能夠保護少數,因為少數派更容易形成聯合以推翻他們不愿意接受的結果。任何社會秩序、社會組織機構內部的秩序,以及為維護或變更這種秩序而制定的法律、決議、規章制度和政策等,在實踐中不可能在每一條文、每一個細節上都百分之百地為全體社會成員或某一社會組織機構的全體成員所一致贊同或執行。既然如此,社會全體或組織機構的全體成員在制定法律、規章制度時,就只能盡可能照顧到多數人的意志。在通過這些法律規章與重大決策的時候,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表決,要求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意志,并由多數人的意志來代表社會全體的意志和整個機構的意志。這種以多數人的意志作為全體代表的主張,是社會全體或組織機構全體共同遵守的原則,是切實可行的民主原則。
有人認為,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犧牲了少數的利益,這沒有體現民主。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對于處于服從者地位的少數來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并不意味著多數人的絕對統治,不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獨裁,而恰恰是民主”。[1]因為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承認了少數存在的權利,保障了少數的民主參與權利,少數雖然不得不放棄或保留自己的意見而服從多數,但是這種服從是以事先的民主參與為前提。“雖然通過的決定沒有反映或沒有完全反映少數的意志,沒有采納少數的主張,這不是他們所愿意的,但不能因此說這就是不民主。因為雖然少數人的意志不能合法地代表全體的意志,但是他們還是作為參與決策的一分子享受了自由發表意見與進行投票表決的民主權利,因此,他們的主張也多少有影響多數人的意志的可能,從而可以牽制或防止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意志與利益的絕對漠視。在真正民主的制度里,多數也必須尊重少數,保護少數,聽取少數人的合理意見,容許少數人有保留意見的權利。至于少數自愿地服從多數,也是少數人享有民主權利的表現。”[2]
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離不開多數表決制。正是通過多數表決制,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才可以轉化為社會整體或某組織機構整體的決定或意見。多數表決制通常有兩種途徑:一是絕對多數,絕對多數是指出席人數的三分之二、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以上,才能通過。如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反過來說就是只要三分之一以上的反對,就不能通過。這就是說是這三分之一的少數迫使多數人服從他們。三分之二的多數要尊重這三分之一的少數。絕對多數制適用于決定特別重大問題,但是存在某項決定不獲通過的危險。二是比較多數。比較多數制只要出席的法定人數中過半數,即可通過,又叫簡單多數。比較多數制使決定較為容易獲得通過。但有時會產生少數人即可通過決定的弊端,因為凡出席過半數即達到會議的法定人數,而通過決定時又只要出席者中的過半數,這樣,即只需超過全體人數的四分之一,就可以通過議案。四分之一這個少數即變成了多數,代表了全體。在英國,上議院有九百人,按照議事規則,只要有三人出席就達到法定人數,于是兩人贊成即可通過議案,按此辦理,則兩個人代表了九百人。當然,實際上上議院在習慣上是由三十人出席才開會,眾議院則只要達到法定人數四十人,即可開會。這仍然是少數代表了多數。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形,有些投票制度規定,無論出席會議人數多少,只要贊成票超過全體人數(包括出席會議和沒有出席會議)的一半,決定才獲得通過。比如,由1000人組成的委員會,委員會決定必須以過500票的有效票通過,無論出席會議的人數是501人還是1000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少數服從多數的真正民主,才能保證通過的決定或獲得當選的人具有認受性。
少數服從多數同樣是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應該遵循的原則,多數表決機制是該“民主程序”的基本方法和步驟。提名委員會作為一個由眾多提名委員組成的單一政治職能機構,其功能就是依照投票權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形成提名委員會的意志和決定,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在提名委員會制度下,對于愛國愛港人士,無論他是屬于某個政黨或政治團體,還是獨立的社會人士,人人都有平等的被提名的機會,人人必須接受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和多數制投票表決機制的檢驗,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提名委員會的正式提名。提名委員會必須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程序”,因而就不可能做到事先確保任何人獲得正式提名。但是,反對派和某些社會團體認為,只有確保少數派獲得正式提名的程序才算是“民主程序”。如香港大律師公會政改意見書認為,“如果一個人只有獲得提名委員會簡單多數的通過才能被提名,那么政治上的少數派不可能會有真正的合理的機會參選,以確保選民自由和真正選擇候選人的機會”。顯然大律師公會意見書的觀點是,確保少數派“出閘”的程序才是民主的程序。正如上文所述,任何人都必須經過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和多數投票機制的檢驗,任何提前確保某個人或某個少數派人士“出閘”的程序不僅違背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而且使提名委員會的民主陷入“人人說了算”、“人人說了又不算”的癱瘓局面。
二、多數制投票制度分析
體現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投票制度,即多數制投票制,目前在選舉實踐中經常被采用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領先者當選制。領先者當選制是多數制的最簡單形式,得票最多的一名或幾名候選人贏得選舉,即便當選人沒有得到絕對多數的有效票。采取該制度,在議會選舉中對大黨有利,容易導致兩黨制,如英國國會選舉。在國家元首或行政領導人選中,有可能導致當選人的認受性不足。如1987年韓國總統選舉,在野黨候選人金大中、金泳三的主要支持者重疊,導致選票分散,于是執政黨候選人盧泰愚以不足40%的得票率當選總統。2000年臺灣地方領導人選舉,國民黨籍連戰和無黨籍宋楚瑜的主要支持者重疊,導致泛濫選票分散,于是在野黨民進黨籍陳水扁以不足40%的得票率當選。
二是兩輪選舉制。兩輪選舉制指選舉無法一次選出結果,采用兩輪投票的選舉制度。如果沒有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中得到一定比例的選票(常常是過半數),那么就進行第二輪投票。法國的總統和議會選舉都采用兩輪選舉制。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中得到過半數選票的候選人當中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法國國民議會選舉,如得票過半數即可當選。兩輪選舉制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領先者當選制票源分散當選者認受性不足的困境。
三是排序復選制。選民在選票上把候選人按照自己的選擇排列優先次序,計票時,首選位最少的人被淘汰,其得票按照排序復選制的規則分配給余下的候選人,取得過半數的候選人當選,其選票也按照排序復選制的方式再分配給其他候選人,計票程序按此進行下去,直至選出所有席位。排序復選制會導致與領先者當選制不一樣的結果。如圖,只有B>C>A是把B排在第一位的,因此B是最少選票(10票)放在第一位的,所以直接淘汰B,于是12張選票選擇了A>C,有10+11=21張選票選擇了C>A,按照排序復選制,C獲勝。

但是,如果是只記首選項的話,按照領先者當選制,則是A當選,而A的得票率實際上只有36.4%,屬于少數當選。如圖:

排序復選制雖然能夠克服少數當選的局限性,但是多次計票會增加選舉結果的不確定性。有時會存在“黑馬”在后幾輪逆轉取勝的情況。排序復選制還可能選出激進的候選人。比如某個激進分子得到30%選票而其余7個溫和候選人由于搶票而每個人只得到10%的選票的情況。也可能會埋沒一些有廣泛群眾基礎的人。如果某提名參選人是大量投票者的第二選擇,但可能很少人把他作為第一選擇,這樣,他在第一次計票中就被淘汰了。
四是全票制(全額連記制或多議席多票制)。全票制適合于多議席選舉或多人當選。投票者擁有與既定當選人數相等的選票,得票最多的前幾名候選人當選。假設要從七名候選人中選出三人,每名投票者擁有三張選票,以得票最多的前三名候選人當選。該制度可以使群眾基礎最廣泛的提名候選人在提名中獲勝,減少偏激的候選人勝出的機會。它比領先者當選制更能體現投票者的態度。全票制鼓勵那些原本因為無法做出唯一選擇而干脆放棄投票的人參與投票。例如:有42名支持A但不愿意放棄B的人選擇了A和B,有58名最想支持C但不愿意放棄B的人選擇了C和B,于是B得到42+58=100票并勝出,而A只有42票,C只有58票。投票結果:B得票最多,B獲勝。
上述案例,如果改成每張選票只能寫上一個人的領先者當選制。

投票結果:被多數人所喜歡的C獲勝。而在可以多選的全票制下,C卻會輸給B。
如果投票者不選擇某個候選人的話,也可能會使他更偏愛的人落選。例如:

三、“過半數”的提名委員會投票機制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了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2017年普選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重大決定,決定指出提委會必須由多余半數決定候選人名單。基于行政長官應向中央政府負責和向香港特區負責,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全國人大決定是具有權威性的法律文件,也是設計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和投票機制的指導性文件。根據全國人大決定,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不僅僅是一個民主程序設計的技術性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中央在香港特首普選問題上已經明確了政治底線,那就是香港特首必須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簡單地說,必須設計一套既符合民主、又有利于“愛國愛港”人士出線的民主程序和投票機制。首輪政改咨詢期間,香港社會各界針對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設計了多種投票方案。泛民團體方案都是確保泛民代表“出閘”的方案,如香港2020方案、18學者方案、真普聯方案、學界方案等。湯家驊曾建議采用排序復選制,正如上文所述,排序復選制的選舉結果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不能派出泛民代表“出閘”的可能性。建制派方面設計的投票機制大都利于“愛國愛港”人士出線。如民建聯、工聯會和鄉議局提出的全票制加過半數方案,但是全票制容易導致票源分散,如果提名委員會中的建制派支持票分擔,就不能派出泛民人士“出閘”的可能性。新民黨、自由黨、經民聯提出領先者當選制,即提名委員會一人一票,得票最多的三至四人出線,毋須過半數。在此方案下,如果建制派提委選票分散,泛民人士有非常大的“出閘”機會,而且毋須過半數也不符合人大決定的精神。
饒戈平教授提出的“逐個陳述、逐個表決”方案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逐個陳述、逐個表決”是一種“一一過關”的贊成投票制。具體而言,提名委員會確定參選人選之后,要求每個參選人向提委會陳述政見,以保障全體提名委員的知情權,以及保障參選人的陳述權利。之后,提委會逐個表決,結果公開,選票最多的N個參選人可成為候選人。根據饒戈平教授的初步設計,該方案嚴格依照基本法和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也符合“公平、公正、公開”的“三公原則”及羅伯特·達爾關于民主程序的標準。全部過程向社會公開,有助于體現全體選民對提名委員會工作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逐個陳述、逐個表決”可以說是既民主又安全的投票機制。“逐個陳述、逐個表決”方案泛民人士幾乎沒有“出閘”機會,因此該方案必然會遭到泛民陣營的極力反對。為了減少阻力,提名委員會的投票機制可以選擇“逐個陳述、逐個表決”和兩輪選舉制相結合的方案。具體操作如下:第一輪可以采取較低門檻,目前比較多的意見是八分之一委員推薦,就可成為參選人,此階段可能有一至兩名泛民代表成為參選人;第二輪采取“逐個陳述、逐個表決”,獲半數支持才能出線,成為正式候選人,泛民參選人根本無出閘可能。這樣設計的好處是,第一輪設計照顧了泛民的參與要求,第二輪設計保證了中央政策底線的絕對安全。
[1][2]郭道暉.論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制[J].政治與法律,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