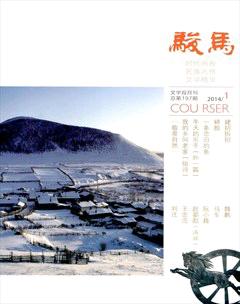“敬畏自然”
劉遷
“敬畏自然”,這是呼倫貝爾文聯(lián)原主席馮老國仁先生對《駿馬》“走進根河”專號主題的評價。他說這個“專號”是他組建文聯(lián)、創(chuàng)辦文學期刊以來,質量最高的一期。他在仔細閱讀所有作品后,使他長久以來從民俗角度認識多神(教)意識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多神(教)意識實質則是“敬畏自然”!我以為,他的這一認識,把表面化的文化認識提升到哲學層面。
今年夏初,根河市委和政府與呼倫貝爾市文聯(lián)聯(lián)合邀請一批實力派作家到“冷極”根河訪問,《駿馬》編輯部將這批作家的作品集中發(fā)表,因此有了這個“專號”。我讀了,很感佩。于是推薦給馮老。他帶著這個“專號”去扎蘭屯市避寒,到了目的地,不到一周,就讀了所有文章,并立即給我打電話,說出了令我振聾發(fā)聵之言。
“冷極”之命名且有標志性建筑,作家采風團在這個抽象建筑前留下了歷史性合影。遺憾的是1976年我曾到過金河,失之于無緣吧。去年中央電視臺在12月和1月份,連續(xù)報出根河、圖里河連續(xù)低溫,總是在零下四十幾度,令全國各族人民印象深刻。其時我還調侃寫了一首詩,首句就是“呼倫貝爾出名了”。其實,未在呼倫貝爾市經歷過嚴冬的,就不知道這里酷寒。現(xiàn)在人們知道這里冷,是由于媒體傳播的快捷、全面和真實。我本人在1966年歷書意義上的初春的3—4月份,就在草原馬背上沐浴過-50℃——查資料,沒有獲得支持。其時雪霰彌漫,天地渾沌,記憶深刻。這似是題外話了。在呼倫貝爾人看來這并不算是題外話,尤其是對曾經長時間在大興安嶺中以及其西側廣袤大草原上從事狩獵和游牧的人們來說,一年就要過七八個月的冰雪之“冬”。狩獵的鄂溫克人,數(shù)百年生活就與這峻美的大自然和諧共處,創(chuàng)造并保存了人類的狩獵文明經驗。
鄂溫克人狩獵文化經驗,是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在當代首先作了形象、真實而生動的展現(xiàn)。我在研究他作品時,曾經認識到,他所提供的狩獵文化經驗是對工業(yè)化及其后人們(中外并不例外)奢侈消費大自然的反撥。我感到對他的作品的價值,不僅研究不足,時而還有誤讀出現(xiàn)。所以,前幾年《駿馬》主編姚廣提出一個設想,即“重讀烏熱爾圖”。我認為這是個極富見地的構想,極表贊同。現(xiàn)在,大概是時候了!
魯迅文學院資深教師劉小珊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說出一個結論性意見:烏熱爾圖屬于當代中國文學。三十年后再來思考這個結論,無疑現(xiàn)實意義更強了。人類走過狩獵時代、農耕時代、工業(yè)時代,并在每個時代都創(chuàng)造了其時的燦爛文明——或曰生存經驗。時代在發(fā)展,人類此前所創(chuàng)造的一切有價值的經驗都應該成為我們再前進的精神財富,或曰多元文化共融共存,以創(chuàng)造人類更美好的未來。而在當今,烏熱爾的小說則是狩獵文化生活的唯一。
現(xiàn)在,面臨嚴峻的生存環(huán)境提出了“建設生態(tài)文明”戰(zhàn)略思想,正因為有了這一指導思想,我們今天才能夠較為深刻、正確理解敖魯古雅存在的寶貴,它的文化價值和意義,以及它對我們哲學思想的啟迪與提升。
作家們走進敖魯古雅,他們是真的俯下身子,感受鄂溫克人具體的生活環(huán)境,認識鄂溫克人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生存方式,體悟鄂溫克人思想的哲學本真,還有,他們認識了幾位真實的鄂溫克獵民朋友。這些都在他們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們確認了狩獵文化的“敬畏自然”的本質,從人物、生活、環(huán)境等多個方面體認這一寶貴文化意識。因此,他們的作品深深地感動了馮國仁老先生。
耿立文章的題目就極具認知:《你不是鄂溫克,你不知道樹》!他認識了安道老獵人,“安道老人用作燒火的劈柴,都是在森林找的枯死的樹,鄂溫克人從不伐還生長的樹做柴燒。”他深具卓識地寫道:“其實他們敬畏的就是一個神,這個神就是自然。他們對自然充滿敬畏,順從自然,不背拗,不狂妄,不貪婪,不過分索取,于是收到敬仰的神就賜予他們更多,讓他們得以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從而他能說出這樣的話:“也許在老人看來,文明人也在退化吧。”
周曉楓同樣的認識采取了批判性述說:“而我們,這些看似精明卻不夠真正聰明的城市人,對世界習慣占用而從不償還……我們從子孫那里透支未來,而且在視力所及的后代那里根本不可能償還的,我們依靠不正義的壞賬過活。”
兩位作家向現(xiàn)代人提出了一個現(xiàn)實大題目:現(xiàn)實的人們,你應該選擇進化還是退化?曹雪芹有言,聰明反被聰明誤。無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無悔改地污染空氣污染水源,為蠅頭小利破壞草原,為填不滿的私欲大肆砍伐森林……是愚蠢,從人類整體生存而言就是退化!這是人生的大經驗。如果有大自然法庭,就應該給這類人以取消地球球籍的判處。
幽默的鮑吉爾·原野說,“在根河行走,我每每想起這句話——‘離白云只有三指寬的距離,這是從肚臍到下面關元穴的距離”。要知道,這個位置正是人生命攸關的地方。作家的精神潛質令他心靈感知:“根河的云朵從養(yǎng)狐貍的磚房的屋脊后面升起,離屋頂?shù)臒焽柚挥腥笇挕T贫涞暨M葛根河的流水里,離山楊的倒影只有三指寬。”“露珠大概在和離自己‘三指寬的距離的另一顆露珠談戀愛。”因為,他心中裝著維拉索老人的鹿甲勺和涂爸爸天火的傳奇故事;故事讓他走進了鄂溫克人的狩獵文化層,并在這個層面獲得了最大的自由。
讓我們來聽一聽詩人的吟唱:“罌粟是藥,也是毒∕這些,誰不知道∕可是你,一點兒也沒有毒的樣子∕只是一朵花的樣子∕只是站在那里∕長莖上纖細的絨毛晶亮剔透∕你朝我微笑,羞澀如少女∕∕你就是一朵花∕藥是人∕毒也是人∕和你沒有一點兒關系∕你,就是一朵花”(《根河的事物·黃罌粟》)不記得在何處讀到過,說人是上帝也是魔鬼。信然!詩人看到了人的異化,異化到失去了自己。“像一棵微型的樹∕你筆直地站在那里∕都說鳶尾是會唱歌的∕你會唱歌嗎∕你唱的歌是否藍色∕∕我彎下腰,去傾聽你的歌聲∕卻沒有聽到∕是我的耳朵不清潔嗎∕我用礦泉水洗耳∕仍然聽不到∕是水有問題嗎∕我用離你最近的河水洗耳∕仍然聽不到∕∕不再傾聽∕我知道是我有問題∕我的耳朵長了這么多年∕帶來了太多的污垢和灰塵∕它不配聽到你的歌聲” (《根河的事物·鳶尾》)
而瑪麗亞·索她會唱“跟馴鹿學的歌”。瑪麗亞·索還唱了這樣一首歌:“藍天藍天你好嗎?還好嗎?我們是天上飛翔的鳥兒啊!河水河水你好嗎?還好嗎?我們是水里游動的魚兒啊!”(葉梅《根河之戀》)這是薩滿與神的對話。這就是鄂溫克獵人的耳與心。“精明”的現(xiàn)代人丟失了曾經有的耳和心了。endprint
一位作家說,森林不是屬于人的,而人則是屬于森林的。這說出了人和自然的“血緣”關系,也挖掘出了其責任與義務。人類是森林的孩子,森林養(yǎng)育了人,智慧的人就應反哺森林(自然)。當今社會上有一些所謂的“啃老族”,這使我想到了同樣還有“啃自然”一族。曾聽說某位掌了權的要人當眾宣稱:老子都活不下去了,誰還能管得了下一代!為了挖蟲草破壞藏地高原草場,為了挖發(fā)菜令內蒙西部草原日趨沙化。天空被霧霾遮蔽了,河被污染了,早被國家列入淘汰的企業(yè)還在變戲法兒地“上馬”再“上馬”;你看,典型的“啃自然族”!人們呀,不要再當啃自然族了,否則你將不會再有好日子過了。
萬物皆有靈,萬物皆是神,這不是迷信。自然是人類的衣食父母。人類對自然就應虔誠敬畏,就應和諧共生共處。
艾平在《姥爺?shù)纳健分杏袀€謎一樣的細節(jié)。“姥爺還在說著話:‘我知道你在……我給你賠個不是不行嗎,見面的時候我給磕頭不行嗎,我知道我欠你的,我也不想吃你喝你,你心疼,我的心也疼啊,你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孩子也是孩子啊……就到了,就到了,你也歇歇腳……姥爺?shù)脑捲评镬F里,好像是跟山神說的,又好像是跟老查干說的。”姥爺與山、泉、樹、草和老馬都是密友至親,都是骨肉兄弟,一切都是商量著做,心懷歉疚在做(索取)。他親他們,敬他們!
作家們用不同的述說,表達了他們在冷極收獲的對大自然的敬畏之純情。我相信他們會永遠受益,我更希望他們更明確更具影響地把狩獵文明的現(xiàn)實意義和永恒價值傳播開去。
這一批實力派作家到敖魯古雅采風,敖魯古雅在上個世紀就哺育出一位享譽文壇的本民族作家烏熱爾圖。烏熱爾圖在他從少年向青年轉變時期就成為敖古雅獵民的一員。烏熱爾圖在這期專刊中發(fā)表了難得一見的階段性“自傳”。他冷靜地回顧了自己那段人生經歷,一個作家成長的經歷,為我們進一步研究他富有激情的小說提供了寶貴資料。從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藝術人物的雛形,以及尚儲存在他腦海中的人、事、情;我們相信他、期待他,會用更精彩的作品以饗他的“粉絲”。
這一期專刊發(fā)表的作品里,作家們許多好故事和真實情感,篇篇皆可點可評。
馮老確認“敬畏自然”這一哲學思想,對增強我們的文學藝術自信,提高我們文學藝術作品質量,都是極具意義的。我們曾為草原文學、森林文學和草原文化,作過多種思考和探索,誠如馮老所說,過去我們更多的是重在民族習俗、民族風情、獨特自然環(huán)境、生產方式等方面,投入精力。《駿馬》這一期“專刊”通過編輯,把國內實力作家們這一極為重要的藝術探索和實踐成果集中展示,尤其對我們全市作家藝術家是大有啟迪作用的,啟迪我們要強化“敬畏自然”自覺,啟迪我們強化生態(tài)文明意識自覺。
責任編輯 五十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