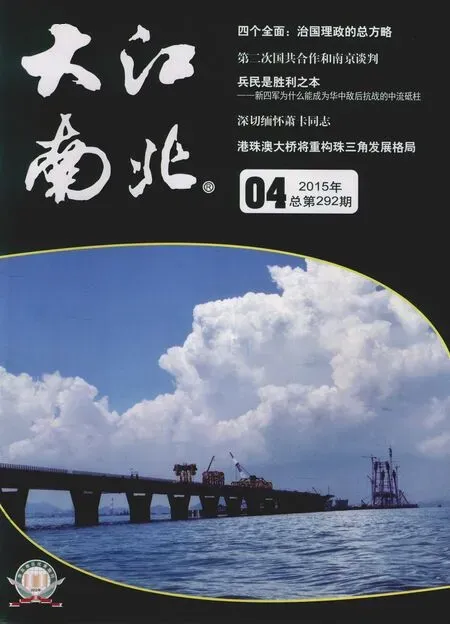蘇北民間抗日司令陳文
□徐皎皎
蘇北民間抗日司令陳文
□徐皎皎
在蘇北的高郵湖畔,至今流傳著民間抗日英雄陳文的傳奇故事。他棄文從武,散盡萬貫家財自建抗日義勇團,匡扶正義;他不畏強暴,率領部隊與日軍殊死搏斗,屢戰屢勝,卻慘死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下。他死后被訛傳為“草莽匪寇”,直到1982年,《陳毅北渡》一書中披露陳毅對陳文部隊抗日精神的高度評價,稱他為“抗日英雄”,歷史的真相才廣為人知。
散盡家財謀救國
1902年春,陳文出生于安徽省郎溪縣畢橋鎮。1921年,陳文從安徽省立宣城第四師范畢業后,在家鄉創辦“畢橋小學”和“懿貞女子小學”,因宣傳無神論,受到當地鄉紳們的阻攔威嚇,兩所小學被迫相繼停辦。
教育救國夢想破滅,面對兵荒馬亂、百姓遭殃的現實,陳文為保一方平安,決定棄文從武。1926年,他自費組建地方民眾自衛武裝,后擴展為“宣郎廣民眾自衛團”,積極聲援北伐戰爭。1928年4月初,陳文率部接受中共郎溪特支的改編,作為副總指揮領導了郎溪農民暴動,攻占郎溪縣城,槍決貪官污吏,打開糧倉賑濟貧民,釋放政治犯。國民黨派兵圍剿,陳文沉著指揮,先后擊退圍敵三次,終因彈盡糧絕、寡不敵眾而撤出縣城。為躲避當局的通緝,陳文背井離鄉,易名隱居蘇北。
1937年,陳文千里迢迢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考入“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接受革命思想熏陶。“七七”事變后,他返回鎮江變賣家產,籌備抗日武裝力量。揚州淪陷后,日寇入城制造了種種駭人聽聞的暴行,陳文怒不可遏,切齒痛恨,親手鐫刻了“抗日義勇團”的木質大印,立志抗日救國。1937年底,陳文在公道橋鎮北街關帝廟前,主持召開了抗日義勇團誓師大會。陳文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到會的工農商各界人士聽得熱血沸騰,會場上不時爆發出震耳欲聾的“團結一致,抗日救國”的口號聲。陳文領導的抗日義勇團有三個連,士兵百余人,分別駐扎在公道橋鎮的張莊小學、鎮北關帝廟及橋頭、鎮郊西婁莊戴倉房。這支部隊成為揚州北鄉及高郵南、天長東面一帶的第一支抗日游擊隊。

陳文(1938年攝于高郵廬山照相館)
率部抗日第一仗
抗日義勇團成立后,與日軍第一仗就是奇襲日軍機場。
日軍侵占揚州后,在城郊的司徒蜀岡處修筑了一座軍用機場,日機經常從這里起飛,對城鎮、鄉村實施狂轟濫炸,抗日義勇團團部所在地公道橋,更是日機空襲的重點目標。1938年春節前后,孩子們正在稻場上玩耍,空中突然傳來日機俯沖的呼嘯聲,孩子們嚇得四處逃散。日機一陣掃射,四五個孩子當場倒在血泊中。陳文聞訊趕到現場,看到孩子們倒在血泊中,失聲痛哭:“鬼子連幾歲的孩子都不放過,我們抗日義勇團還有何顏面去面對父老鄉親!”陳文回到團部,望著掛在墻上標有日軍機場的軍事地圖,憤怒地抓起毛筆,在墻上寫下“以血還血”四個大字。他決計要摧毀揚州機場,給無辜死去的孩子報仇雪恨!
1938年2月5日晚上,陳文率領第一、第二連向日軍機場進發。夜12時,義勇團戰士潛入機場外圍,看到4架飛機停在簡陋的停機坪上,機翼在黑暗中發出微弱的亮光,日本軍旗隱約可見。陳文命令盧海濤連在鐵絲網外圍的高坡上架起兩挺機槍作掩護,同時派出尖刀班迅速干掉機場大門的崗哨,并擊墜了崗樓上的探照燈。隨后,信號兵打亮手電筒向空中揮動三圈,發出了襲擊信號。
十幾人的身影像離弦的箭頭穿過被尖刀班切開的鐵絲網,向機場內飛奔而去。黑沉沉的油庫旁,兩個在寒風中站崗的鬼子哨兵見探照燈突然熄滅,跑去查看。兩名身手不凡的戰士悄悄靠近,神不知鬼不覺地解決了他們。后面的突擊隊員們立即舉起成捆的手榴彈向油庫擲去。“轟”地一聲震天巨響,油庫爆炸,火光沖天。與此同時,一部分突擊隊員將蘸了汽油的棉棒點燃向飛機上扔去,另一部分突擊隊員向飛機的駕駛艙投擲手榴彈。頓時,機場火光四起。幾個守衛機場的日軍從睡夢中驚醒,剛出營房,就被事先埋伏在營房門口的突擊隊員用手榴彈炸倒,接著機槍一陣掃射,又掃倒幾個。戰斗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勝利結束,共計炸壞日機4架,擊斃日軍7人,繳獲槍支10余支和一批子彈、手榴彈,還繳獲了罐頭、軍大衣等一批物資。
三次激戰公道橋
襲擊機場的勝利,狠狠打擊了駐揚日軍的囂張氣焰,一時間,揚州地區上空風平浪靜。但陳文心里清楚平靜的背后即將是一場報復性的惡戰。他讓宣傳隊動員鎮上的民眾做好撤離準備,并部署部隊做好迎戰準備。
2月26日夜,80名日軍氣勢洶洶直撲公道橋,企圖一舉搗毀陳文團部。陳文立刻率領部隊埋伏在公道橋附近。27日清晨,日軍隊伍在北街頭駐扎下來。第二天后半夜,陳文率領200多名戰士潛回鎮里,直撲日軍駐地。日軍從夢中驚醒,倉促應戰,且戰且退。當退至十字街口,守候在街道兩旁屋頂上的義勇團戰士,將手榴彈擲向敵群。陳文身先士卒,站在房頂,手握輕機槍,向敵群掃射。日軍很快亂了陣腳。陳文正打得起勁,突然一顆子彈擊穿了他的右小腿,頃刻間鮮血染紅了褲筒,他仍咬著牙堅持掃射。不一會兒,另一顆子彈又擊中了他的肩胛處,他撕開一塊內衣將傷口簡單一裹,拿起槍繼續戰斗……在這危急時刻,一連連長盧海濤率部迅速趕到救援,戰士們見團長身上掛彩,憤怒地沖向敵群。日軍慌忙潰退。公道橋首戰告捷,繳獲日軍重機槍一挺,步槍20余支、手榴彈60多枚,擊斃擊傷日軍30余人。
4月4日,日軍從揚州城里出動兩百多兵力,直撲公道橋而來,大隊人馬分別在關帝廟和碧家祠堂駐扎。午夜,陳文部隊發起攻擊。日軍吸取上次的教訓,不敢夜戰,一連兩天也不敢下鄉“掃蕩”。陳文斷定,敵人熬不住,可能在第三天會全面出動回揚州。果然第三天午時一過,日軍出動,隱蔽在北街、西街屋頂上的伏兵灑下了密集的彈雨,僥幸沒有被打死的日軍落荒而逃。逃到方巷南首,發現通往揚州的道路被挖斷了。在此等候多時的一個排戰士,突然從兩邊麥田、溝坎里射出密集的子彈,日軍奪路向揚州城方向逃竄。這一仗斃傷日兵100余人,活捉2人,繳獲步槍近百支,機槍6挺,手槍10多支,子彈2萬余發,手榴彈100余枚,戰馬2匹等。
日軍萬萬想不到在小小的公道橋鎮一再受挫,于是決定派重兵占領公道橋。4月上旬,300余日偽軍,采取迂回戰術,出揚州北門經龍尾田到方家集,再到楊壽壩,企圖合圍于公道橋。日軍的先頭部隊30多人剛到方家集南首,就被抗日義勇團趙長泰的部隊發現,隨即雙方接火,戰斗進行近一個小時。大批日軍從西南邊的楊壽壩和南邊的方家集向公道橋包抄,在公道鎮旁的婁莊駐扎下來,抓來大批民夫拆房拉梁,準備在公道橋鎮上修筑碉堡工事,安營扎寨。誰知,一夜之間,所有修筑碉堡工事的木料、石料等,全部被義勇團的戰士搬個精光。與此同時,義勇團還破壞了公道橋通往揚州的公路,以阻止日軍汽車通行,造成日軍供給上的困難。日軍不得不于4月25日撤回揚州。此時,揚州至天長公路兩側的集鎮基本上連成一片,成為一塊穩固的抗日游擊區。
揚天公路打勝仗
日軍到處追蹤義勇團,然而,一旦與義勇團接上火,卻連吃敗仗。三戰公道橋后,抗日義勇團又先后和日軍展開了方巷反擊戰、南小街之戰、十五里塘伏擊戰、七里甸阻擊戰、巷子口伏擊戰等,屢戰屢勝。陳文清醒地意識到日軍連續受挫,絕不會善罷甘休。
1938年8月,駐揚司令官小川下令調集駐天長、儀征兩縣的日偽軍連同揚州本部駐軍共1000余人,兵分三路,分別從天長、儀征、揚州出發,向大儀、公道方向合圍,由東至西實施縱橫梳篦式的“掃蕩”,企圖一舉殲滅陳團。
獲悉此情報后,陳文即部署了各路伏兵。
戰斗打響后,各路“掃蕩”的日軍,一進入伏擊圈后,就遭到義勇團戰士們的猛烈打擊。義勇團打仗素以“猛打、猛沖、猛追”的三猛著稱,此次戰斗發揮得更是淋漓盡致,隊長身先士卒,戰士以一當十,與敵人死拼。日偽軍節節敗退。
揚天公路沿線戰斗大捷,共計斃敵100余人,繳獲各種槍支400有余,東洋馬25匹等。
血戰沙場含冤亡
陳文部隊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正面與日軍作戰大小戰斗達一百余次,開辟了東至邵伯湖,南至揚州、儀征,西至天長,北至塔集、金溝三河(現屬金湖縣)方圓500余里的抗日游擊區,成為蘇北抗日的一支勁旅。
抗日義勇團在逐步發展壯大的過程中,韓德勤和地方勢力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正、副指揮李明揚、李長江都想方設法將陳文部隊收編在自己麾下,以壯大自己勢力,陳文一邊率領部隊同日軍浴血奮戰,一邊還得和頑固派軍隊及地方勢力周旋,在夾縫中求生存發展。
1939年春,新四軍挺縱三支隊渡江北上,陳文仰慕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治軍有方,派參事邱劍鳴與中共蘇北工委取得了聯系,請黨組織派人整軍。經陳毅批準后,1939年5月派蘇北工委委員呂鎮中、陳干去陳文部隊創辦教導隊,向陳文說明要以抗大和陜北公學的教學方法來辦教導大隊,并要在部隊中發展中共黨員,建立黨的組織。1939年7月,經蘇北工委批準,在陳文部隊秘密建立了中共黨支部,發展了一批新黨員。
韓德勤將不聽調遣并和共產黨親密接觸的陳文部隊視為眼中釘,1939年8月,悄悄調集數十萬兵力分水、陸兩路,不惜一切代價大舉圍剿陳文抗日義勇團。陳文措手不及,兵力分散,等待救援不及,突圍失敗。為保全抗日骨干和部隊,陳文毅然站出大喝一聲:“我就是你們要捉的陳文!”
陳文被抓后拒不投降,也不交出共產黨員,并向看管他的軍官宣傳:“國難當頭,應一致對外,不能為某人某派而置民族利益于不顧!”韓德勤惱羞成怒,于9月中旬在蔣壩將陳文秘密處死。這位在高郵湖畔叱咤風云的抗日志士,沒有倒在日寇的槍林彈雨中,卻慘死在國民黨頑固派的屠刀之下。陳文含冤而死,年僅37歲。
陳文抗日義勇團被國民黨頑固派扼殺了,但他開辟的抗日游擊區,為此后新四軍蘇皖支隊建立高郵湖西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編輯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