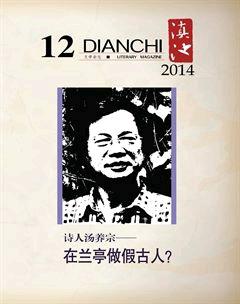湖底人家
張建梅
人應該生活在水上,怎么會在湖底呢?可伴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態的發展,很多原本應該在地上的東西,卻沉入水中,而沉于水里的東西卻自然顯露了出來。如白鶴梁、豐都鬼城,靜靜沉入水底,留給人們無限的遐思。
湖底人家,是因水庫建設移民搬遷,而從沉入水庫(湖底)的低洼處,搬遷至靜靜湖畔的幾戶人家。伴著水庫工程的竣工,曾讓幾代人留下深深記憶的美麗家園、牧場、農田、老宅子,隨著水庫蓄水水位的不斷升高,漸漸沉入湖底,那一刻,我不知道主人內心泛起的滋味是酸是甜,是苦是辣。更想象不出當美麗家園瞬間變為湖底的那一刻,主人對那片曾經的家園的深深眷戀,那種割舍不下的情緣,那種心與情的糾結是啥滋味兒。然而,一切都在舍小家顧大家,舍小我顧大我的無私奉獻中一筆勾銷。那平凡人家的不平凡的故事,像一道劃破夜空的流星,只存記憶,卻找不到痕跡。
湖底人家成為自然的湖畔人家的糾結感人的故事,讓心猶如一堆亂麻纏繞著,思緒在火光中跳躍著,故事在火塘邊彌漫著,一杯淡淡的水酒,在娓娓道來的故事中,不斷發出清脆的碰撞聲,烤火房內,火塘兩側低矮漆黑的老床,一邊鋪著暖暖的羊皮襖,一邊鋪著暖暖的羊毛氈毯,顏色,早已被那一茬茬光顧火塘的游客們坐得都已發黑變黃,那承載歷史歲月滄桑、用來存放糧食散發著古樸的斗柜,仿佛在為主人作古敘舊。湖畔的短暫停留,讓封存的記憶在瞬間穿越時光隧道,又從時光隧道的夢幻中醒來。連連喝下親密碰撞的酒杯中的美酒……再回過神來,放眼近在咫尺的湖光山色,才感覺,湖畔的美帶有幾分羞澀,湖畔的風帶有幾分涼意,是夏季送來的清涼,還是綠水青山的造化,或是大自然的深呼吸?
湖畔,一葉輕舟在湖水中蕩起陣陣漣漪,垂釣的人們,背倚著木樁,專注著即將上鉤的魚兒。置于美輪美奐的人間仙景,心中的幾多惆悵,漸漸從心中移走。留下的,是對湖畔人家美好生活與未來的憧憬。緊接著,一番“阿德子客棧”的廬山會議,在你一言我一語中拉開序幕:古老民間文化的傳承保護、文化包裝與提升、房屋建筑的合理布局,農家特色菜烹飪的傳承等等話題,在火塘邊彌漫開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頓時,我們仿佛成了主人、成了文化使者、成了策劃大師……德文老人面帶微笑,靜靜傾聽著這幫不文不武、不土不洋的人們七嘴八舌的建議,似朋友、似兄弟、似親人。其實,從湖底人家到湖畔人家,農耕放牧養家糊口,再到農家客棧的小本經營維系生存,每走過一步,德文老人何嘗不比我們更明白、更清楚?昨天與今天的對話,在他心中永遠揮之不去。
緊接著,幾道地地道道的白族農家菜肴端上桌來,聽罷主人幾番吆喝上桌吃飯的客套話后,美味在口中彌漫。走遍大江南北,只知道餐桌上的菜或雞鴨魚肉什么的,是論盤按10元、20元不等的價格賣的,或者論斤頭賣的,可從未見到過哪家餐館、餐桌上的菜肴不限量的。可在湖畔人家品嘗農家菜,擺上桌的燉土雞、燉火腿等一道道美味佳肴,吃著吃著,便見主人不停地往餐桌的菜盆里添菜,仿佛主人家烹制菜肴的食材都不是用錢買來的,而是從湖水中隨手撈上來的,或是用主人的真心與熱情烹制出來的,那種真心一波接一波,那種熱情一浪高過一浪,讓人感覺,永遠也品嘗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