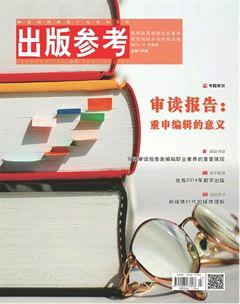《少年斯特法諾》:從男孩到男人要走的路
趙文偉
去年的一個周末去了趟徽州,那里粉墻黛瓦,路邊的田地里是一片片嫩黃色的油菜花。眼前擺了一堆獲安徒生獎的童書,從中單單挑出了這本《少年斯特法諾》,因為我有個意大利朋友叫斯特法諾,后來才知道,這本書的作者,阿根廷女作家瑪麗亞·特蕾莎·安德魯埃托的父親也叫斯特法諾,也是意大利人,這本書就是獻給他的。如果可以借花獻佛,我也想把這本書獻給我的朋友斯特法諾,他會用中文說“你好嗎”,他的二兒子,十歲的加布里埃萊也在學中文。有一天去他家吃飯,還給加布里埃萊上了堂課,這個孩子漂亮聰明,還認真得不行,臨走前,我把剛讀完的一本路內的小說《云中人》送給了他,對他說,“現在讀不懂,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你會讀懂的。”這本《少年斯特法諾》也是,如果感覺讀不懂,長大了就會明白。
《少年斯特法諾》是一個關于成長的故事,在這本書中,我們會清晰地看到一個男孩成長為男人的軌跡。成長是必然的,男孩的成長首先要離開母親,而過早的成長有時候是出于青春期的叛逆,在特定的時期,則是出于無奈和環境的壓力,人畢竟要生活下去,更準確地說是生存下去,有了生存才有生活。在斯特法諾離開家鄉前,鎮子里的人已經走光了;空蕩蕩的街道上只剩下老人。有個彈曼陀鈴的瞎子每禮拜天上午去教堂,為死去的人祈禱,為漂洋過海的人祈禱。城門口鐘樓旁邊還有一個人,他沒有腿,嘴里不住地念叨著:“媽媽,你會跟我在一起,你再也不會孤單了。”斯特法諾一直想離開,他并不是想離開母親,而是想過上更好的日子。可是,母親不愿意走,意大利是她的祖國,是斯特法諾父親的土地。最終,兒子的遠行是她阻攔不了的,幾年后,斯特法諾和幾個小伙伴一起踏上了去南美的路。從斯特法諾走出家門,轉過彎,知道已經離開母親的視線,抬起袖子,擦干眼淚的那一刻,他的成長真正開始了。
成長就是往前走,把一些東西留在身后,斯特法諾把祖國和母親留在了身后,真的是這樣嗎?空間上是,他的身體離開了,和意大利、和母親產生了距離,但心理上沒有,也許靠得更近了呢,因為人人都會思念。所以,成長中總有一些東西是永遠伴隨我們的,又有一些新的東西不知何時加入進來,舊的像新的一樣,新的也會變舊,直到有一天,我們不再去區分新和舊。成長是一種遷移,時間上的、空間上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遷移,從這一年到那一年,從意大利到阿根廷,從一個男孩到一個男人,從一個女人到另一個女人,伴隨著這種遷移的還有他對母親的愧疚。
愧疚是一種有良知的思考,反思自己的不對,想要改正,但不一定會有改正的機會。斯特法諾與母親分別時,兩個人都克制著不去制造抱頭痛哭的悲情一幕,克制著不讓對方看到自己的眼淚,故作堅強地各自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然而,太克制容易在胸中結成塊壘,于是,母親一次又一次,甚至太多次出現在斯特法諾的夢里,每次都問同樣的問題,問他為什么走,問他幸福不幸福。還好,斯特法諾有艾瑪這個愿意傾聽的對象,他似乎試圖用“談話療法”治愈對母親的愧疚,在他痊愈之前,也許時不時會想起城門口那個嘴里不停念叨著“媽媽,你會跟我在一起,你再也不會孤單了”的瘋子吧。可是,母親最后還是孤單地死去了,雖然有鄰居和神父照料,但兒子不在身邊。得知母親的死訊后,斯特法諾似乎有意識地加快了成長的腳步,他要去圓母親的心愿,找到她的朋友琪雅拉,找份穩定的工作,組建一個屬于自己的家。書中一部分是斯特法諾獨白分析先前的經歷,試圖找到其中的意義。一部分是向沉默的艾瑪講述他和母親的生活,他的夢,試圖在講述中與母親達成和解,也試圖理解她拒絕離開的原因。斯特法諾從一個男孩成長為一個男人,但是人生漫長,成長的腳步不會就此停住。這本書中有孤獨,有悲傷,但也有希望,有愛。
一本書由很多層的感覺構成,瑪麗亞說,作家并不總是能意識到這一點。深挖的話,你就會發現,沒有哪種人性是普通的,或者奇怪的。瑪麗亞將她的經驗、痛苦、喜悅或驚奇變成文字,變成小故事放進我們這些陌生人的耳朵里,世界是一個大故事,她在這個大故事里加了幾句令我們難忘的話,我們要感謝她。
(作者系《國際安徒生獎大獎書系·少年斯特法諾》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