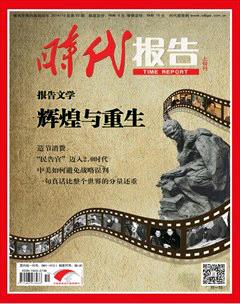“最可愛的人”和那個英雄輩出的時代
王君
最可愛的人,在當代中國已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代名詞。
談起這背后的淵源,就不得不提到《誰是最可愛的人》的創作者,魏巍。出現在全國中學生語文課本中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所謳歌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鼓舞、教育了幾代人。
1950至1951年是抗美援朝戰爭最艱苦的階段。魏巍就是在那時調到了總政。1950年6月25日,朝鮮半島由于領土爭端,爆發了朝鮮戰爭。上級為了便于開展對敵政治斗爭,派了魏巍在內的一個小組,去朝鮮了解美軍戰俘的思想情況。
完成任務后的魏巍在本可以回國的情況下卻選擇上了前線。在前線陣地上采訪的三個月里,他見證了戰士們對國家的忠誠、對殺敵的無畏,親身感受到了來自敵人巨炮的轟鳴。他踏過被炮彈深翻過的陣地,也握過那被鮮血浸透的泥土。回憶起這段經歷,他說前線的這三個月,令他終生難忘。
從朝鮮回來時已經是1951年的2月了,此時的他已調任《解放軍文藝》副主編。雖已身在故鄉,但在朝鮮時前方將士那忠誠為國、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在他的心中依然濃烈。一個念頭始終占據著他的腦海,他要讓祖國人民了解自己的兒女是怎樣的英勇,又是怎樣的頑強。
“我們眼前這平平常常的一切,都是他們鮮血的代價,這絕不是一句空話。”
在朝鮮,魏巍的腦子里時常會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的戰士,為什么那樣英勇呢?一個活生生的人就硬是不怕死啊!那種高度的英雄氣概是從什么地方來的呢?為了尋找答案,他找了好多人談話,開了好多座談會。他去找戰士們談,讓他們把心里的話都講出來。與他談話的,有指揮員、戰斗英雄、一般的戰士、干部、新參軍的學生和過去曾經是落后的人。在采訪過程中魏巍發現,他們由于閱歷不同,對事物的認識也不同,雖有些差異,卻也有著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偉大祖國的愛、對朝鮮人民的同情和在此基礎上想要做一個革命英雄的信念,他們有著共同的信仰。魏巍明白了,這種偉大深厚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思想感情,就是我們戰士英勇無畏的最基本的動力。他想,這不是最本質的東西嗎?這就是最本質的東西!
“我肯定了它。我一定要反映它。我毫不懷疑。一切其他枝節性的,片面性的,偶然性的東西,都不能改變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魏巍曾就這篇文章談論自己的創作經驗時說:“現在,回過頭來看這篇稿子,使我更明確了這一點:在現實生活中的深入感受,對寫作的人是多么重要!你感受得深了,寫出來,也就必然有那么一股子勁,人家讀了,也就感受得深;你感受得淺,人家從你這兒得到的,也就淺。如果你自己都沒有感動呢,那就用不著說了。深入的感受,跟深入的采訪很有關系。就拿在戰士中的采訪來說吧,你跟他們談得越深,對他們的了解就會越深,他們的氣質、思想、感情,會感染你,使你也沉入到他們的情緒中。也就是說,使你感受得更深些。”
采訪本上的20多個故事,魏巍幾經遴選又幾經推敲,最后才確定最典型最感人的三個細節。《誰是最可愛的人》第一位讀者、《解放軍文藝》主編宋之的閱罷,當即吩咐:“送《人民日報》!”
1951年4月11日,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鄧拓將《誰是最可愛的人》在第一版頭條發表。毛澤東閱后批示:“印發全軍”。 朱德讀后連聲稱贊:“寫得好!很好!” 周恩來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上講話時,竟推開了講稿,對著話筒大聲說:“在座的誰是魏巍同志,今天來了沒有?請站起來,我要認識一下這位朋友(這時,全場都望著從座位上站立起來的魏巍,熱烈鼓掌),我感謝你為我們子弟兵取了個‘最可愛的人這樣一個稱號。”
“《誰是最可愛的人》這個題目不是硬想出來的,而是從心底跳出來的,從情感的浪潮中蹦出來的。”魏巍后來曾經這樣說過。
之后的一段時期中,黃繼光、邱少云、劉英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英雄人物形象相繼出現在文學作品里。毫不夸張地說,英雄人物的產生孕育了《誰是最可愛的人》,而《誰是最可愛的人》又催生了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伴隨著紙質作品的傳播,舉國上下掀起了向英雄學習的高潮,爭當最可愛的人。
1963年4月,《雷鋒日記》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在全國發行。這也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雷鋒日記》。一共選輯了其中的121篇,約4.5萬字編輯成書。根據一個公開的數字表明,《雷鋒日記》光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前就印刷了160萬冊。
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為雷鋒題詞。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先后發出“向雷鋒學習”的號召。
隨后,《雷鋒日記》又再版了幾十次,甚至“漂洋過海”到了國外。據1973年統計,當時就有28個國家,用外文翻譯出版的《雷鋒日記》《雷鋒詩文集》,共有英文版、法文版、日文版、朝鮮文版、泰文版等32種。
雷鋒,不僅在中國家喻戶曉,還成為一種象征、一個文化符號而走向世界。美國《時代周刊》介紹:“雷鋒品牌是中國人民也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全面介紹了焦裕祿的感人事跡,同時還刊登了《向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學習》的社論。
……
如今,雖然曾經的英雄已經離我們遠去,但報告文學這一載體與之相伴相隨,他們輝映出的時代精神永遠留在了人們心中。
2014年,習近平主席兩次抵達蘭考。在焦裕祿生前工作過的地方,他感慨萬分地說,雖然焦裕祿已經離開我們50年了,但焦裕祿精神是永恒的。很多東西存在的時間是短暫的,但就是這短暫的一刻化為了永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