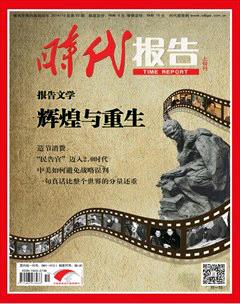《哥德巴赫猜想》創造了報告文學史上的一個神話
董海燕
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接見著名數學家陳景潤
30多年前,在中國曾經有一個傳言,說的是,美國有一個代表團到我國訪問,見到我國領導人就問陳景潤。領導人不知陳景潤何許人也。于是,就讓人找,費了很大的勁,才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找到了陳景潤。
就是這個陳景潤,他在全國上下鬧革命的年代,居然解決了一個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
如果把數學難題比作金字塔,按照當時的說法,哥德巴赫猜想就是鑲嵌在數學世界難題上的明珠。
據說,陳景潤在國內沒有刊物發表論文的情況下,把論文偷偷寄到國外發表了,引起了國際數學界的重視,才有了美國代表團到中國訪問時詢問陳景潤,而我們又在全國各地遍尋陳景潤的傳說。
這一傳說是否真實,現在已經無從考究。但是,由此引出的一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則成為了一代乃至幾代人無法忘卻的記憶。
1977年10月,《人民文學》雜志社得到一個消息,全國科學大會即將召開。而科學大會的召開,預示著科學的春天即將到來。編輯部的同志深受鼓舞,同時也想到了自己應負的責任和使命——如果能在這個時候組織出反映科學領域的報告文學,讀者一定會喜歡看。
于是,他們在討論中有人談起了陳景潤的傳說。
談論中,大家一致認為,如果把陳景潤報道出來,肯定能引起反響,而要引起反響,就必須使用報告文學這一文體。
選題確定下來之后,大家又開始考慮請哪個作家來寫比較好,徐遲就是在這個時候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徐遲雖然是一位詩人,但他做過新聞記者,還寫過不少通訊特寫,當時已經在《人民文學》上發表過報告文學《祁連山下》,他寫地質學家李四光的報告文學《地質之光》也即將在《人民文學》發表。那時寫工農兵的作家多,但寫知識分子的比較少,因此大家一下子就想到了徐遲。
負責與徐遲溝通的,是當時組織寫作《哥德巴赫猜想》的《人民文學》原常務副主編、現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顧問的周明。
史無前例的《哥德巴赫猜想》 年代
時值1977年深秋,周明掛長途電話到武漢,尋找久違了的詩人徐遲。周明在電話里問候了徐遲,對方告訴他自己身體還好。周明說明情況,幾天后,徐遲風塵仆仆地從揚子江邊帶著滾滾的濤聲趕往了北京。
為了寫好這篇報告文學,徐遲在當時進行了深入的采訪和大量的調查研究。他住在中關村,白天黑夜都排滿了采訪日程,先后采訪了許多著名的數學家,其中有陳景潤的老師,也有陳景潤當時的同事。有講陳景潤好的,也有對陳景潤有看法的。講好的、講壞的,正反兩方面意見徐遲都認真地傾聽。他說:“這樣才能做到客觀全面地判斷一件事物、一個人。”
在數學研究所,徐遲去了陳景潤經常出入的圖書館,去了他的辦公室,跟著他一起進食堂,一塊兒聊天,還去看了“文革”時期陳景潤被毒打滾下樓去的那個樓梯。而陳景潤當時的自我保護意識相當強,在徐遲的耐心誘導下,陳景潤才慢慢向徐遲打開了心扉。
陳景潤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間6平米房間成了后人津津樂道的“陳景潤精神”的載體。而在當年頗具詩人氣質的徐遲看來,似乎并不美好。“六平方米的小屋,竟然空如曠野。一捆捆的稿紙從屋角兩只麻袋中探頭探腦地露出臉來。只有四葉暖氣片的暖氣上放著一只飯盒。一堆藥瓶,兩只暖瓶。連一只矮凳子也沒有。”
1978年1月,《人民文學》在頭條以醒目的標題刊發了《哥德巴赫猜想》。據后來的資料顯示:在改革開放發軔之初,因為思想上的開禁,題材上的創新和藝術上的精進,這篇報告文學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重點報紙紛紛予以轉發,全國幾乎所有的電臺和地方性報紙競相連播或轉載了這篇報告文學,廣大讀者自發排著長隊購買當期報刊,大中學教科書先后選錄該文。與此同時,徐遲和《人民文學》收到的讀者來信數以萬計……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
《文藝報》的《時代呼喚<哥德巴赫猜想>式的作品》對當時的情形進行了充滿激情的評述:《哥德巴赫猜想》創造了那個年代報告文學的一個神話,并以其赤誠的民主精神和強烈的科學訴求,義無反顧地充當了引領改革開放新征程的“雄鷹”,充分顯示了報告文學自由純真的本性、熱烈奔放的氣質和推動社會前進的雄渾力量。
一個史無前例的“《哥德巴赫猜想》年代”呼之欲出——
陳景潤、張海迪、中國女排、楊利偉……一個個響亮的名字,照亮了無數顆年輕的心。
1981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通訊《癱瘓姑娘玲玲的心情像一團火》。張海迪熱潮席卷全國,信封上只需寫上“張海迪收”,就能寄到團中央。定價4角的張海迪事跡手冊《閃光的生活道路》印數超過1500萬冊。在厄運面前不認輸,在困難面前不低頭,成為那個年代人們真誠高昂的價值。
“1978年到上世紀80年代初的大學生,受《哥德巴赫猜想》的鼓舞最大。不僅是喜歡數學、研究數學的,所有的青年學生都受其影響,這個影響就是要上大學、要學知識、要向科技進軍。”與陳景潤齊名的“中國學派”之一的潘承洞院士的弟弟潘承彪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說過。
在《哥德巴赫猜想》發表30年后的2008年,潘承洞的學生展濤從山東大學校長任上離開。他說,當時,即便是“兩彈一星”宣傳得也很少,而徐遲的報告文學使得以華羅庚為代表的數論研究的這個群體,一下子走到大眾面前,成了那一代知識分子中最輝煌的代表。
“《哥德巴赫猜想》和那一代科學家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展濤說。
《哥德巴赫猜想》張揚了時代精神
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
當年的3 月18 日, 陳景潤和6000 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科學家一起來到了人民大會堂,出席全國科學大會, 他和他的老師華羅庚教授一起坐上了主席臺。
“一位外國教授曾經問我:‘是什么力量和意志,使你解決了如此之難的哥德巴赫猜想問題呢?……科學的獻身精神,百折不回的毅力,這些都是攻關的科學戰士所必須具備的品質……”
這是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數學家陳景潤的一個發言片段。如今,我們已無法目睹那樣的場面,但從他五千多字的發言稿中三次提及當時自己的興奮與激動,似乎可以看出,剛剛摘掉“白專”帽子的陳景潤的內心世界奔涌著怎樣的熱流。
在那次大會上,鄧小平擲地有聲說:“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自覺自愿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就是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 按政治標準來說,就不能說他們是白,而應該說是紅了。”
摘掉了“白專”帽子的陳景潤被請到臺上作典型發言,又作為著名科學家代表受到黨中央領導接見, 陳景潤和鄧小平握手的照片也成為那個時代的見證。
在潘承彪看來,《哥德巴赫猜想》能夠火起來,也跟當時的形勢息息相關。長時間的思想禁錮、知識貶值和精神壓抑,使作品一出現便暗合了急于尋找宣泄口的公眾意愿和社會情緒,讓特定歷史關口各層公眾有了精神上的松綁需求和解放快感。
展濤也持同樣的觀點,大家的壓抑解除后,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希望。整個民族也在往前看:民族的希望在哪里?而科學、學術,正是一個民族發展最具標志性的方面。徐遲的報告文學,讓人們看到了一種希望,產生了發自內心的自豪感,給每個人帶來了激情和振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