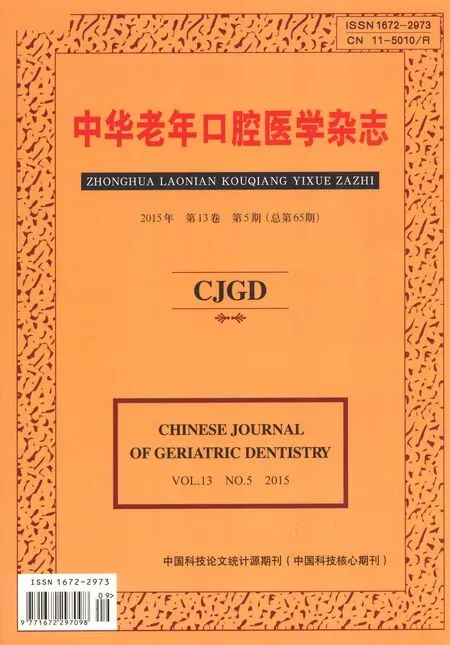CBL 和PBL 教學法在顳下頜關節紊亂疾病的相關心理因素學習中的應用*
徐 娟 胡 敏
顳下頜關節紊亂病(Temporomandibular disorders,TMD),是一類病因尚未完全清楚而又有共同發病因素和臨床主要癥狀的一組疾病的總稱。其病因復雜,目前認為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諸多研究表明,心理因素與TMD 的發病有一定聯系,并日益成為社會廣為關注的焦點。
1. PBL教學模式與CBL教學模式簡介
1969 年,加拿大麥克瑪斯特大學醫學院的Howard Barrows 教授首先把PBL 教學模式引入教育領域[1]。 PBL 教學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核心是“學生為主體、問題為中心、教師為引導”的教學方式[2]。在教師引導下,通過以學生為主體的多種途徑學習后,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獲取知識的主動學習模式。由此激發了學生學習的興趣和熱情,獲取大量應用知識的機會。PBL 的教學流程為:“案例下發-問題提出-查閱資料-小組討論-問題再提出-查閱資料-班級交流與討論-總結反饋”的周期循環,每個周期內包涵數次課堂討論。
19 世紀70 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蘭德爾首創CBL 教學模式。CBL 教學模式(Case-Based Learning)是繼PBL 教學模式之后發展而來的全新教學模式,“病例為先導,問題為基礎,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小組討論式教學法是CBL 教學模式的核心內容[3]。也就是說,在CBL教學模式中,讓學生扮演醫生角色,直接面對患者,進行病情分析,而教師引導著學生對發現的問題,進行問題探討,問題解決[4]。CBL 教學流程相對較簡單,從討論一個臨床案例開始,學生經過一次或二次課堂討論即可掌握知識要點,達到教學目的。
雖然CBL 和PBL 都為較先進的教學方法,但都存在不足。在醫學臨床教育中,通過PBL 教學模式的學生在積累了醫學基礎階段知識的學習后,對臨床醫學知識的激發出強烈探究欲。因此,通過傳統的由標準、典型案例入手,從點到面的學習將失去強烈的吸引力。若直接對醫學生選用CBL 教學模式的教學,由于基礎醫學和橋梁醫學知識的缺乏,會出現學生的自學難度與時間消耗增加。學生面對大量無法通過自學完成的案例分析時會產生浮躁心理。所以更應該把CBL 與PBL 相結合,使兩者互相促進,互相補充,以達到更理想的教學效果[5]。
2014 年,江洪等[6]人選取重慶醫科大學臨床醫學本科專業2009 級(1)班的30 名學生為觀察組,另選取同一專業2009 級(2)班的30 名同學為對照組,對照組采用傳統的“一對多”教學方案,觀察組采用CBL+PBL 的教學方案,對比分析兩種教學方案的教學效果。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實習結束時,其病理分析成績、理論考試成績、臨床實操成績及論文成績均顯著高于對照組,CBL+PBL 的教學方案可提高臨床醫學本科學生學習耳鼻咽喉頭頸外科積極性及學習熱情,提高學生學習成績及臨床操作能力。
吳曉霞等[7]研究,將82 名學生隨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兩組,每組41 名。實驗組學生采用CBL結合PBL 的教學模式,對照組學生采用傳統教學模式。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在期末考試中理論及臨床病例分析的平均分數均明顯高于對照組。問卷調查表明90.2%以上的學生認為CBL 結合PBL 的教學模式能夠極大的提高學習興趣、臨床思維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及團隊協作能力等。
黃嫦斌[8]把中職護理專業兩個班隨機分為試驗組和對照組,試驗組采用PBL+CBL 教學模式完成病理學教學任務,對照組采取傳統式教學模式完成教學任務。授課結束后面對兩組的理論考試成績、學生對授課滿意度及授課教師評優率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試驗組的三項指標均高于對照組且有統計學意義。
以上研究結果均說明,采用CBL 結合PBL 教學模式比傳統教學模式可以明顯提高教學質量、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學習成績。而且,PBL 更注重基礎理論知識的學習,CBL 更注重于臨床實際情況的分析。這說明,CBL+PBL 的教學模式更加適合臨床醫學專業的學習。
2. 顳下頜關節紊亂病相關心理因素
顳下頜關節紊亂病(Temporomandibular disorders,TMD),是指累及顳下頜關節和/ 或咀嚼肌系統, 具有相關臨床問題如疼痛、彈響、張口受限的一組疾病的總稱。是口腔臨床的常見疾病之一。其病因比較復雜,目前認為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許多研究表明,心理因素與TMD 的發病有一定聯系。
2008 年,Roger Fillingim 等[9]對2737 名TMD患者進行問卷調查以及心理和身體癥狀的收集,問卷包括90 項癥狀清單修訂版(SCL-90-R)、艾森克人格問卷修訂版(EPQ-R)、焦慮狀態-特質問卷(STAI)、情緒狀態-雙極型(POMS-Bi)、覺察壓力量表(PSS)、生活事件量表(LES)、癥狀清單平民版(PCL-C)、應對策略問卷修訂版(CSQ-R)、疼痛災難量表(PCS)。結果顯示,心理壓力和情感困擾為預測TMD 疾病的首要因素。心理和軀體癥狀的出現為TMD 發生的最強的危險因素。2013年,楊嫻睿等[11]對100 名TMD 患者和100 名健康人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為焦慮自評量表(SAS)和抑郁自評量表(SDS)。結果表明,焦慮傾向與抑郁傾向為TMD 相關危險因素,隨著其嚴重程度的增加,患TMD 的危險性也增加[10]。以上研究說明,TMD 發病的心理因素既有共性,如焦慮、抑郁。又因TMD 患者的人格、情緒、壓力大小等不同而存在差異。所以,在研究TMD 發病的心理因素時,不僅要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做支撐,還要因人而異,對每一例患者進行個性化的病因診斷,實行個體化的治療策略,并且要根據診斷結果進行最適宜的治療。傳統的教學模式為“理論教學-教師試教-練習-指導”的流程。所以,傳統的教學模式并不能很好對病因復雜且尚無準確定論的TMD進行學習和探討,而應把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把CBL+PBL 教學模式用于TMD 相關心理疾病的學習和研究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3. CBL和PBL教學法在TMD相關心理因素的學習和探討當中的應用前景
近十年來,PBL 模式已被世界眾多醫學院廣泛采用或探索研究。即選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新型教學模式,代替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模式;以小組討論,學生之間的互動式學習代替教師講授。CBL 模式是讓學生扮演醫生角色,通過對病案的分析,直接面對患者的過程。教師和學生共同協助,風險共擔,教師通過事先選出的典型病例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探索問題、解決問題[6]。
根據CBL+PBL 教學模式的特點和TMD 疾病的性質,結合以往研究所使用的教學方案,現提出如下教學方案:
3.1 授課前的問題設計 在授課前一周給學生布置幾個關于TMD 心理因素的問題,臨床醫學學習問題的設計要符合以下幾個條件:首先,問題要緊扣臨床實際,有層次性和連貫性。內容包括詳細的患者個人資料和疾病詳細情況,如:患者主訴、臨床表現、體征、診斷依據、鑒別診斷、治療方法,以及疾病的發病機制、病理生理等。其次,問題要有較強啟發性和激勵性,以激發學生興趣培養學生臨床思維和解決臨床問題的能力[12]。
根據一般疾病的學習內容,TMD 患者心理方面的學習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病因、臨床表現、診斷、治療和護理。
3.1.1 病因 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發展,心理因素作為病因之一逐漸開始受到關注。關于心理因素對TMD 影響的研究也逐漸備受關注。
一項調查TMD 心理因素的研究顯示,心理因素對TMD 起決定性的作用。消極被動的心理因素可以通過心身途徑調節患者的軀體功能,讓患者自覺軀體不適,加重甚至誘導其肌肉慢性疼痛的產生[13]。
劉法鑫等人對88 名TMD 患者和92 例對照組進行隨機分組研究,使用SCL-90、SAS、SDS、EPQ 問卷調查。研究顯示,TMD 患者中多次患病比初次患病焦慮和抑郁水平高,且TMD 患者與正常對照組相比,存在不同程度心理障礙[14]。這說明,TMD 的病程和得病時間對心理因素有一定影響。
Kindler 等[15]對3006 名患者進行了5 年的跟蹤調查,研究者對患者進行了關節和肌肉觸診,然后通過問卷 CID-S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Screener)測定心理障礙。研究結果顯示,抑郁癥與TMD 有內在聯系,抑郁癥為TMD的一項危險因素。
楊建斌等[16]采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對90例TMD 患者進行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并與全國常模比較。研究結果顯示,TMD 患者的SCL-90 總分、總均分和陽性項目數均高于全國常模,軀體化、人際關系、抑郁、焦慮及恐怖等因子均高于全國常模。這說明,TMD 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情緒問題。
通過以上的研究提示,TMD 相關的心理因素有多種,我們應該有針對性地進行診斷和治療,因人制宜,不同的心理因素應采用不同的診斷和治療方法,才能有助于患者的康復。
3.1.2 臨床表現 顳下頜關節紊亂綜合征主要的臨床表現有局部酸脹或疼痛、彈響和運動障礙等。疼痛部位可在關節區或關節周圍,并可伴有輕重不等的壓痛。關節酸脹或疼痛尤以咀嚼及張口時明顯。彈響在張口活動時出現,響聲可發生在下頜運動的不同階段,可為清脆的單響聲或碎裂的連響聲。常見的運動阻礙為張口受限,但也可出現張口過大或張口時下頜偏斜。此外,還可伴顳部疼痛、頭暈、耳鳴等癥狀[17]。
心理方面表現為多數TMD 患者不僅在軀體上受到疼痛的折磨,心理上亦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焦慮、敏感和失眠等[18]。軀體癥狀和心理癥狀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周振等人對90 名TMD 患者進行研究,研究表明,TMD患者所出現的各種口頜面部的急慢性疼痛也反作用于患者心情等因素,對其心理造成極大的影響。身心之間相互作用和影響[19]。
3.1.3 診斷 TMD 患者心理診斷的標準首先在20 世紀90 年代初期由美國華盛頓大學的Dworkin 和Von Korff 在美國國立牙科研究所的支持下提出。提出的內容為TMD 研究診斷標準,即“TMD 雙軸診斷標準”(RDC/ TMD),建議從軀體軸和心理軸全面評估TMD 患者[20]。關于心理狀況的內容主要為:抑郁(SCL-90-R 抑郁及生活單調癥狀分級,包括正常、中度及重度)。
在RDC/ TMD 這一診斷標準的基礎上,我國的馬緒臣和張震康提出了目前在我國使用較廣泛的雙軸診斷標準[21]。心理疾病的診斷標準:精神心理狀況(根據SCL-90 癥狀自評量表分級)正常:SCL-90 分值小于普通人群分值均數加1 倍標準差;中度:SCL-90 分值大于普通人群分值均數加1 倍標準差,但小于普通人群分值均數加2 倍標準差;重度:SCL-90 分值大于普通人群分值均數加2 倍標準差[22]。
3.1.4 治療和護理 一項關于TMD 的心理因素和治療的相關綜述里顯示,關于TMD 的心理因素治療的措施主要包括,藥物治療、綜合心理治療(疏導、解釋、鼓勵、音樂治療、電療等)、催眠療法、生物反饋療法和認知行為療法[18]。
心理因素在病因和治療方面已證實與TMD 關系密切。要求醫生在TMD 的臨床治療中,不僅要注重其傳統藥物治療和手術治療;同時也要求醫生注重個人儀表,尊重患者,注意聆聽并及時做出積極的回應,用熱情積極的口吻與患者溝通,注重患者的心理狀態和心理治療,減輕患者心理和生理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質量[23]。
3.2 典型病例的選擇 上見習課時,要求老師選出一到兩個典型病例,與患者提前進行溝通,并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和理解。首先,教師應選擇依從性較好的患者,從而能夠保障配合學生問診、查體和心理量表的完成等。其次,教師還應選擇具有教學價值的病例,這樣會給學生留下深刻印象。
3.3 互動式討論 在教學過程中采用PBL 結合CBL 的教學模式,帶教老師選取有代表性的典型病例并提出啟發性問題,為學生搭建討論平臺的同時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經過啟發引導鼓勵后,學生進行積極熱烈的討論,同時也能主動客觀的發表自己不同的見解。見習學生畢竟沒有臨床經驗,對于討論中出現的一些錯誤或帶有偏見的見解,帶教老師應在討論過程中進行及時有效的修正,這樣可以避免全盤否定而影響學生的積極性。在分析問題的環節中,要充分考慮學生的知識面和理解能力,適當的引導并給予廣闊的思考空間,引導見習學生向更進一步思考。通過選擇互動式發言討論,鍛煉了學生,提升了與他人溝通合作的能力[21]。
3.4 見習總結 2012 年,Kim 等人對36 名TMD 患者的主觀癥狀、客觀體征、心理問題和心理特征進行了分析。使用癥狀嚴重程度指數(SSI)和顱頜指數(CMI)分別用于評估主觀癥狀和客觀體征。使用SCL-90-R 和MMPI 用于心理測評。研究結果顯示,有心理問題的TMD 患者的SCL-90-R 和MMPI 之間的關系有限,提示臨床醫生在針對有心理問題的TMD 患者時,需要對他們進行更全面的心理測試[24]。
以上研究說明,雖然關于TMD 的心理診斷已存在書面的標準,但是在具體的臨床見習和臨床診斷、治療過程中,還需要具體實踐的學習。所以,既要掌握TMD 的相關理論知識,又要把這些理論用于臨床實踐當中。還因TMD 的病因不明確,心理因素的相關研究還亟待更多證據,應鼓勵更多關于TMD 的心理因素的研究。這更需要使用CBL+PBL 的教學模式對TMD 的相關心理因素進行學習和探究,從而探索出有助于提高學生臨床見習質量的教學模式,同時也能為TMD 相關心理因素的患者診療提供更好的應用前景。
[1] Barrows,H. S. A taxonomy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methods[J]. Medical Education,20(6): 481-486
[2] 張 敏,陳媛媛,劉盼寧. CBL 與PBL 教學模式在固定義齒教學中的應用探討[J]. 消費電子,2013,1(2): 219
[3] 吳錫蓮. CBL 教學模式在口腔內科學教學中的應用探討[J]. 中國健康月刊,2011,4(30): 261-262
[4] 曹 霞,鄭家偉,張建中,等. CBL 全英語教學在口腔臨床醫學教學中的應用[J]. 上海口腔醫學,2009,(18): 207-209
[5] 李 稻,韓玉慧,蔣 益,等. 醫學基礎教育中PBL 和CBL兩種教學模式的實踐與體會[J]. 中國高等醫學教育,2010,(2): 108-120
[6] 江 洪. PBL 教學法結合CBL 教學法在耳鼻咽喉頭頸外科教學中的應用研究[J]. 中國校外教育(下旬刊),2014,(z1): 590
[7] 吳曉霞,張 勇,史 真,等. CBL 結合PBL 教學模式在口腔臨床教學中的應用[J]. 現代口腔醫學雜志,2014,2(28):115-117
[8] 黃嫦斌. PBL 和CBL 教學法相結合在病理學教學中的應用[J].科技信息,2014,(11): 173-174
[9] Roger Fillingim,Richard Ohrbach,Joel Greenspan,et al.Psychologic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velopment of TMD:The OPPER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The Journal of Pain. 2013,14(12):T75-T90
[10] 楊嫻睿,宋 穎,張 希,等. 心理因素與顳下頜關節紊亂病癥狀表現的相關性研究[J]. 上海口腔醫學,2014,4(23):460-464
[11] 杜小靜,宋紅霞,梁紅玉,等. PBL 結合傳統教學法在基礎護理學實驗教學中的應用研究[J]. 護理實踐與研究,2011,1(8):13-15
[12] 姜振東,張學淵,鐘 誠. CBL 結合PBL 教學法耳鼻咽喉科八年制見習中的應用[J]. 基礎醫學教育,2014,8(16): 645-647
[13] Auerbach SM,Laskin DM,Frantsve LM,et al. Depression,pain,exposure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and long-term outcomes in temporomandibular disorder patients[J]. J Oral Maxillofac Surg,2001,59(6): 628-363
[14] 劉法鑫,黃 磊,蔣立堅. 顳下頜關節紊亂病患者心理狀態的研究分析[J]. 廣州醫藥,2015,(1):48-52
[15] Kindler S,Samietz S,Houshmand M,et al.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as risk factors for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pain: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J Pain,2012,13(12): 1188-1197
[16] 楊建斌,邵月保,魏東義,等. 顳下頜關節紊亂病患者心理健康狀況調查[J]. 新鄉醫學院學報,2011,2(28): 231-232
[17] Pankaj Prakash. 心理干預與藥物治療對顳下頜關節紊亂病的療效對比研究[D]. 天津醫科大學,2014
[17] 雍翔智,唐黎黎,農曉琳. 顳下頜關節紊亂綜合征的心理因素及其治療[J]. 國際口腔醫學雜志,2013,5:634-637
[19] 周 振,王美青,李 楠,等. 顳下頜關節紊亂病患者疼痛的臨床描述分析[J]. 華西口腔醫學雜志,2008,4:402-405
[20] Dworkin SF,LeResche L. Research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temporomandibular disorders: review,criteria,examinations and specifications,critique[J]. J Craniomandib Disord,1992,6(4):301-355
[21] 馬緒臣,張震康. 顳下頜關節紊亂病治療理念的進步及對規范化治療的思考[J]. 中華口腔醫學雜志,2012,1(47): 2-5
[22] 馬緒臣,張震康. 顳下頜關節紊亂病雙軸診斷的臨床意義和規范治療的必要性[J]. 中華口腔醫學雜志,2005,5(40):353-355
[23] 王俊成,劉洪臣. 口腔全科醫師的醫患溝通能力的培養[J]. 中華老年口腔醫學雜志,2014,6(12):357-359
[24] M-J Kim,M-J Lim,W-K Park,et 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CL-90-R and MMPI in TMD patients with psychological problems[J]. Oral Diseases,2012,2(18):14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