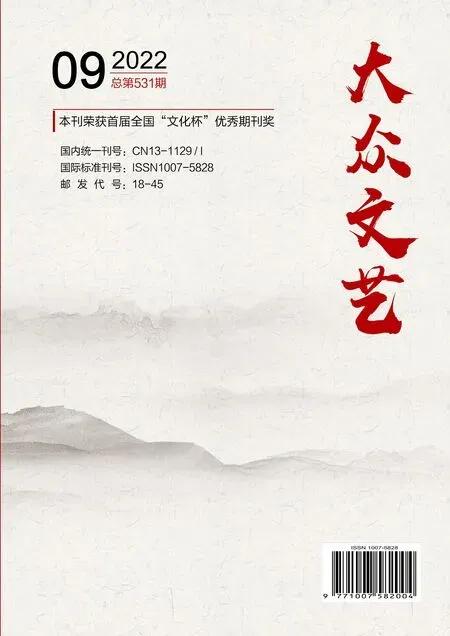淺談“圈舞”舞蹈文化遺存的萌芽與發展
海維清 (四川大學 610207)
淺談“圈舞”舞蹈文化遺存的萌芽與發展
海維清 (四川大學 610207)
“圈舞”是人類最初創造的舞蹈藝術形式之一,中華大地上的“圈舞”舞蹈文化遺存歷史悠久,形式豐富,傳播地域廣泛,堪稱活著的舞蹈“化石”,它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種重要信息載體,昭示著人類童年特殊的社會生活內容和人類心理、情感“進化”的復雜記憶。舞蹈作為“非物質”屬性傳承的藝術門類,使我們試圖研究“圈舞”歷史萌芽與發展脈絡的進程顯得異常艱難,而研究“圈舞”文化的產生、傳播與發展進而考察“圈舞”功能、形式和審美的歷史嬗變也因此顯得尤為重要,因為這將為我們在當下時代認識并繼承好"圈舞"這筆寶貴的舞蹈文化財富提供更為科學合理的方法。而當我們正確地認識這些“圈舞”舞蹈現象之所以萌芽、產生、發展、傳承的因素時,我們就能為這些即將消失的歷史久遠的舞蹈形式,重新找回屬于它們自己的靈魂。
圈舞;舞蹈;文化;萌芽;發展
一、“圈舞”舞蹈文化遺存及其萌芽
中華“圈舞”舞蹈文化源遠流長:其有據可考的歷史至少可從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出土的新石器時代“舞蹈紋”彩陶盆算起,到當下仍在藏區廣為流傳的各類“鍋莊”,四川羌族的“薩朗”,摩梭人的“甲蹉舞”,云南納西族的“熱美蹉”“維蒙達”“東巴舞”,佤族的“木鼓舞”,獨龍族剽牛祭天牽手圍圓的“剽牛舞”,新疆維吾爾族蘇菲派宗教性“薩瑪”圈舞,東北鄂倫春族“篝火舞”……傳承至今約五、六千年。
由此可見,中華大地上的“圈舞”舞蹈文化歷史悠久,“圈舞”遺存形式豐富,“圈舞”舞蹈文化傳播地域廣泛。
而“圈舞”舞蹈文化之所以能在這些不同的民族中普遍萌芽、發生并傳承、發展,體現出如此寬廣的文化跨度及“適應性”,僅依賴舞蹈文化自身的傳播能力是無法達到的。究竟是什么樣的條件,才如土壤和甘露般,促成“圈舞”舞蹈文化在這些民族文化生活中萌發與生長?
通過對擁有“圈舞”舞蹈文化遺存現象的多個民族比對與分析,我們可以肯定,在這些瑰麗的“圈舞”舞蹈文化遺存現象背后,積淀著中華民族深厚的人文內涵。而初民原始、樸素、平等的特殊社會結構和“崇拜意識”下“萬物有靈”觀念的產生,則是“圈舞”萌發的重要誘因。
統觀具有“圈舞”文化遺存現象的這些民族,他們都具有或曾經具有“萬物有靈”觀念下的“多神崇拜”信仰傳統,如以“鍋莊”著稱的藏族,古代曾普遍信仰具有原始崇拜特征的巫教——“苯教”,直至公元7世紀后才逐步改信佛教;西北蒙古族、維吾爾族、土族以及東北鄂倫春、鄂溫克等民族,歷史上曾長期信仰薩滿教;而西南地區的羌族、彝族、納西族、苗族、侗族、普米族、瑤族、基諾族、獨龍族、佤族等少數民族,其信仰種類繁多,如羌族“釋比”,彝族“畢摩”、“蘇尼”,納西“東巴”,摩梭“達巴”……但這些信仰大都具有“多神崇拜”的某些基本特征,且其社會成員多具有較為樸素、平等的社會關系。
在這種“崇拜意識”支配下“重巫尚神”的信仰中,崇拜儀式與祭祀活動較為頻繁,而由崇拜、敬畏心理引發初民情感、意識的集體性投射與集中,聚焦至核心崇拜對象上,便交集出一個客觀存在的“圓心”,從而促使人們圍繞這個“圓心”相互聚攏,在向神靈訴說族群共同的愿望、感激、哀傷與敬畏時,情不自禁的聯袂集中,呼號頓踏,最終踏歌而舞,從而促使“圈舞”舞蹈形式的萌芽與產生。
二、“圈舞”舞蹈文化傳播及其形式、功能流變
需要指出的是,“圈舞”文化的發生和傳播是多因素的,例如由民族戰爭、遷徙造成民族之間文化(包括舞蹈文化)的傳播與融合,也是促成“圈舞”舞蹈文化現象在少數民族舞蹈文化中普遍傳承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而這個因素在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圈舞”文化傳播歷史中更為突出。
筆者較為認同賈安林老師的觀點——羌系民族是“圈舞”在西南地區的重要傳播者。
羌族歷史淵源悠久,殷甲骨卜辭中有役使“羌”或“多羌”以及以大量“羌”作“人殉”的記載,而關于羌族的歷史淵源及秦漢時期向西南地區遷徙的歷史,在馬長壽先生遺著《氐與羌》和任乃強先生著《羌族源流探索》以及其他大量關于羌族歷史、文化研究的著作、論文中,都作過非常系統的研究和闡述。
秦漢之際,古羌族先民通過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大量向南遷徙,與西南本地土著民族逐漸融合,產生了彝族、納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頗族、拉祜族、基諾族等眾多兄弟民族。
此外,藏族與羌族在族源上也有密切的聯系:7世紀松贊干布時期,吐蕃從山南遷都邏些(拉薩),隨后兼并了北方的蘇毗、象雄等西羌部,又破黨項、白蘭羌部,擊敗西遷甘、青的遼東鮮卑“吐谷渾”政權。隨著戰爭兼并,西北羌族大范圍融入吐蕃并被不斷同化。綜上所述,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多數民族族源上與羌族之關系密切,這一點也為眾多學者所認同。
通過對馬家窯“舞蹈紋盆”的研究,專家們普遍認為這就是西北地區古羌先民樂舞活動的真實摹寫。其舞蹈文化特征與今天聚居茂縣一帶的羌族民間“莎朗”非常類似,它也與今天甘肅南部舟曲縣(與古羌故地之一的“宕昌”相望)藏族“羅羅舞”舞蹈形態酷似。
我們可以設想,由于古羌先民長期大量南遷,加之古代民族間戰爭、兼并造成的民族文化融合,促使“圈舞”舞蹈文化也隨之向更遙遠的西南地區傳播。古羌民族“圈舞”文化基因伴隨南遷的腳步,與途中“土著”民族的舞蹈文化相互消解并相互融合,因而使西南眾多藏緬語族形成了較為普遍的“圈舞”舞蹈文化現象,因此也促使西南地區各民族中的“圈舞”舞蹈文化分布更趨集中。不過,上述現象僅能解釋“羌系”民族或“藏緬語族”圈舞文化傳播、傳承的主要因素,而東北和新疆地區“圈舞”文化的傳承因素還需另做它論。
正如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奧斯本·威爾遜的觀點:“在進化的意義上講,文化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適應性的。”在廣義社會“文化”發生變化的同時,其影響也同樣直接或間接體現在作為“意識形態”的舞蹈文化之中,“圈舞”舞蹈文化在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其功能、形態、審美均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雖然藝術起源有著非常復雜的機理,但在這里,“群體意識”的確是早期“圈舞”形式發生的重要誘因。初民在狩獵、采集歸來后,圍于篝火邊炙烤的食物周圍,共享食物,分享獵獲成功的興奮。飽食慶祝之余,呼號振臂,頓踏擊節,逐漸形成“圈舞”雛形,其舞蹈以強化群體認同與溝通,維系初民樸素平等的社會關系為主要功能。
而隨著“神靈意識”的產生,“圈舞”則逐步以“娛神”或“巫術”為主要目的進行,并促使人們聯結成各種形式獨特的圓圈,例如佤族“獵頭祭谷”的“木鼓舞”,獨龍族“剽牛祭天”的“剽牛舞”等,往往借助這樣的“圈舞”活動,以達到初民操縱自然的企圖,可見這時的“圈舞”功能已逐步發生變化。
伴隨著歷史社會的不斷發展,“世俗化”的社會文化逐步形成,昔日敬獻神靈的舞蹈,卻成為了人們自娛、社交的媒介,舞蹈恢復了它本來的形態,其功能從“娛神”走向“娛人”。這樣的轉變在今天還在發生,那許多祭祀鬼神的舞蹈,如佤族“獵頭祭谷”的“木鼓舞”,今天再敲響起舞的時候,根本不需要“人頭落地”來作為祭品,或許它正在某個旅游景點的舞臺上,成為供人欣賞的藝術;羌族的“莎朗”有“憂事”、“喜事”之分,土家族擺手舞分的“大擺手”“小擺手”,嘉絨藏族鍋莊舞分“大鍋莊”和“小鍋樁”,凡此種種,大抵也是這個道理,只是在很早時候,這類“圈舞”已衍生出兩種甚至多種不同的功能與形態。
從形態來看,西部民族“圈舞”舞蹈形式的發展,應該符合藝術形式發展的一般規律,即從“樸素、稚拙”走向“繁復、華美”再到“抽象、簡約”的階段,呈“螺旋式”發展。
因為“童年期”人類的構形能力并不發達,最初的“圈舞”大多結構松散,形式樸野——它們往往步伐簡單,動作即興,多呼號頓踏,重復循環,若以今人視之,或無幾分美感。
而宗教觀念產生之后,人們才懷著敬畏、崇拜的心理,結手成環,歌舞祈愿,以祀鬼神。這種聯臂舞蹈,結構較縝密,恰如一系列馬家窯“舞蹈紋盆”所描繪的那種“圈舞”舞蹈形式。
此后,“圈舞”的形式,向著更為繁復的方向發展,出現許多“圈舞”形式的變形和變體,例如侗族“多耶”舞變單圈為多圈相套;苗族“蘆笙舞”和云南彝族“左腳舞”開始內外圈互相穿插;景頗族“目腦縱歌”則是在圈舞隊形上變出更為復雜的紋路調度;羌族“莎朗”變幻出熱烈歡快的復雜舞步;摩梭人的“甲蹉”在圓圈中繞出“U”形和“S”的調度,嘉絨藏族的“鍋莊”更是出現了在舞蹈中將“圓弧”切成男女各異的兩個半圓,為面對面的直排舞蹈埋下伏筆。
在自娛的功能下,人們以更為繁復的聯結方式將手臂“編織”在一起,或者干脆松開“鏈”接的雙手,在圓圈中更灑脫、自由的手舞足蹈,創造出新的“圈舞”形式美感。
三、當下時代“圈舞”舞蹈文化遺存的繼承與發展
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現代人演繹的古人“圈舞”,即使動作完全相同,但它也已經不是古人所跳的那個“圈舞”了。
隨著整個世界的現代化,曾經積淀在中華民族“圈舞”身后那些古老厚重的歷史和文化正在被現代文明慢慢消解。當下“旅游文化”的興起,以往“圈舞”中的“莊嚴神秘”的美,早已被“歡快、熱烈”的喧囂所代替,以“創收”為目的“圈舞”,其舞蹈“功能”也早已嬗變,它們多淪為滿足游客獵奇心理,體驗參與“互動”的某個環節,“圈舞們”踏出越來越快卻愈發蒼白無力的舞步。
面對這樣的現狀,作為藝術工作者,我們無法因當下“圈舞”繁華的表象而沾沾自喜。如何合理對待這種古老舞蹈文化的傳承和發展,絕不是金錢和“一哄而上”的熱情所能替代的。它還需要科學、合理的引導,方能真正達到保護和傳承良好心愿。因為不恰當的方法致使意圖與結果南轅北轍的例子在舞蹈文化的傳承和保護工作中并不鮮見。
在當年“鍋莊舞”的普及與推廣中,在達到普及目的的同時,也曾一度使部分藏區的“鍋莊舞”呈現出“單極化”的局面,因為在普及的過程中,那些本身極具本土特色的地方鍋莊被極度“邊緣化”甚至失傳,令人非常惋惜。因此,如何更科學合理地繼承并發展“圈舞”,不是一個簡單的議題,筆者曾和他人做過一些討論,對此有一些不盡成熟的觀點,以下拋磚引玉,以供探討。
對待“圈舞”文化的傳承問題,應該實行“雙向并列”的戰略性方針路線。所謂“雙向并列”,簡言之,就是“民間草根”和“舞臺高端”采取截然不同但卻并行不悖的兩條路線:
1.在圈舞“民間傳承”中借鑒并采取類似韓國傳統文化保護的一些方法,恰如現在國家出臺的一系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措施一樣,將那些本土“圈舞”文化的重要繼承人以“傳承人”的方式進行重點保護,同時指定一定的本土“繼承人”,通過“言傳身教、口傳心授”的方式進行傳承。其傳承方式盡可能以“原封不動”的模式進行,以最大限度地保持這種傳承的“純正性”,禁止“繼承人”的隨意的改動或編撰。同時做好相關影音、文字記錄和整理工作,做到即使意外失傳也可以“有據可考”,甚至可以逆向恢復。
2.在“圈舞”的“舞臺發展”和弘揚上,則可不必拘泥于那種過于保守的發展方式,在不破壞所發展“圈舞”的文化根基上,利用相關舞臺藝術手段,進行合理的發展和創新。但務必切記的是,這種創新不能為了讓“圈舞”適應舞臺表演而徹底破壞它作為“圈舞”的基本形式和基本語匯,應該在創新中有一定比例的“原型”出現。此外,更應注意“圈舞”外在形態和內在審美相對統一的問題,不應扭曲“圈舞”固有的人文內涵和舞蹈語匯,這些也是所有傳統舞蹈創新發展中必須重視的要素之一。
而在這兩者之間,還應注意“雙邊路線”的“并行”,以及各自路線實行“領地”的界限。所謂“并行”,是指這兩種方針必須同步,否則就會重蹈覆轍,不能很好的兼顧“繼承”和“發展”這兩方面內容;所謂“領地”,就是各自方針所實行的范疇和區域,粗略看我們就可以以“民間業余”或“專業舞團”的角度劃分其領地。
此外,在“民間草根”和“舞臺高端”這二者之間,還有一個“灰色”的地帶,是最不容易實行引導的部分——“旅游文化”演出。
在這一范疇內,“圈舞”的發展現狀往往隨本地旅游業的發展情況各自為政,良莠不齊。但“旅游演出”的受眾最廣,影響深遠,同時“偽民俗”和“外來文化”對這部分的沖擊更為直接,究其原因,往往是由“文化自信”不足甚至“文化自卑”的心理造成。
對這一部分而言,筆者認為,即使“土”,即使有些“單調”,但游客千里迢迢慕名而來,希望看到的其實應該是極具民族文化特色,原汁原味的本土“圈舞”藝術瑰寶,而不是迎合商業需要,看似華麗實則廉價的“贗品”和“山寨”。
因此,對待這一區域內的傳統“圈舞”,應該充分利用旅游業的資金優勢,吸引當地更多人加入到“繼承人”的行列。而在旅游文化范圍內,應該采取較為保守的藝術態度進行引導,不盲目地強調創新,不人為扭曲“圈舞”舞蹈語匯和形式以迎合觀眾,才能最大限度保持進入這一區域的“圈舞”以“原生”形態進行有效繼承與傳播。
研究中我們還發現,“圈舞”活動往往隨著相關民俗或宗教節日而存在,因此可以利用本土的這些民俗節日,以一定的物質獎勵,鼓勵引導鄉鎮群眾“圈舞”匯演或“圈舞”聯誼活動,促使“圈舞”藝術能夠在民間仍然保持深厚的群眾基礎,將有利于“圈舞”文化的良性的發展。
不可否認,“圈舞”是最有生命力的傳統舞蹈藝術形式之一,從有據可考的“圈舞”藝術萌芽、誕生至今約6000多年,仍然莘莘不息。而在現代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來自天南海北的陌生游客依然能夠很輕松地加入到旅游景點“圈舞”的舞蹈隊列之中,不僅透露出今天人們返璞歸真的一種內心需要,而且還昭示著“圈舞”這種古老舞蹈文化遺存所蘊含的巨大魅力和潛力···
透過那輪轉不息的一個個舞圈,我們依稀還會發現,這個人類童年誕生的“精靈”,依舊如此天真爛漫,毫無拘束地站在我們對面,用真摯的手,邀請我們加入到他那稚拙、唯美的圓圈,而當你、我的手觸及他指尖的那刻,你我還應該意識到——研究、繼承承并發揚好“圈舞”舞蹈文化遺存,是為孩提時代的中華先民,重新找回那顆被人們遺落在荒原,埋沒于塵埃之下的星辰。
[1]賈安林.《“篝火之舞與聯袂踏歌”—藏緬語族圈舞文化特征和功能》《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5(2).
[2]羋一之.《從精美舞蹈盆說到民族發祥地》《青海民族研究》,1998(1).
海維清,男,滿族,四川省舞蹈家協會會員,藝術學碩士,四川大學藝術學院舞蹈系教師,研究方向:民間舞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