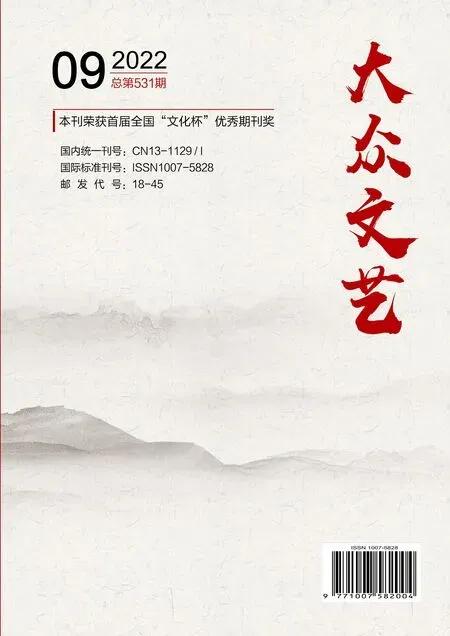從《廣藝舟雙楫》看康有為碑學審美觀
王育育 (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 570228)
從《廣藝舟雙楫》看康有為碑學審美觀
王育育 (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 570228)
康有為系碑學的集大成者,其《廣藝舟雙楫》可謂是書論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于書法發展的折轉期,康氏通過該書,在“變易”這一核心書學思想下提出“尊碑抑貼”、“尊魏卑唐”的主張,壯大了碑學聲勢,拓展了碑學影響。在“氣象”此一審美范疇的統領下,康有為極力推崇“雄強茂密”的陽剛之美,受儒家思想影響,亦兼尚“陰柔”與“中和”之美,體現出其思想的復雜性。在其碑學審美觀的指引下,康氏開一代書法新風,創成獨具一格的“康體”書法,使后世學書者受益。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碑學;審美觀
康有為(1858~1927)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及思想解放的先驅,其一生除游歷求學、教學、組織變革活動外,潛心學術,著作頗豐,其中,文藝類的屬《廣藝舟雙楫》影響最為深遠。
康氏集碑學之大成,繼包世臣《藝舟雙楫》之論而“廣”說之,著成《廣藝舟雙楫》,以通變的史學眼光審視書法流變,評論碑品,講述學書經驗與技巧;體例彰明,征引廣博,論證嚴謹;集中體現了康有為的書論見解。因其作于康氏向皇帝上書不達,變革大計受攻責,心中苦悶而鍵戶讀碑之際,故多受其革新思想影響。書中激越之詞與變古立異之說為時人所責,然恰是此不溺舊說、另辟蹊徑之學說促使康有為專注于碑學研究并最終使碑學兼具實踐與理論系統。該書成為嶺南書學乃至中國書學研究的經典著作。
一、尊崇“雄強茂密”之美
嘉慶、道光以后,帖學盛極而衰,向來以“清朗俊逸”、“妍妙秀媚”為審美旨趣的傳統帖學在時世危艱之際已無法滿足時人表達其熾熱的情感和困頓的人生之需。康氏認為當適時注入遒勁舒放的風格,方可振拔其生氣,遂極力推崇“雄強茂密”的審美理想。這是康有為在書法藝術上主張變革并著眼于書法形體表現特征的一大貢獻。
(一)推崇“雄強茂密”
康有為所著《廣藝舟雙楫》在阮元(公元1764~1849年)、包世臣(公元1775~1855年)首倡重視碑學以救帖學之弊后于大量出土碑版的充裕客觀條件的支持下,進一步明確提出“尊碑抑貼”這一核心書學思想,從中便可窺見其尊尚雄強之風。康氏尊碑一方面是由于書帖日久老化,頻繁翻用而受損,另一方面,則為碑版書法的五點特征所折服,言曰:
“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于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這段話集中體現了康有為重碑輕帖、尊魏卑唐的書學觀點及原由。所列前四點從書體的角度論六朝碑之優點:魏碑不但因書法字體齊備、筆畫完好而易于臨摹,而且還具有史料價值和承上啟下之用,可以考證隸楷之流變與后世各變體之源流;第五點則從風格上作論,當是最為關鍵的一點,舒長而刻入的筆法與雄奇之勢使其達到唐宋書法所未能達的獨特境界,這是康有為在其書中首次流露出對雄強之氣的推崇。由此觀之,其所謂“尊碑”,從審美上而言,尊的是碑版書法所展現出來的內在氣勢,即有似于曾國藩(1811~1872)以乾坤二卦論作字造形時所言之“乾道”。曾氏認為具此卦象的書法內主于神氣而脈絡舒通,與從形質出發而要求結構合乎法度的“坤道”迥然相異。[2]88康氏論書不拘泥于法度,這恰與其激進的變法革新精神及其自身剛強性格特征形成對應關系。由此便不難理解其為何如此極力推崇“雄強茂密”之風。
除此,康有為尊尚雄強之氣、推崇茂密之體格亦可散見于其論述書體源流、品評碑品等相關書論篇目中。卷二《體變第四》雖是論述書法藝術自先秦至清代、從籀篆到隸楷之發展情況,然其在梳理書體流變并強調學書者研究書法藝術當觀古論時之際多有論及此一審美風尚:秦分是最先從鐘鼎及籀字演變而來的字體,康有為因秦書《瑯琊》“茂密蒼深”而以其為極則;漢末書體演變為真書,康氏觀三國鐘繇書帖與該時期的其它碑版以其“茂密雄強”為美。《寶南第九》一篇中認為南朝碑數量絕少,只字片石,最可寶貴,其源溯于吳,吳碑中被康有為推為篆、隸、真、楷之極的四碑亦是或渾勁無倫,或奇偉驚世。然而自宋、齊之后,碑版書法體勢日漸纖弱,至于梁及陳朝已變為娟媚柔好,再無雄強之氣,幸至北魏碑版書法體態莊茂且不乏飛宕俊逸之氣,魄力猶存,盡顯茂密,評論至此,康有為言辭間流露出激賞之意。由此觀之,康氏盡購南北朝碑而又專尊魏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些碑版在態勢形質上所體現的陽剛美正中其審美旨趣。另有《取隋第十一》稱隋碑深得洞達之意故足取之,卻又因部分碑版氣勢薄弱,行筆間尚乏雄強茂密之氣象,康氏不得不對其稍加貶抑。
(二)“雄強茂密”的具體指涉
康有為以“十美”為總概,道出尊崇魏晉南北朝碑的審美旨趣及其具體所指:
“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
“十美”中“魄力雄強”居首,可見其地位之著重。細作品思,此處康有為所謂的“雄強”已然成為一種具有概括作用的審美范疇,統攝書法藝術生成的其他諸種因素。從書法的精神品格上出發,提出“魄力”“氣象”“意態”“精神”“興趣”,在整體上給審美主體產生“壯”“大”之感。所謂“筆法”“點畫”“骨法”“結構”“血肉”,則從運筆和結構形式上強調力度感。康有為在談及魏碑時,認為其盡是佳品,無不可學者,并時時褒賞其“骨血峻宕”之特征,此處,“骨”與“血”的關系亦是強調用筆所透之力。給人以壯美的“大”以及富有生命感的“力”恰是“雄強茂密”表現出的書法形質意味。
“雄強”體現為熔鑄于書法中創作主體的精神人格,屬內在意蘊,“茂密”則表現為書法創作的外在形質,是內在力度的顯現。真正的陽剛之美當由此二者相互融合而成。提倡“雄強”之美非以康氏為首,前代之人已有相關論述。包世臣在《藝舟雙揖》中對“雄強茂密”作過具體闡釋:“雄則全氣勃勃,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包氏雖然強調雄強與茂密二者緊密結合,但他認為書法若達“茂密”之態,則“雄強”已備,此乃視“雄強”為達成“茂密”之條件,強調的是“茂密”。
康有為繼承包氏提倡“雄強茂密”,但綜觀其文論,其對于二者間的關系則有了新解。在他看來,二者并無所謂孰重孰輕,且非包含條件關系,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離,沒有“雄強”難言“茂密”,沒有“茂密”,“雄強”亦無復存在。如上文所述,康有為用南北碑刻的“十美”來作具體分析。顯然,他并不效仿包氏就“茂密”而言“雄強”的做法,而將這一審美理想同書法藝術生成的精神品格、運筆結體等諸因素結合起來,構成包含有其他諸多審美趣味的范疇群。這種對前人理論的繼承與發展,在拓充“雄強茂密”這一審美理想的內涵之余還使得其更具獨特意味。
二、兼尚“陰柔”、“中和”之美
作為碑學的集大成者,康有為的碑學思想雖多有激越之詞,但在審美形態觀上,除上文論證的推尊“雄強茂密”之美外,還兼尚“陰柔”“中和”之美。
(一)“陰柔”之美
陳永正評論康有為的審美觀曰:“康氏在肯定書法藝術‘陽剛’之美的同時,卻否定了它的對立面‘陰柔’之美,未免偏激”,筆者認為此評說有失偏頗。康有為確實反對過于“妍媚”“靡弱”的書風,亦有激越之詞,但在其思想深處仍兼尚“陰柔”之美。
康氏兼尚“陰柔”這一審美旨趣仍可見諸《廣藝舟雙楫》一書。卷六《榜書第二十四》中,康有為指出榜書的習寫有臨仿難周、筆毫難精、運管不習、執筆不同、立身驟變之“五難”,推薦學書者取法并臨摹古人所寫的大且精之字。其中,北魏素有“書法北圣”的鄭道昭(455~516)所書《云峰山刻石》深受康氏青睞,被列為“妙品上”,且評論該碑曰:“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鄭道昭下筆多為正鋒,方圓并用,給人以結體寬博之感,又體氣高逸,特別是在章法上做到密致而又通理,使整體趨于和諧,呈現出迥異于陽剛氣的陰柔美。
此外,康有為雖不提倡干祿體,但在《干祿第二十六》中又因《裴鏡民碑》和《樊府君碑》具有陰柔之美而大贊之。在他看來,《裴鏡民碑》整朗方潤、字畫豐滿,虛和娟妙,清秀有如出水之蓮花與開天之明月,當奉為干祿書體中的無上上品,他認為有此二碑,學榜書幾乎無需再取法其它碑版。
綜上所述,康氏對書法的陰柔之美確有崇尚之意。在《廣藝舟雙楫》中,描述具有“陰柔”之美的碑版多用“媚麗”“娟好”“妍美”“虛和”“圓靜”“平整”“端和”“勻凈”“精秀”“清朗”“疏朗”“逸韻”等詞語。由此觀之,“靜逸”與“和諧”是康有為所兼尚的陰柔美中的主要類別,以形式的統一、完整,韻味逸永為主要特征。據統計,《廣藝舟雙楫》中約120處涉及“陰柔”氣象[3]134。實際上,“陰柔氣象”包含為康氏所詬病的“靡弱”與“妍媚”,本文所講的“陰柔之美”是建立在剔除該類氣象的基礎上,探討康有為審美旨趣中所尚賞的陰柔美。與推崇陽剛之美的內在氣韻不同,康有為兼尚“陰柔”之美的核心思想是指向書法表現形式的和諧,有類于曾國藩論書之“坤道”,言其“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2]88。康氏對后者的品評言辭雖未若品評前者般將其尊崇之意推到極致,但我們仍不可否認其在審美上對“陰柔”之美的追求這一客觀事實。
從康有為品評《三公山碑碑額》《樊敏碑》《司馬升墓志》等碑石中可見具有陰柔美的書法內在表現為生命力較小,外在體現為整體形式的和諧與勻整。這與陽剛美所體現出的雄強旺盛之生命氣息以及茂密之結體截然不同。
(二)“中和”之美
康有為一生在政治及學術上的思想尤為復雜,至于其碑學審美觀更是如此。介于陽剛與陰柔之間,還存在一種“中和”氣象。康氏碑學審美觀中也包含對書法“中和”氣象的向往。
在《榜書第二十四》一文中,康有為列具有“中和”之美的《淇園白駒谷》《泰山經石峪》《太祖文皇帝石闕》為佳碑,還因尖山、岡山、鐵山摩崖之書皆渾穆簡靜而稱其高絕。《泰山經石峪》用筆為圓,《淇園白駒谷》用筆為方。康有為更傾心于前者,列其為榜書第一,原因便在于其具有草書的風情之余還散發出篆書之雅韻,整體上盡顯雄渾古穆。康有為本最為尊尚書法結體之茂密,但當論及榜書鑒賞時則持相反態度。他再次以寬綽有余的《泰山經石峪》為例,論證榜書的作法異于其他書法形式,筆墨講求雍容之態,神態力主安靜簡穆,避免雄肆之氣帶來的突兀與視覺沖擊,一改陰柔美生命力較小之狀態,使其趨于中和,且特別強調作榜書若有意寫就氣勢雄強者屬粗野之人或不能書之人,是可鄙的。貶斥之余,康氏不忘回味《泰山經石峪》和《太祖文皇帝石闕》給人以“中和”之美的享受:“若有道之士,微妙圓通……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氣韻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絕”。用“有道之士”“冰雪”“處子”這些處于生命本然狀態的事物作比喻,更顯露出康有為對碑版書法之“中和”氣象的神往。
由此觀之,康有為所兼尚的“中和”之美表現在具體作品上是指結體與章法由內而外散發出渾樸、深沉之氣且內中富含意蘊,其最根本的特點在于“渾穆”。明朝項穆(1550~1600)認為“道統出源,匪不相通”,即人之倫理道德與書法之精神品格有相通之處。因而其尊評仲尼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氣質渾然,中和氣象也”,且認為書法之美善者亦當如此。所謂“中”即“無過不及”,所謂“和”則“無乖無戾”。具有“中和”之美的書法,介于陽剛美與陰柔美之間,在神態上趨于本然,體態上靜中含動,雖沒能如“雄強茂密”一般能以其磅礴氣勢而易于奪人眼球,亦無娟娟雅好之碑所特有的能扣人心弦之高逸氣韻,但卻散發出質樸淳和之氣,令人愈品愈覺醇香。
《廣藝舟雙楫》中與“中和”氣象相關的描述多用“淳古”“雍容”“渾穆”“靜穆”“安簡”“虛和”“自然”“古樸”“和雅”,等等。書中約有138處文字談及對該類氣象的描述。其中,“淳古”“雍容”“靜穆”“端美”“凝重”是“中和”之美的幾種代表類型。康有為在品評《三公山碑》《是吾碑》《東海廟碑》等碑版時多有論及此些特征。從中可觀知,“中和”之美的內在狀態可理解為生命力的深藏不露,而其外在形式即是這種生命力以自然之態顯現出來的感性表現。
三、審美觀之“矛盾”的原因探析
綜上所述,康有為的書法審美觀中存在兼尚“陰柔”、“中和”之美的旨趣已成事實,然而,目前學界對這一觀點尚未達成共識。筆者認為,一方面是因為康有為在言辭上將“雄強茂密”之美推崇至極,主觀意向上對其的關注程度深于另外二者,自然導致研究者的疏忽;另一方面則由于對康有為書法的研究大多還停留在就書法論書法的境地中,而未能從康氏的人生經歷以及心理學等角度探尋形成其審美觀上存在此種“矛盾”的內在原因。
追本溯源,康有為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審美觀根源于其思想的復雜性。而其思想雛形的形成與其自小所受的教育密切相關。康父早逝,康有為孩提時所受的教育均來自祖父康贊修,冠年之時又拜朱次琦為導師。康贊修是一醇儒,篤守程朱之學;而被世人尊稱為“九江先生”的朱次琦(1807~1881)則是晚清經學家,亦主張程朱理學,且兼采陸王心學,治經則歸宗孔子。在二者的影響下,康有為一生中最初的思想啟蒙完全來自儒學,于接受能力最強的青年時段更是立志做圣賢之人,決心讀遍圣賢書,儒家思想在康有為的意識中早已根深蒂固。
康有為曾自稱“至乙酉之年而學已大定”。乙酉之年為1885年,既然“學已大定”,那末此時其思想胚胎早已形成,而《廣藝舟雙楫》成書于己丑之臘,即1889年,從時間上看來,該書的寫作是在康氏思想雛形已定之后,自然受溶浸于其思想深處的儒家溫婉之氣所影響,這體現在書法審美上便是上文論及的兼尚“陰柔”之美。
基于儒家思想,康有為作《大同書》,在西方現代化大生產的前提下,展現了一副以人道主義、天賦人權為內容的資產階級社會理想,構建烏托邦,表達其大同思想。這種追求至善至美、和諧的大同理想折射在康有為的書法審美旨趣上恰是對“中和”之美的向往。康氏將中國富強與世界大同視為其生平的素志與理想,此二者出自同一人的思想藍圖,看似矛盾,實則不然,因其層次分屬不同且所處階段各異。那么,康有為在書法審美旨趣上既推崇“雄強茂密”之美又兼尚“陰柔”、“中和”之美這一現象實則亦無矛盾可言,因其分別強調的是對書法內在氣韻、表現形式、整體風貌等諸因素所呈現出的不同狀態的界定與評說。
化解矛盾的前提是承認它的存在。探討康有為的碑學審美觀,只有在認識并承認他對“雄強茂密”“陰柔”“中和”之美存在不同程度的尚賞,才能在原因探尋中化解此種“矛盾”,經此客觀而全面地透視康氏碑學審美觀。
雖然康有為碑學審美觀兼尚“雄強茂密”“陰柔”“中和”之美,但其主要貢獻仍體現在前者的影響上,不僅乘帖學之壞興碑學,扭轉“靡弱”書風,開一代“雄強”之氣,豐富中國書法藝術流派,還促成“康體”書法,對后世學書者,如梁啟超、徐悲鴻、劉海栗、蕭嫻等皆有指導意義。
[1]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注[M].崔爾平.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
[2]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
[3]參見劉兆彬.康有為書法美學思想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0.
[4]陳永正.嶺南書法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194.
[5]項穆.書法雅言[M].北京:中華書局,2010:155.
[6]康有為.康有為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