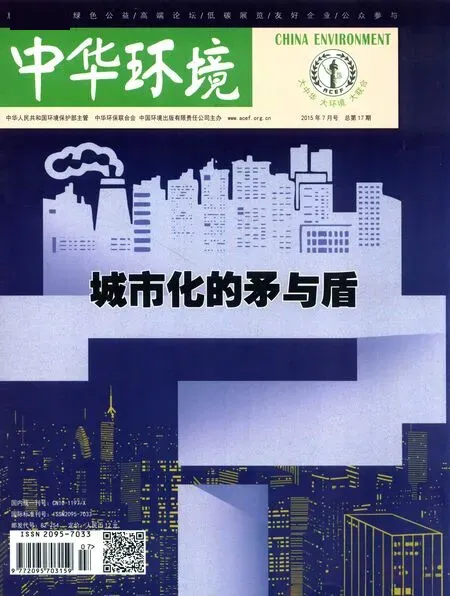6個人干活8個人監工
費米
6個人干活8個人監工
費米
有一次,上班等車的時候,路當中的綠化隔離帶上有人在種草,旁邊停了一輛標有北京某區園林局字樣的卡車。種草的一共6個人,看模樣都是外地農民工;一旁站著的8個北京人,又抽煙又聊天,顯然都是監工。聯想到有一段時間每遇公關危機,就會拋出幾個臨時工來墊背,敢情機構不斷膨脹,戶口又卡得那么緊,北京的年輕人又不稀得去種草種樹干體力活,有限的招工指標都給了外來的臨時工了。這莫非是我們想要的城市化的結果?
我這樣說沒有絲毫排外的意思,只是對所謂的城市化有點意見而已。對城市發展規劃者來說,發展意味著什么應該是心中有數的∶肯定不是單純的面積擴大和人口增加。北京的城市發展口號是建設科技北京、人文北京、綠色北京、和諧北京,但我所看到的只是單調的復制∶圈一塊農田,蓋幾排房子,建幾個商場,弄一所社區衛生院,再搞個餐館一條街,這就齊活了。當初喊得震天響的科技、人文和綠色呢?連個影子都沒有。砌個磚,抹抹灰,整個煎餅攤子,不需要多高的學歷;賣個假立邦漆什么的,只要膽子夠大就行。這樣的活,就連剛被征了地的北京郊區農民都不愿意干的,他們情愿拿征地補償去買輛車趴路邊,打打撲克開開黑車打發日子。于是砌磚抹灰賣煎餅的活就由外來農民接手了,一年半載下來,這些人就成了常住人口了。
一面是城市規模簡單擴張,一面是周圍鄉村日趨凋敝。近年來,不斷有媒體在報道農村的空巢化,良田因無人耕種而荒蕪∶旱地拋荒五成左右,水田拋荒一兩成不等。比這更嚴重的是雙季稻改種單季稻的大面積隱性拋荒。南方水稻主產區統計公報顯示,包括建設、拋荒等因素,各省播種面積數年內下降數百萬畝,拋荒面積三千萬畝以上。全國拋荒面積又是多少﹖記者最近在河南省部分“空心村”采訪時看到許多房屋常年無人居住,墻皮脫落、房門朽爛,屋頂垮塌。一些群眾形容:“外面像個村,進村不是村,老屋沒人住,荒地雜草生。”以大范圍村莊調查數據為基礎進行的估算表明,我國村莊空置面積超過一億畝(近七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全國耕地總量的18分之一。
什么原因導致了如此結果?答案是土地財政。知道為什么各大城市要頻繁修改城市規劃嗎?在規劃部門看來,對城市總體規劃十年一大修,五年一小修,仍是“一項常規工作”。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有關負責人說∶總體規劃到2020年實現的兩大最主要指標人口總量和人均GDP已經突破,所以面臨的將是一次大修編。地不夠用了,賣完了,地方政府就會通過總體規劃修編,從中央政府嚴格控制的“地根”里,獲取新的建設用地指標。根據國務院建設行政管理部門頒布的《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規劃人口與用地指標有著對應關系,規劃人口越多,用地指標越多。于是,做大人口規模成為地方政府修編規劃時傾力而為之事。1990年代總體規劃修編中,還出現這等怪事:至規劃期限2010年,各城市人口規模相加,竟達20億人。
以征地要錢為能事,規劃的科學性和前瞻性便告闕如。道路交通的設計建設沒有思路,堵車就成了新常態;建筑容積率耽誤了開發商掙錢,綠色就是稀缺物;治理霧霾和廢棄物成了燙手山芋,癌癥引發的死亡率自然就高居榜首;外來的人員不斷補充簡單工種資源,本地人的好逸惡勞被誘發,大家爭當甩手掌柜,再不濟的吃個征地補償,吃個低保或者啃一啃老。城墻外面,良田荒蕪十室九空,塵土飛揚萬物凋零。這場景,很像好萊塢的世界末日題材電影∶全部人口龜縮在有數的幾個城市里,靠微薄的一點資源茍延殘喘;城外,仿佛剛經歷了一場巨大災難,到處飄蕩著放射性塵埃,大地上寸草不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