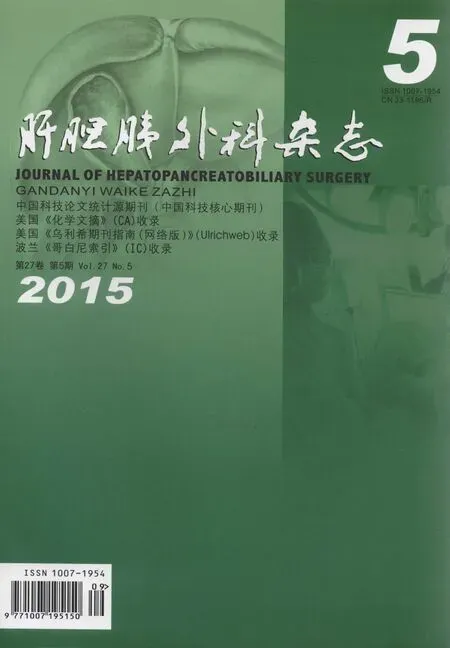經膽囊管匯入部微切開與膽總管一期縫合在腹腔鏡膽總管探查術中的應用比較
屠政斌,袁建毛
(南通大學附屬吳江醫院 肝膽外科,江蘇 蘇州 215200)
我國是膽道系統結石疾病高發地區,針對膽管結石的治療依然以手術為主,但傳統的開放手術甚至腹腔鏡手術均不可避免地在膽管內留置T管引流,造成大量的消化液流失,內環境紊亂,妨礙了術后快速康復。而本研究著重比較了腹腔鏡下膽總管探查取石術中經膽囊管匯入部微切開與膽總管一期縫合兩種方式,現報道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月至2014年1月在我院接受治療的原發、繼發膽總管結石患者共62例,其中男29例,女33例,年齡28~74歲,平均50.52歲。按手術方式不同分為兩組:33例行腹腔鏡下膽總管探查一期縫合術(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and primary suture,LBEPS組),29例行腹腔鏡下經膽囊管匯入部微切開探查取石術(microincision of the cystic duct,MICD組)。所有患者就診前均表現為上腹部疼痛,無發熱,其中合并黃疸9例(TBIL<50 μmol/L),合并急性膽源性胰腺炎2例。常規行術前檢查及MRCP排除以下情況:(1)肝內膽管結石及嵌頓的肝總管、左右肝管的結石;(2)膽管狹窄、畸形;(3)肝功能Child-Pugh分級B或C級。通過比較LBEPS組和MICD組病例的性別、年齡、膽總管直徑、膽總管內結石數量以及術前出現黃疸癥狀的例數(見表1)。兩組臨床一般資料差別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表1LBEPS組與MICD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1.2 手術步驟
全身麻醉后取足低頭高位,常規以“四孔法”放置各Trocar,分離膽囊三角,解剖辨明膽囊管與膽總管、肝總管之間關系,常規暴露膽囊管與膽總管交匯處。分離膽囊動脈予以Hem-o-lok夾閉并切斷,牽引膽囊后準備行膽總管探查。以下部分就兩種術式分別描述:
1.2.1 腹腔鏡下膽總管探查一期縫合術組(LBEPS組):選擇膽囊管匯入部下方2 cm內膽總管前壁表面無血管區域,以電鉤切開表面腹膜。切開刀切開膽總管確認膽汁流出后,以剪刀沿膽總管長軸方向剪開前壁,切口長約1.0~1.5 cm。經主操作Trocar置入纖維膽道鏡探查膽總管、肝總管及肝內膽管,以網籃取出結石后再次進鏡觀察膽總管下段,確認無結石殘留,下端通暢,乳頭收縮良好。以4-0可吸收縫線自上而下間斷縫合膽總管切開處,縫合時針距、邊距控制在1.5~2 mm,腹腔條件許可時同時將膽總管表面腹膜切開處再次縫合,覆蓋于膽總管切開處。
1.2.2 腹腔鏡下經膽囊管匯入部微切開探查取石術組(MICD組):將膽囊管遠端以Hem-o-lok夾閉,后距離膽囊管匯入部約5~10 mm處剪開膽囊管前壁約1/2周徑,自劍突下戳孔置入膽道探條,由小到大依次擴張膽囊管匯入部。后自膽囊管切開處下方,向匯入部切開,部分可延伸至膽總管右側壁。切開處頂端以4-0可吸收縫線間斷縫合防止取石過程撕裂膽總管。經膽囊管切開處置入膽道鏡探查取石,取石完畢后同樣需確認膽總管下端通暢無結石殘留。4-0可吸收縫線自膽總管向膽囊方向間斷縫合切開處,縫合至距離匯入部5 mm以上時,可使用Hem-o-lok夾閉膽囊管。
術后常規放置小網膜孔引流管,觀察有無膽汁樣液體流出。
1.3 觀察指標
分別對兩組患者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24 h引流量、帶管時間、肛門排氣(即胃腸功能恢復)時間、術后住院時間及術后膽漏發生率等指標進行分析。
1.4 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所有病例均成功完成取石,無中轉開腹,無手術導致死亡病例。LBEPS組與MICD組間各項臨床結果比較(見表2),可見兩組間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肛門排氣即胃腸功能恢復時間比較均無顯著差異(P>0.05);術后并發癥主要為膽漏,該項MICD組少于LBEPS組(P<0.05),而術后24 h引流量、帶管時間以及術后住院時間這幾項指標顯示MICD組優于LBEPS組(P<0.05),這可能與LBEPS組患者中有4例發生膽漏有關。術后并發癥主要為膽漏,均發生于LBEPS組,4例患者均通過延長肝下引流管拔管時間自愈,無明顯腹腔感染及膽汁性腹膜炎病例發生。
41例通過門診獲得隨訪,隨訪時間6~20個月,平均11個月。兩組間均無殘余結石或結石復發病例,也無術后膽管狹窄病例。

表2LBEPS組與MICD組患者術中及術后臨床結果比較
3 討論
目前膽總管結石的治療還是以開腹膽總管切開取石+T管引流術(open choledocholithotomy T-tube drainage,OCTD)為主,但是隨著腹腔鏡的誕生以及運用的深入,腹腔鏡下膽總管探查術(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LCBDE)逐漸普及。但由于LCBDE依然會在膽管腔內留置T型管外引流,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并發癥,如消化液、消化酶的大量丟失可影響術后食欲及恢復[1],長期帶管出院狀態可增加膽道感染的機會等。文獻報道T管所帶來的總并發癥發生率可高達15.3%[2]。同時鑒于十二指腸鏡下逆行胰膽管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 pancreatography,ERCP)聯合乳頭括約肌切開術(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EST)治療膽總管結石本質上會破壞Oddi括約肌的完整性,造成如反流性膽管炎甚至癌變的后果,所以即便該術式能避免長期的帶管狀態,其適應證始終有限且備受爭議。
而有關腹腔鏡聯合膽道鏡經膽囊管途徑行膽總管探查取石的研究,由于膽囊管直徑的限制以及Heister瓣的阻礙,即使采取術中擴張膽囊管的方法,其手術成功率依然有限。此后國內學者率先采用經膽囊管匯入部微切開入路進行取石[3],取得了理想的效果。與此同時,更多的學者從事將開放膽總管切開探查術中的一期縫合技術應用于腹腔鏡手術中,腹腔鏡下膽總管探查、一期縫合術(laparoscopic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and primary suture,LBEPS)與經膽囊管途徑相似,均能避免T管的留置。
3.1 術后并發癥的預防
無論是經膽囊管微切開入路還是膽管一期縫合,在合理避免留置T管、破壞Oddi括約肌等劣勢之外,其最大的潛在風險是膽漏和膽管狹窄。
3.1.1 膽漏:本次研究中,經膽囊管微切開入路行膽總管探查的病例無一例膽漏發生,而MICD組4例發生膽漏,雖經充分引流后自愈,但讓我們認識到,LBEPS術后膽漏還是其主要并發癥,這也與國內外諸多報道結果一致[4-5]。排除高血糖以及低血漿白蛋白這兩個引起術后膽漏的患者自身獨立因素[6],我們認為,防止LBEPS術后出現膽漏的主要措施來源于良好的縫合,充分的引流。具體措施如下:(1)為方便腹腔鏡下縫合操作,主操作Trocar的位置可較LC稍偏下,可減少姿勢帶來的疲勞;(2)選用“雪橇”狀縫針,4-0或5-0無損傷可吸收線,方便縫合;(3)針距、邊距保持1.5~2 mm,間斷、連續或者“8”字縫合均可,當管壁菲薄時可多采用“8”字縫合,必要時將周圍游離的肝十二指腸韌帶一期縫合;(4)鏡下打結力度合適,避免膽管壁切割;(5)縫合可用紗條輕壓,輕度膽漏不可反復加針縫合,可留置ENBD作為預防膽漏的措施;(6)妥善放置腹腔引流,確保引流通暢。
另外,一些通過膽道內支架管植入或者ENBD來防止LBEPS術后膽漏的方式也被認可[7-8],但由于:(1)術后需胃鏡取出,增加醫療費用和患者痛苦;(2)引流管移動后回縮膽總管可能;(3)引流管頭端存在長時間抵住腸壁可能等缺點,使用時也頗具爭議。
分析膽囊管微切開入路出現膽漏的原因主要在于膽道鏡的粗暴操作造成切開處向膽總管撕裂。在注意操作輕柔之余,在膽道鏡插入之前預先于切開的頂端縫合一針,可有效防止撕裂膽總管。另外,我們主張自下而上間斷縫合膽囊管匯入部,縫合操作與一期縫合相似,但需注意的是縫合范圍必須超過膽囊管夾閉處,以免膽囊管夾閉處與縫合區域之間出現膽漏。
3.1.2 膽管狹窄:41例獲得隨防患者中均無膽管狹窄的并發癥發生。避免膽管狹窄的發生,同樣需要有良好的縫合技術。縫合時主張邊距合適,可控制在2 mm左右。邊距過小易造成縫合張力降低和膽管壁切割,形成膽漏;而邊距過大可使縫合處膽管壁內翻,術后瘢痕增生造成狹窄。此外預防膽管狹窄也應嚴格篩選患者,掌握合理的適應證。
3.2 手術適應證
腹腔鏡下經膽囊管匯入部微切開取石與一期縫合兩種方式在臨床開展的關鍵還在于適應證的選擇,在術前均需全面評估患者整體情況,MRCP我們認為是必須的檢查,可判斷結石的形狀、大小、數量以及位置。綜合文獻報道[9]以及我科經驗,我們認為腹腔鏡下經膽囊管匯入部微切開膽道探查取石術的適應證為:(1)膽囊結石繼發膽總管結石,術前可合并胰腺炎、黃疽但已控制;(2)膽總管直徑>1.0 cm;(3)膽囊管內徑寬且直,寬度至少應與纖維膽道鏡相當;(4)繼發性膽總管結石直徑應<1 cm,數量應≤3枚,但具體情況可適當放寬;(5)術前影像學檢查未發現膽總管結石,但DBIL、ALT、AKP增高懷疑膽管結石;(6)無法解釋的膽總管擴張。另外需要強調,由于解剖上膽囊管是向下匯入膽總管的,膽囊管匯入部與肝總管的角度是一銳角,這就使該術式探查肝總管及以上膽管存在困難,術前影像學檢查需更完備才能避免殘余結石,必要時術中可經膽囊管造影。
而LBEPS的要求在對膽總管直徑要求>1.0 cm以外,主要排除以下禁忌:①肝內膽管結石;②膽總管腫瘤、炎性狹窄;③重度黃疽并導致肝損;④AOSC;⑤術中出現膽管損傷;⑥低蛋白血癥且一般情況差;⑦膽源性胰腺炎。而高齡患者、膽管壁菲薄(<1 mm)則被認為是相對禁忌。隨著膽道鏡取石技術和縫合技術的發展,一些以往被認為LBEPS手術禁忌的患者也能成功實施該手術。對于膽管直徑>8 mm、膽壁厚的患者,只要膽管結石能取盡并保證膽道通暢者,國內部分專家認為行一期縫合也是可行的[10]。
[1] Ahmed I, Pradhan C, Beckingham IJ, et al. Is a T-tube necessary after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J]. World J Surg,2008, 32(7): 1485-1488.
[2] Wills VL, Gibson K, Karihaloot C, et al. Complications of biliary T-tube after choledochotomy [J]. ANZ J Surg, 2002, 72(3): 177-180.
[3] 韓威, 張忠濤, 李建設, 等. 膽囊管匯入部微切開在腹腔鏡膽道探查術中的應用 [J]. 中國微創外科雜志, 2011, 11(11): 970-972.
[4] 周蒙滔, 孫洪偉, 金約朋, 等. 膽總管一期縫合術在膽道外科的應用 [J]. 肝膽胰外科雜志, 2009, 21(1): 31-33.
[5] Zhu QD, Tao CL, Zhou MT, et al. Primary closure versus T-tube drainage after common bile duct exploration for choledocholithiasis [J]. Langenbecks Arch Surg, 2011, 396(1): 53-62.
[6] 王毅本, 曾小兵, 吳馳, 等. 膽總管探查后一期縫合膽汁漏的臨床分析 [J].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05, 12(4): 351-352,360.
[7] 田明國, 王立云, 楊俊峰, 等. 腹腔鏡膽總管探查定期自行脫落J型膽道支架引流術150例報告 [J]. 肝膽胰外科雜志, 2013,25(2): 96-99.
[8] Wani MA, Chowdri NA, Naqash SH, et al. Closure of the Common Duct -Endonasobiliary Drainage Tubes vs. T Tube: A Comparative Study [J]. Indian J Surg, 2010, 72(5): 367-372.
[9] 尚培中, 周鳳桐, 賈國洪, 等. 膽道鏡經膽囊管行膽道探查147例 [J]. 人民軍醫, 2007, 50(6): 345-346.
[10] 王博, 程浩, 袁志林, 等. 兩種微創方法治療膽囊結石合并膽總管結石的療效比較 [J]. 腹腔鏡外科雜志, 2010, 15(5): 379-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