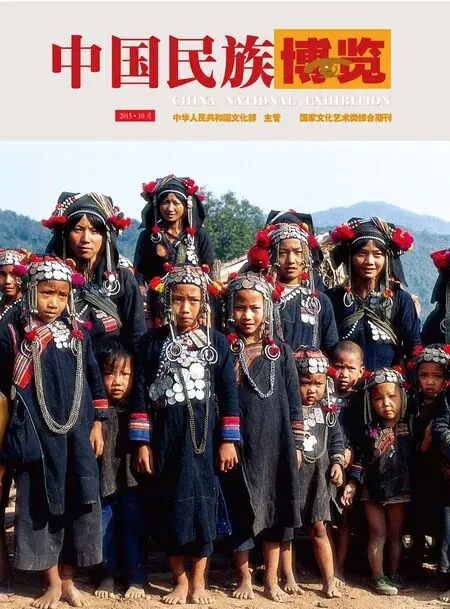匈奴統(tǒng)治西域時(shí)期新疆地區(qū)的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
王 莉
(新疆醫(yī)科大學(xué) 語(yǔ)言文化學(xué)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1)
匈奴統(tǒng)治西域時(shí)期新疆地區(qū)的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
王莉
(新疆醫(yī)科大學(xué) 語(yǔ)言文化學(xué)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11)
匈奴統(tǒng)治西域時(shí)期,在新疆地區(qū),多種語(yǔ)言文化互相影響、互相交流,尤以匈奴文化、漢文化影響為甚。這種狀況不僅僅取決于各民族成員的自然選擇以及當(dāng)時(shí)的地理生態(tài)環(huán)境,同時(shí)匈奴與中原王朝在爭(zhēng)奪西域過(guò)程中兩大政治勢(shì)力在經(jīng)濟(jì)政治上的實(shí)施經(jīng)略對(duì)這種局面的形成也起到強(qiáng)大的推動(dòng)作用。
匈奴;多元文化;互動(dòng);因素
匈奴作為北方草原強(qiáng)勢(shì)軍事實(shí)體,興起于公元前三世紀(jì),在漢通西域之前統(tǒng)一著北方乃至統(tǒng)治西域。匈奴政權(quán)除了對(duì)西域進(jìn)行行政管理外,也不可避免地給地方文化帶來(lái)了一定的影響。再加上這一時(shí)期匈奴與中原王朝在西域的角逐中雙方對(duì)其產(chǎn)生的影響,都使這一時(shí)期在西域文化發(fā)展進(jìn)程中的作用不可抹殺,學(xué)者嚴(yán)文明曾說(shuō)過(guò):“隨著匈奴文化和漢文化影響的加強(qiáng),新疆各地文化之間的交流更為頻繁,作為東西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也日益顯現(xiàn)出來(lái)。”可見(jiàn),匈奴統(tǒng)治西域時(shí)期與這一歷史時(shí)期之前相比,西域多種文化的交流較為頻繁,影響更為強(qiáng)勁。因此考察這一時(shí)期的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關(guān)系,不僅可以還原當(dāng)時(shí)文化面貌,還可以由此看出新疆民族歷史文化前進(jìn)的軌跡,亦可給后人充分展示多元文化發(fā)展的歷史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
一、匈奴統(tǒng)治西域時(shí)期新疆的民族、語(yǔ)言與文化
這一時(shí)期,西域生活的主要民族及部落有塞人、月氏、烏孫、羌人、車(chē)師、匈奴和漢人。這些民族和部落在西漢初年經(jīng)過(guò)不斷的遷徙和發(fā)展,并與當(dāng)?shù)赝林用窕ハ嗳诤希⒘苏?quán),即史書(shū)上所說(shuō)的“城郭諸國(guó)”和“行國(guó)”。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邊綠洲或山間盆地生活的定居或半定居的居民,已形成相對(duì)獨(dú)立的聚落,大多有城郭,史稱(chēng)“城郭諸國(guó)”。而行國(guó)主要指匈奴、烏孫等以游牧為主,隨畜逐水草的政權(quán)。
據(jù)現(xiàn)有資料看,這一時(shí)期的語(yǔ)言文化狀況大致如下:天山南部多數(shù)民族都屬于印歐語(yǔ)系,而且這種語(yǔ)言可以進(jìn)一步分為塞語(yǔ)和龜茲—焉耆語(yǔ)。塞語(yǔ),流行于塔里木盆地南緣,塔里木盆地以北諸國(guó)流行用婆羅米文字書(shū)寫(xiě)的吐火羅語(yǔ),稱(chēng)為龜茲—焉耆語(yǔ)。這種語(yǔ)言又分為龜茲和焉耆兩種方言,一種流行于高昌、焉耆一帶,叫甲種吐火羅語(yǔ),一種流行于龜茲地區(qū),叫乙種吐火羅語(yǔ)。南道鄯善諸國(guó)流行的民間語(yǔ)言是樓蘭語(yǔ),于闐地區(qū)除了塞克語(yǔ)外,還流行佉盧文為代表的“印度俗語(yǔ)”。隨著中原漢族的大量遷入,漢語(yǔ)文也在城郭諸國(guó)中廣泛流行,一些上層貴族使用的比較多,而且程度很高,可見(jiàn)它的通用性多在以漢語(yǔ)為母語(yǔ)的民族和少數(shù)民族上層貴族中使用,在少數(shù)民族普通人家中的使用卻受到條件的限制,因?yàn)闈h語(yǔ)秦時(shí)進(jìn)入西域,但較廣泛的傳播卻從張騫出使西域與兩漢王朝對(duì)西域的統(tǒng)一開(kāi)始。同時(shí),這一時(shí)期塔里木盆地初步形成吐火羅化,吐火羅語(yǔ)成為南部的區(qū)域交際語(yǔ)。屬于漢藏語(yǔ)系的有羌人、漢人,屬于阿爾泰語(yǔ)系的有匈奴人、烏孫人。北部以操阿爾泰語(yǔ)的民族為主,阿爾泰語(yǔ)系語(yǔ)言于是就成為北部民族區(qū)域交際語(yǔ)。羌語(yǔ)由于和漢語(yǔ)同屬漢藏語(yǔ)系,羌族人口較少,常用漢語(yǔ),其語(yǔ)言使用范圍逐漸為漢語(yǔ)所涵蓋,因此多限于民族內(nèi)部使用。至于車(chē)師人的種族、語(yǔ)言目前還是一個(gè)沒(méi)有完全研究清楚的問(wèn)題。
二、匈奴統(tǒng)治西域時(shí)期的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
(一)匈奴的語(yǔ)言文化對(duì)新疆的影響
當(dāng)時(shí),在北方占有統(tǒng)治地位的匈奴,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jì)和文化等方面占有絕對(duì)優(yōu)勢(shì),因此同樣在語(yǔ)言文化方面也給其他民族以種種影響。
首先,匈奴語(yǔ)言對(duì)西域各個(gè)民族有一定影響。西漢人說(shuō)匈奴“箕據(jù)反言”,這極易使人想到阿爾泰語(yǔ)系的賓謂句式。北魏時(shí)代語(yǔ)言屬于突厥語(yǔ)族的敕勒人,“其語(yǔ)略與匈奴同,而時(shí)有小異”。北匈奴的后裔在今北疆一帶建立的悅般國(guó),“其風(fēng)俗言語(yǔ)與高車(chē)同”。這些記載都可以推測(cè)出,匈奴人到南北朝時(shí)期,是講阿爾泰語(yǔ)系突厥語(yǔ)族的某一種語(yǔ)言的,同時(shí)亦可推測(cè)匈奴與西域其他民族語(yǔ)言之間的相互影響。
其次,匈奴的風(fēng)俗文化對(duì)新疆各個(gè)民族亦有影響。如匈奴的生活習(xí)俗是“……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漢文史籍記載說(shuō),烏孫與匈奴同俗。再如,張騫初通烏孫時(shí),烏孫昆莫“見(jiàn)騫如單于禮”,“昆莫起拜,其他如故”。上述可見(jiàn),匈奴的風(fēng)俗禮儀影響了烏孫,同樣也將影響當(dāng)時(shí)新疆的其他民族。
再者,我們從《漢書(shū)·西域傳》中可以看到西域諸國(guó)使用匈奴官號(hào)的情況。據(jù)《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dāng)戶、左右骨都侯……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zhǎng)亦各自置千長(zhǎng)、百長(zhǎng)、什長(zhǎng)、裨小王、相、都尉、當(dāng)戶、且渠之屬”。這些職官稱(chēng)號(hào),西域諸國(guó)也有所見(jiàn)。例如,鄯善國(guó)設(shè)有左右且渠擊車(chē)師君各1人,于闐國(guó)設(shè)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皮山國(guó)設(shè)有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各一人,疏勒國(guó)設(shè)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zhǎng)各一人,龜茲國(guó)設(shè)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以上是見(jiàn)于《漢書(shū)·西域傳》記載的西域諸國(guó)的職官情況。對(duì)這一現(xiàn)象的合理詮釋是匈奴在接受新疆諸民族文化影響的同時(shí),也將本民族的文化傳播給新疆各族。
(二)漢語(yǔ)漢文對(duì)新疆的影響
兩漢王朝在西域與匈奴角逐戰(zhàn)爭(zhēng)的勝利到對(duì)西域的完全統(tǒng)一,經(jīng)歷了較長(zhǎng)的時(shí)間。這一時(shí)期,漢語(yǔ)漢文在西域的廣泛使用離不開(kāi)漢代的屯墾、通使、通婚、貿(mào)易等活動(dòng)。這些活動(dòng)常伴有大量的語(yǔ)言文化交流。漢語(yǔ)漢文對(duì)新疆的影響可以從新疆考古出土的殘簡(jiǎn)、木簡(jiǎn)等看出。羅布泊西漢烽燧遺址出土了《論語(yǔ)·公冶長(zhǎng)篇》殘簡(jiǎn),斯文赫定在“海頭”遺址發(fā)現(xiàn)了東漢末年《戰(zhàn)國(guó)策》殘卷及算書(shū)《九九術(shù)》殘簡(jiǎn)。另外,尼雅出土八枚木簡(jiǎn),是系在禮物上的木排,上書(shū)送某物于某人,兩面書(shū)寫(xiě)。 這些漢文木簡(jiǎn)收錄在《樓蘭尼雅出土文書(shū)》中,從姓名及內(nèi)容來(lái)看,為當(dāng)?shù)赝林褡逅z留。如上面提到的“瑯玕”、“玫瑰”是珠玉的名稱(chēng)。簡(jiǎn)文中所載送禮者“休烏宋耶”和接受禮物的“大王”、“小太子九健特”等人顯然都是少數(shù)民族中貴族的姓名。“大王”、“王”、“王母”是對(duì)地方統(tǒng)治者的尊稱(chēng)。這些人無(wú)論作為送禮者或收禮者,都是能使用和了解漢文的,這生動(dòng)地反映出西域土著民族通曉漢語(yǔ),使用漢文的情況。學(xué)者尚衍斌曾有此說(shuō)法:“他們使用漢文和上述形制的簡(jiǎn)牘互制問(wèn)候,顯然是接受了漢文化的影響。”[1]這些均說(shuō)明這一時(shí)期漢語(yǔ)文在當(dāng)時(shí)西域業(yè)已使用,也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西域土著民族中,一部分人顯然是受了漢文化的影響。
(三)漢匈語(yǔ)言文化的互動(dòng)
1.漢語(yǔ)漢文化對(duì)匈奴的影響
1.1匈奴使用過(guò)漢文字
史書(shū)中留下了一部分關(guān)于通曉漢語(yǔ)的匈奴人及通曉匈奴語(yǔ)的漢人的記載,如漢武帝時(shí)的金日磾和張騫、蘇武、投降匈奴的中行說(shuō)等。《史記》和《漢書(shū)》中還提到匈奴單于屢次給漢朝呂后和皇帝寫(xiě)信的事,這些書(shū)信當(dāng)是出于漢人之手,用漢文寫(xiě)的。由此可見(jiàn),在匈奴的政治生活中,曾廣泛使用了漢文字。從文獻(xiàn)記載看,匈奴與漢朝的往來(lái)文書(shū)十分頻繁。如《史記》、《漢書(shū)》記述了漢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是時(shí)冒頓方強(qiáng),為書(shū)使使遺高后……”,漢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單于)遺漢書(shū)曰……”單于與漢廷往來(lái)的書(shū)信,似乎都是用漢文寫(xiě)的,但也不能排除這些文字是漢人所譯。假如是漢人書(shū)寫(xiě)的,則這些信件更可能是出自投降匈奴的漢儒之手,他們?yōu)閱斡趯?duì)付漢朝出謀劃策,包括書(shū)寫(xiě)信函。漢景帝的宦官中行說(shuō)就曾為單于回復(fù)漢廷書(shū)信出主意,漢遺單于書(shū)牘以尺一寸,中行說(shuō)教單于回復(fù)漢書(shū)牘以尺二寸及印封皆令廣大長(zhǎng)[2],代單于書(shū)寫(xiě)信函當(dāng)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出土文物中,也有證據(jù)表明匈奴曾使用漢語(yǔ),匈奴上自單于下自各級(jí)官員的印章都是用漢語(yǔ)刻制的,目前已發(fā)現(xiàn)和出土的匈奴官印有二十多枚,均為漢文,如青海大通上孫家寨所出“漢匈奴歸義親漢長(zhǎng)”、東勝采集的“漢匈奴栗借溫愚印”、“匈奴呼律居訾”、“漢匈奴呼盧訾尸逐印”、“休屠長(zhǎng)印”、“休屠胡佰長(zhǎng)印”、“匈奴相邦玉璽”、“右賢王印”、“俎居侯印”、“四角胡王印”、“漢匈奴惡適尸逐王印”、“漢匈奴姑涂畢臺(tái)耆印”、“匈奴破虜長(zhǎng)印”、“匈奴歸義親漢君印”等。這些印章大都是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以后之物,為漢朝廷所頒賜。
1.2匈奴受到漢文化各個(gè)方面的影響
如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等,甚至于精神層面。像公元前一世紀(jì)的匈奴古墓中出土有漢式的鐵鐮和鐵鏵。1956年在遼寧西豐縣西俞溝發(fā)現(xiàn)兩漢時(shí)期的匈奴墓葬中有漢字的鐵制工具,還有許多漢式環(huán)首小鐵刀、錐以及漢族的陶器、兵器、馬具、銅鏡、服飾、貨幣等。可見(jiàn)中原經(jīng)濟(jì)和文化有力地影響了匈奴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文化的發(fā)展。在與中原王朝的長(zhǎng)期交往過(guò)程中,匈奴人在禮儀上也受到漢文化的熏陶。如在孝道上,據(jù)《漢書(shū)·匈奴傳》記載:自呼韓邪單于之后,匈奴單于見(jiàn)漢帝死后在謚號(hào)中含有“孝”字,于是也在自己的名號(hào)中加“若鞮”二字。匈奴稱(chēng)“孝”為“若鞮”。
1.3匈奴語(yǔ)的一些詞語(yǔ)
在兩漢時(shí)期被漢語(yǔ)音譯保存了下來(lái),如胡(匈奴的別稱(chēng))、單于(匈奴最高首領(lǐng)的稱(chēng)號(hào))、頭曼(萬(wàn))、冒頓(圣)、撐犁(天)、孤涂(子)、閼氏(單于妻妾的名號(hào))、居次(公主)、屠耆(賢)、谷蠡(官名)、當(dāng)戶(官名)、祁連(祁連)、且渠(官名)、稽粥、甌脫(邊界)、逗落(墳堆)、徑路(寶刀)、服匿(陶制的容器)、比余(櫛)、胥比(瑞獸)(鈞)等。
1.4其他語(yǔ)言對(duì)漢語(yǔ)的影響
吐火羅語(yǔ)對(duì)漢語(yǔ)的影響也甚為顯著,雖然就目前發(fā)現(xiàn)的殘卷內(nèi)容而言可以勘定的詞匯不多,但是這些詞匯大多還在現(xiàn)代漢語(yǔ)中活躍著。如:
漢語(yǔ)“蜜”字來(lái)自吐火羅語(yǔ)A “myat”、吐火羅語(yǔ)B “mit”。
漢語(yǔ)“沙門(mén)”來(lái)自吐火羅語(yǔ)B “samane” 。
漢語(yǔ)“沙彌”來(lái)自吐火羅語(yǔ)B “sanmir” 。
漢語(yǔ)“佛”最早來(lái)自吐火羅語(yǔ)B“pud”。
漢語(yǔ)“獅子”來(lái)自吐火羅語(yǔ)A sacake 。
漢語(yǔ)“翕候”來(lái)自吐火羅語(yǔ)A yapoy,吐火羅語(yǔ)B ype (土地) 。
漢語(yǔ)“沐猴”來(lái)自吐火羅語(yǔ)A mkow,吐火羅語(yǔ)B moko 。
還有漢語(yǔ)中有較多的音譯地名,如吐火羅語(yǔ)地名:龜茲、樓蘭、尉犁、且末;羌語(yǔ)地名有若羌。
通過(guò)上述材料,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匈奴統(tǒng)治西域時(shí)期,該階段文化基本上看不到不同文化系統(tǒng)在新疆的對(duì)峙局面,各有自己使用的廣度,但是漢文化有逐漸加強(qiáng)趨勢(shì),匈奴文化處優(yōu)勢(shì)地位,部分地區(qū)初步出現(xiàn)吐火羅化。
三、匈奴統(tǒng)治西域時(shí)期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因素探討
匈奴統(tǒng)治西域時(shí)期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形成了一種以匈奴文化居于優(yōu)勢(shì)地位,漢文化處于逐漸加強(qiáng)趨勢(shì)的特點(diǎn),這種特點(diǎn)的形成除了各民族成員自然選擇的結(jié)果外,也脫離不了當(dāng)時(shí)的地理生態(tài)環(huán)境、匈奴與中原王朝在爭(zhēng)奪西域中經(jīng)濟(jì)、政治、軍事、文化上的勢(shì)力角逐以及其他民族遷徙、人口流動(dòng)等各種因素。
(一)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是產(chǎn)生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的前提
語(yǔ)言文化是屬于民族的,語(yǔ)言文化的接觸是由民族接觸交往引起的。民族個(gè)體(即文化個(gè)體)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各族人民之間的交往(離不開(kāi)經(jīng)濟(jì)物資的交流)必然引起語(yǔ)言文化的互動(dòng)。根據(jù)史載,古西域的塞人、月氏、匈奴等諸多民族是游牧民族,他們逐水草而居,不時(shí)遷徙,必然帶來(lái)民族的接觸。林斡曾提到過(guò)“匈奴族十分重視與漢族互通關(guān)市。除漢族外,匈奴與羌族經(jīng)常發(fā)生商業(yè)交換;與烏桓族以及西域各族也發(fā)生過(guò)交換。”再如,從新疆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斷定,漢代以前就有不少漢人來(lái)到新疆。自秦漢以來(lái),越來(lái)越多的漢人不斷流入新疆。隨著各個(gè)民族交往的廣度以及深度的增加,民族間文化的互動(dòng)也變得愈加活躍。
(二)古西域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是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的自然生態(tài)基礎(chǔ)
古代西域地處古絲綢之路咽喉之地,這里是溝通中原文化及東西方文化的津梁。往來(lái)這里的有使臣、商旅、宗教人士等,不僅有中原派往西方者,更有來(lái)自歐洲等地的各色人士,他們或從事政治活動(dòng),或進(jìn)行朝貢貿(mào)易,或致力于宗教、文化活動(dòng)。這樣的地理環(huán)境為民族的融合、語(yǔ)言文化的互動(dòng)創(chuàng)造了優(yōu)越的自然生態(tài),成為匈奴統(tǒng)治西域時(shí)期新疆地區(qū)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的自然基礎(chǔ)。
(三)當(dāng)時(shí)西域的歷史狀況是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的人文生態(tài)基礎(chǔ)
古西域位于中亞,是中西文化交匯地,但對(duì)于中國(guó)古代北方民族來(lái)說(shuō),不僅是戰(zhàn)略要地,更是游牧民族重要的經(jīng)濟(jì)補(bǔ)充地。誰(shuí)占領(lǐng)了西域就等于控制了中西交通要道,從中可以獲得豐厚的經(jīng)濟(jì)利益。而對(duì)于中原王朝來(lái)說(shuō),這一時(shí)期,匈奴控制西域,已經(jīng)成為能與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大勢(shì)力,并對(duì)中原王朝構(gòu)成了威脅。正因如此,這一時(shí)期出現(xiàn)了漢朝與匈奴頻繁爭(zhēng)奪西域的戰(zhàn)爭(zhēng)。這兩大勢(shì)力的對(duì)抗必然帶來(lái)民族間的連年征戰(zhàn),但這些客觀上推動(dòng)了各民族間語(yǔ)言文化的互動(dòng),同時(shí)這些政治勢(shì)力所實(shí)行的經(jīng)濟(jì)政治上的經(jīng)略也成為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的重要推動(dòng)力。如和親、派遣質(zhì)子、互市政策以及安置降人、設(shè)置“譯長(zhǎng)”等方式。
聯(lián)姻政策的實(shí)施有利于雙方保持友好關(guān)系,有利于雙方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除了漢朝善于使用和親政策外,匈奴也曾與西域的一些國(guó)家結(jié)下過(guò)秦晉之好。史料記載,漢元封中,漢朝以江都王建之女細(xì)君為公主,令嫁給烏孫。而匈奴從漢元封中到昭帝時(shí)期,對(duì)烏孫也一直采取著和親政策。伴隨著和親,實(shí)施和親者隨之帶去大量的財(cái)物以及人員,這些都會(huì)對(duì)語(yǔ)言文化的活動(dòng)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再者,為和親而開(kāi)展的一些活動(dòng),如派使團(tuán)求親、交納聘禮、約定婚期、公主出嫁后的答謝,等等,都為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加深了兩族在語(yǔ)言文化方面的相互影響。
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也經(jīng)常會(huì)有遣質(zhì)子行為,像漢武帝時(shí)攻打樓蘭,劫持了樓蘭王。樓蘭王降漢,匈奴知道后也發(fā)兵攻打樓蘭。樓蘭為了不得罪匈漢兩大勢(shì)力,于是向兩國(guó)各派遣一個(gè)質(zhì)子。這些質(zhì)子對(duì)傳播文化起到不小的作用,由于他們廣泛接觸文化,不少人回國(guó)后,成為民族文化的傳播者。
開(kāi)放關(guān)市,是中原王朝的一種策略,這種策略對(duì)于加強(qiáng)民族間的聯(lián)系以及促進(jìn)經(jīng)濟(jì)文化的交流具有積極意義。通過(guò)互市,各個(gè)民族不僅換得了較多的生產(chǎn)、生活用品,同時(shí)也獲得了接觸不同文化的機(jī)會(huì)。
除此之外,西漢安置匈奴降人的方式,使得軍中的匈奴人在語(yǔ)言、服飾和生活習(xí)慣等方面受到漢文化影響。西域諸國(guó)普遍設(shè)置“譯長(zhǎng)”方式,這種方式架設(shè)了民族交往跨越語(yǔ)言障礙的橋梁。 譯長(zhǎng)是主持傳譯和奉使的官職。據(jù)《漢書(shū)·西域傳》記載,西域三十六國(guó)都設(shè)有譯長(zhǎng)。大國(guó)設(shè)譯長(zhǎng)三人或四人,如莎車(chē)國(guó)、龜茲國(guó)、焉耆國(guó),中等國(guó)家設(shè)譯長(zhǎng)二人,如疏勒國(guó)、姑墨國(guó)、溫宿國(guó)等,最小的國(guó)家如單桓國(guó),只有“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也設(shè)有譯長(zhǎng)一人,由此可以看出當(dāng)時(shí)西域民族之間處于不斷接觸中。
四、結(jié)語(yǔ)
通過(guò)對(duì)匈奴統(tǒng)治西域時(shí)期語(yǔ)言文化互動(dòng)現(xiàn)象的梳理以及影響因素的探討,我們對(duì)其有些許思考。首先,匈奴統(tǒng)治西域的這一歷史時(shí)期,新疆多民族語(yǔ)言文化仍處于和諧發(fā)展階段,漢文化影響力開(kāi)始顯現(xiàn),但到張騫鑿?fù)ㄎ饔蚝蟛耪宫F(xiàn)出漢文化的輻射力。因?yàn)檫@一時(shí)期中原與匈奴勢(shì)力角逐中趨于均勢(shì),無(wú)法打破兩極格局,從而使得此時(shí)文化仍處于多元文
化并存階段。其次,這一時(shí)期,匈奴文化隨著匈奴軍事強(qiáng)勢(shì)推進(jìn)也自東向西滲透,因此,在分析這一時(shí)期西域文化發(fā)展進(jìn)程時(shí),可以尋到此時(shí)“匈奴文化”影響先于“漢文化影響”的蹤跡。再者,通過(guò)這一時(shí)期歷史還原,我們發(fā)現(xiàn)新疆各族人民與中原人民之間早已存在著經(jīng)濟(jì)物資互相依賴、風(fēng)俗文化互相交流的手足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無(wú)法割舍,它數(shù)千年來(lái)強(qiáng)有力地維系著中華民族多元統(tǒng)一的完整體系。這亦更能說(shuō)明新疆與內(nèi)地有著悠久、深厚的歷史淵源。我們對(duì)這種關(guān)系的清楚認(rèn)識(shí),將有益于今天新疆的長(zhǎng)治久安和社會(huì)的穩(wěn)定發(fā)展。
[1]牛汝極.西域語(yǔ)言接觸概說(shuō).中央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J].2000,4.
[2]張鐵山.從回鶻文<俱舍論頌疏>殘葉看漢語(yǔ)對(duì)回鶻語(yǔ)的影響.西北民族研究[J].1996,2.
[3]孫守道.“匈奴·西岔溝”古墓群的發(fā)現(xiàn)[A].匈奴史論文選集[C].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3.
HO
A
王莉(1976-),蒙古族,河南南陽(yáng)人,文學(xué)博士,新疆醫(yī)科大學(xué)語(yǔ)言文化學(xué)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漢語(yǔ)與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文化等。
本文系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項(xiàng)目“新疆維吾爾族聚居區(qū)的語(yǔ)言生活及其發(fā)展變化趨勢(shì)研究”(14BYY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