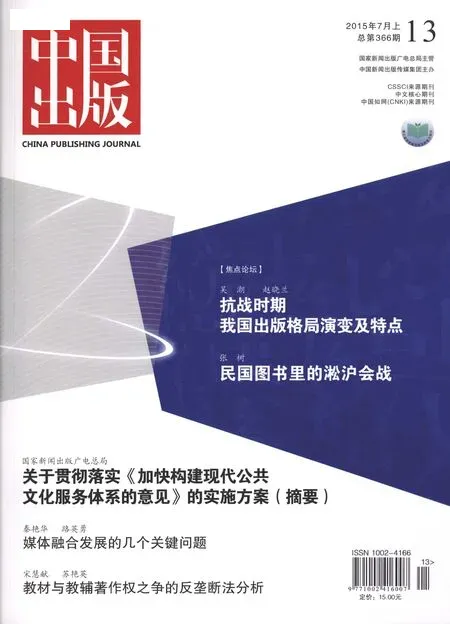抗戰時期我國出版格局演變及特點
□文│吳 潮 趙曉蘭
抗戰時期我國出版格局演變及特點
□文│吳潮趙曉蘭
抗日戰爭時期,我國自近代以來形成的出版格局發生了全國性中心西移和區域性中心不斷涌現等重大演變,并在此過程中表現了動態游移、擴展輻射、格局多元等重要特點。這一演變的發生是我國出版界應對抗戰現實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深刻影響和改變了當時以及之后的中國出版格局。
抗戰時期出版格局演變過程演變特點
我國現代概念意義上出版社的出現和編、校、印、發出版體制的建立,發端于19世紀上半葉,歷經近百年的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時,大致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南京、北平(今北京)、天津、廣州等幾大城市為次中心的出版格局。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隨著戰場形勢的變化和戰區的推移,原來作為出版中心與次中心的城市先后淪陷,我國出版格局亦隨之發生了全國性中心西移和區域性中心陸續出現等重大演變歷程。這一演變的發生是我國出版界應對抗戰現實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深刻影響和改變了當時以及之后的中國出版格局,在我國出版史上留下了風雷激蕩的歷史篇章。
一、抗戰時期我國全國性和區域性出版中心遷移演變的基本描繪
抗戰初期,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州先后成為淪陷區,原有的出版格局被徹底改變。由于八年抗戰期間戰場形勢變化多端,戰區范圍不斷擴展,出版機構為躲避戰火重整旗鼓,不得不在中國的大地上頻繁地輾轉遷移,這一游移性的遷移過程幾乎貫穿抗戰始終。從宏觀層面上考察,我國的出版格局在抗戰期間形成了全國性中心的西遷與區域性中心次第出現的動態性演變過程。
1.全國性出版中心的遷移與演變
(1)曇花一現的全國出版中心——武漢(1937年7月-1938年10月)
抗戰初期上海出版中心解體之后,新中心的建立并未形成共識,各出版機構向外遷徙各行其是。在這一過程中,國家政治和經濟中心的搬遷去處與交通樞紐所在之地,成為出版機構遷移時的基本考量因素。因此,上海淪陷后,廣州、長沙、武漢等地都曾被列為重要的轉移去所。
從抗戰初期政治中心的走勢來看,南京陷落之后,重慶成為戰時首都,國民政府一部分機構西遷入渝,但軍事統帥部和相當數量的政府機關卻駐留在武漢,這樣武漢實際上成為抗戰初期全國軍事、政治的中心;加之號稱“九省通衢”的武漢享有的重要交通樞紐之便利,于是武漢自然成為抗戰初期中國出版的中心城市。
依托長江航運的便利交通,上海和南京的各大出版社陸續遷移至武漢,使武漢以出版書刊為主的出版社由抗戰初期的15家迅猛增至63家,當時我國最著名的民營報紙《申報》和《大公報》先后在武漢開設分版,其余民營的和政府機構的報刊也或在武漢創刊、或搬遷至武漢出版。“這樣一來,武漢的報紙不僅數量很多,而且匯集了一批著名的大報,成為抗戰初期的輿論中心。”[1]
同時,由于抗戰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10月和12月,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先后在此成立;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發行,這是中共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第一份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報刊。這些狀況的出現相較于抗戰之前國統區的出版格局而言是一種豐富和改變。
1938年5月之后,隨著戰火向華中地區逼近,許多出版機構又開始陸續離開武漢內遷。1938年10月下旬,武漢陷落。武漢作為抗戰初期我國出版中心的歷史使命也隨之結束。
武漢出版中心存在前后約一年時間,雖然時間短暫,但對于穩定甫遭戰火驚魂未定的中國出版業界,盤整抗戰初期的中國出版格局,動員民眾宣傳抗戰,以及促進華中地區出版事業的發展,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相對恒定的全國出版中心——重慶(1937年 -1945年)
1937年11月,重慶被定為中國的戰時首都,以陪都身份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的政治中心,這也為重慶出版業的發展帶來了歷史契機。
由于抗戰之前重慶的出版業在全國影響微弱,因此,雖然有全國性政治中心的背景,但重慶作為全國性出版中心地位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
上海、南京淪陷后,已有部分出版機構西遷入渝,但當時因為武漢成為上海淪陷后事實上的全國出版中心,重慶的這一地位未能顯現。武漢失守后更多的新聞出版機構陸續遷入,重慶的出版事業醞釀著質的飛躍。但在抗戰前期,動蕩的戰爭形勢和艱難的西遷過程,使中國的出版格局尚顯混沌。同時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當時上海租界“孤島”和殖民地香港的出版業,依然保持著旺盛的活力,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滬港兩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承擔著為內地大后方出版業界印刷造貨的工作,這在無形之中也遮蔽了重慶作為全國出版中心的地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上海“孤島”和香港淪入敵手,兩地的出版工作者陸續來到重慶,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中國出版業巨無霸也搬遷到重慶,重慶集中了全國最多數量和最高質量的出版機構。1942年,重慶圖書出版數量一躍為1941年的兩倍多。到1943年,重慶一地擁有的印刷廠數量為全國的31.7%,書店數量為全國的23.7%,圖書出版數量為全國的37.3%,[2]“隨著重慶圖書業在戰時的迅速壯大,逐漸形成以重慶為依托溝通全國各地的發行網絡”。[3]直到此時,重慶才真正成為抗戰時期的全國出版中心。據不完全統計,重慶在抗戰八年中,“出版書刊的單位共有644家,出書8000余種,出期刊近2000種。”[4]
中共領導和影響下的新聞出版機構繼續構成了這一格局演變的重要內容。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新華日報》搬遷至重慶復刊;同時,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新知書店、新華日報圖書課、中國出版社等中共領導下的出版機構亦云集山城,使武漢時期形成的多元化出版格局得以延續并光大。
1945年抗戰勝利之后,陪都重慶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各出版機構陸續遷回原地,重慶作為全國性出版中心的地位亦隨之結束。
(3)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出版重鎮——桂林(1938年 -1944年10月)
桂林地處邊遠,抗戰之前出版事業并不十分發達。但是由于特殊的機緣,桂林在抗戰期間成為中國出版的重鎮,“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據不完全統計,桂林先后有各類書店和出版社共200余家……據1943年7月的統計,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廠109家……抗戰期間桂林出版了200多種雜志……發行的網線,也遍及全國。”[5]
考察桂林成為中國出版重鎮的原因,大致為:第一,在抗戰的初期階段,桂林因為遠離戰區,被一些重要的文教單位與新聞出版機構選為避難之所;第二,廣西是桂系的地盤,“桂系為了發展自己的力量,在政治上采取了較為開明的政策,為出版業的發展提供了寬松環境。”[6]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大批文化人抗戰期間集結于桂林,“桂林是全國兩大文化城之一,它擁有廣大的出版機構,它集中了全國文化人的三分之一。”[7]
由于桂林抗戰期間在我國出版格局中重要的地位和獨特的作用,有人認為:“在抗戰期間,桂林是大后方的一個文化城。若從某種意義來說,桂林在抗戰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過重慶。”[8]不過,盡管一些出版史的資料和著述中把桂林視為抗戰時期全國性的出版中心,但從出版物的數量,以及所產生的全國性影響等方面來看,桂林與重慶相比,兩者的地位還是有高下之分的。有的學者將這一格局稱為“以重慶為中心、以桂林為重點”[9],筆者認為對于桂林而言應該是比較合適準確的出版地位描述。
1944年11月,桂林陷落,桂林作為抗戰時期中國出版重鎮的地位亦隨之消失。
2.區域性出版中心的形成
除了上述武漢、重慶、桂林等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出版中心和出版重鎮之外,還有一些城市和城鎮,抗戰期間出版業也有了長足的發展。由于它們是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發揮著重要作用,并未形成全國性的影響,所以本文將這些城市或城鎮稱為區域性出版中心。
這些區域性出版中心的分布十分廣泛,其影響幾乎覆蓋了當時中國未被日軍侵占的所有地區,其形成原因與演變發展亦比較復雜,大致可以分為下述幾類。
第一,有些城市原本就是省會所在地或是該地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這些城市的出版行業具有較好的基礎或一定的規模。抗戰期間因為上海出版中心的消失和新的全國性出版中心的游移,加之戰爭對于交通的阻隔,使得這些城市在一定的時間段或整個抗戰期間成為當地的出版中心。屬于這種類型的有:西北地區的西安、蘭州、迪化(今烏魯木齊);中南地區的長沙;華南地區的廣州;西南地區的昆明、貴陽等城市。
第二,有些城市本是中小城市或是縣城,出版事業不甚發達。由于省會城市陷落后省府機構、文教單位遷入該地,促成了該地文化事業的發展,進而成為統領全省甚至影響數省的文化和出版中心。屬于這種類型的有:浙江的金華—麗水,湖北的恩施,福建的永安,江西的泰和,湖南的衡陽—耒陽,廣東的韶關等。
第三,有些鄉野集鎮,抗戰期間因為學校等文教單位大量遷入,使原來幾乎為零的出版業異軍突起。例如湖南邵陽地區安化縣的藍田鎮(今漣源縣城),本來只是一個鄉間的小鎮,抗戰期間來自湖南各地大量的文教單位遷移至此,“國立師范學院設在這里,長沙許多著名的公私立中學搬遷在這里。為適應大中學師生對圖書的需要,出版發行業應運而發展起來。”[10]藍田鎮連同周邊緊鄰的城鎮,在很短的時間內出現了35家書局書店。
除了以上三種類型之外,抗戰期間還有兩種類型的區域性出版體系或中心與上述情況有所不同。
其一,以延安為核心的邊區——抗日根據地出版體系。抗戰時期延安物質資源相當匱乏,如果以出版機構的設施條件和出版物的數量質量等比較,延安并無突出之處。但是延安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立了完善的出版領導機構,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出版政策,建立了報刊社、書局書店、通訊社等較為完備的新聞出版機構,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出版發行了大量的圖書報刊。更為重要的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每個根據地都要建立印刷廠,出版報刊,組織發行和輸送的機關”[11],從而形成了以延安為核心,領導并聯網山東、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華中、華南各根據地的出版發行工作,影響力覆蓋敵后廣大區域的獨立出版發行體系。
其二,上海的“孤島”出版中心。上海被日軍侵占后,由于國際關系的緣由,從1937年到1941年4年期間,上海的租界區域仍然由西方國家治理,即所謂的政治飛地——“孤島”。抗日力量借助上海原有的雄厚出版實力,將“孤島”發展成為一塊出版飛地,宣傳抗日的書刊得以繼續在“孤島”出版。
“孤島”出版中心對于抗戰時期中國出版的貢獻還在于——上海原有的出版機構總部雖然內遷,但是印刷設備保留在“孤島”,大量抗日書刊在內地編纂之后,通過“孤島”的印刷設備制作為成品,再運往大后方和敵后根據地,這即是抗戰時期著名的“印刷造貨”。用這些特殊的方式,“孤島”依然使自己在抗戰時期占有了重要的出版地位。
二、抗戰時期我國出版中心遷移和出版格局演變的特點
八年抗戰的烽火遍及中華大地,同時也極大地沖擊和改造了中國的傳統出版格局。在這一改造與演變過程中顯現出了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1. 動態游移頻繁變遷
抗戰之前,以上海為中心輔以若干城市為次中心的我國出版格局,自近代形成后歷經發展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而八年的抗戰卻使這一格局經歷了快速的動態演變。
就全國性的出版中心而言,經歷了從上海武漢重慶的幾次轉換。武漢中心的時間只有約一年時光,重慶中心地位的完全確立大致在1942年之后,但這一地位也僅僅保持到1945年,隨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和各大出版機構陸續遷回原地而宣告結束。另一個具有全國性出版重鎮地位的城市桂林,在歷經了數年快速發展之后,在1944年也因為淪陷而失去了這一地位。
區域性出版中心由于靠近戰區受戰事影響更大,動態游移也就更為頻繁隨性,存在的時間和發展規模亦取決于戰爭形勢的變化,一旦戰事迫近或城市淪入敵手,其區域性中心地位迅即消失,為其他城市取而代之。于是,搬遷移入形成建立快速發展遷移消失,區域性出版中心這一游移過程,抗戰期間在許多地區不斷地重復出現。以浙江為例,1937年12月杭州淪陷后,浙江省政府遷移至金華地區永康縣的方巖,浙江省的文化和出版機構則大部遷移到金華城區,形成了金華中心;1942年5月,金華淪陷,浙江省政府繼續南遷,在浙江南部麗水地區山林深處的各縣之間不斷搬遷,政治中心的轉移帶來了文化中心的同步轉移,原先在金華的出版機構也隨之南遷至麗水地區,形成新的區域性出版中心。
這種頻繁的動態游移,造成了疏散搬遷過程中的人員流失、物資損耗、成本劇增,對于出版業的正常發展是不利的。例如桂林在淪陷之前的轉移疏散過程中,只能帶走紙型,笨重的書籍無法運走,幾乎都毀于戰火,安全到達重慶的估計不到百分之一二,可謂損失殆盡。[12]
2. 擴展輻射遍地結果
雖然動態游移對于出版業的正常發展不利,但這種出版中心在城市、城鎮間的快速轉換為當時和之后的中國出版格局帶來了另一種變化——它將出版業的觸角擴展探伸到我國的廣大地區,帶動和扶持了出版落后地區出版事業的快速發展和繁榮。
抗戰之前中國的出版格局可謂是上海一家獨大,其余數城輔之。上海作為最早的開埠城市之一和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僅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三大出版機構,就占了1936年全國出版物總冊數的71%。[13]再輔之以南京、北平、天津、廣州等幾個次中心城市,例如,“抗戰前夕我國全國共有一千二百余種雜志,比較重要的也有五六百種。其中十分之五是在上海出版,而有十分之二是在南京出版,十分之一是在北平出版”。[14]這一格局偏于沿海和傳統政治文化中心,寥寥數城幾乎構成了中國出版格局的全部,然而這并不是一個十分合理的布局。
全國性出版中心的內遷雖然是戰時的應急無奈之舉,但卻極大地改變了中西部地區落后的出版面貌。重慶作為出版中心同時也是文化中心,名流薈萃,文人云集,外國通訊社的駐華機構也匯集于此,城市的文化品位得到極大提升,成為出版事業大發展的軟件基礎。上海老牌出版機構的遷入則構成了硬件保障,高水平的印刷技術和設施迅速提升了重慶的出版水平,“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這些老字號大型現代出版社遷渝,在編輯工作社會化、印刷技術現代化、發行方式商品化三方面做出表率,對于重慶出版事業的發展無疑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并且成為重慶出版中心地位確立的標志。”[15]
如果說全國性出版中心遷渝為重慶帶來了出版事業質的飛躍,那么,區域性中心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于中國廣大地區出版事業的擴展這一方面。區域性出版中心的形成是一個由省城等大中城市向中小城市和鄉野集鎮漫溢輻射的過程,這一過程受戰局演變的影響相當大。由于戰事往往圍繞著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爭奪展開,省府機構和文教單位只能盡可能地向中小城市或縣城遷移,遷移的去向帶有隨意性和偶然性,事先并無周密計劃。隨著戰火的蔓延,有時這種遷移在某些省區一再發生,鄉野集鎮亦成為疏散之地。正是在這種頻繁的遷移過程中,出版業的疆域逐漸拓展,原本在中國出版格局中無足輕重的地區乃至出版事業的荒漠地帶,成為我國出版格局中的區域性中心,就連“荒鄉僻地都可發現各種各色的報紙”。[16]上文所闡述的區域性出版中心的第二和第三種類型,即是這種現象的典型體現。以湖南為例,在長沙淪陷之后,伴隨著省府機構和其他文教機構的疏散轉移,漸次形成了衡陽—耒陽、邵陽—藍田、常德—沅陵等三個區域性出版中心,藍田書報社出版的教學用書和學生課外讀物,抗戰時期在湘中、湘西南一帶頗為暢銷。[17]
因此,抗戰期間全國性出版中心的內遷和區域性出版中心的擴展探伸,填補了原先中國出版格局中的空白地區。中國出版界以其非常時期的薪火相傳,在廣大的城鄉地區燃起了出版事業生生不息的火炬。
3. 中心互補格局多元
抗戰時期的中國出版格局并不規整,一些地區由于敵我犬牙交錯,戰區之間形成隔絕,作為全國出版中心和重鎮的重慶與桂林偏于一隅,發行能力根本無法覆蓋全國,其全國性的影響力實際上是有限的。全國性出版中心控制力和影響力的不足使兩種情況成為可能。
首先,凸顯了區域性出版中心的地位。區域性中心本身出版能力有限,出版物的輻射力和影響力也較多地局限在一定區域之內,但這恰好填補了因路途不暢、物流受限、全國性中心力所不逮而出現的空白,造成了區域性中心從時間和空間上成為某一地區、某省乃至數省的核心出版力量。以浙江的金華—麗水中心為例,金華在抗戰期間被定為全國五大文化驛站之一(另外四個是重慶、桂林、西安、蘭州),金華—麗水出版中心其輻射影響力覆蓋了安徽、江西、福建的部分區域,使之不僅成為浙江本省出版事業的中心,還成為東南地區的書刊集散中心。這種全國性出版中心與區域性出版中心的互補大大抬升了區域性中心的地位,區域性中心的作用比起戰前的出版次中心顯得更為重要。
其次,我國出版格局的控制力量呈現多元化的狀況,各派政治力量風云際會,各展其能。從武漢到重慶,全國性出版中心的控制力量是國民政府;桂系則控制了出版重鎮桂林和由桂系人士主政的浙江金華—麗水出版中心;迪化區域中心則由當地的政治力量所控制。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出版力量構成了多元化出版格局中的非常重要的板塊。其中,主體力量是以延安為核心的邊區——抗日根據地出版體系,同時在國民政府控制的重慶出版中心和地方勢力控制的其他地區,也拓展了很好的發展空間。例如,“桂林文化城與武漢、重慶等新聞出版中心相比,有著一個顯著的特點,即中共的宣傳力量超過了當時駐重慶的國民黨中央的力量。”[18]抗戰期間出版格局的多元化對于團結各派政治力量,維護和鞏固統一戰線,高效有力地宣傳抗戰,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三、結語
抗戰期間我國出版格局的重大演變,見證了我國出版業界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以自己獨特的方式高揚抗戰大旗、鼓舞民心士氣、凝結文士菁華、延續文化脈絡的奮斗過程。在抗戰勝利70周年的今日,這種精神依然值得出版業界后人追思和效法。
(作者單位:浙江傳媒學院國際文化傳播學院浙江傳媒學院學報編輯部)
[1]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三卷)[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80
[2]蘇朝綱.抗戰時期陪都重慶出版業的發展變化及其特點[J].出版史料,2004(2):71
[3]郝明工.試論抗戰時期的重慶出版事業[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1995(4):62
[4]唐慎翔.抗戰期間重慶的出版發行機構及圖書業//鐘樹梁.抗戰時期西南的文化事業[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448
[5]魏華齡.抗戰時期桂林的出版事業//龍謙,胡慶嘉.抗戰時期桂林出版史料(桂林文史資料第三十八輯)[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3
[6]王余光.中國出版通史·民國卷[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132
[7]司馬文森.擴大宣傳周之后建議成立西南文抗[N].大公報(桂林),1944-06-21.轉引自魏華齡.抗戰時期桂林的出版事業//龍謙,胡慶嘉.抗戰時期桂林出版史料(桂林文史資料第三十八輯)[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1
[8]千家駒.在桂林的八年[J].學術論壇,1981(1):37
[9]熊復.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后方出版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3
[10]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聞出版志[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67
[11]何揚鳴.抗戰時期浙江中共新聞活動的再研究[J].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1(5):34
[12]趙家璧.憶桂林——戰時的“出版城”[N].大公報,1947-05-18.轉引自吳永貴.民國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62
[13]王云五.十年來的中國出版事業//宋原放.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1卷上)[C].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426
[14]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三卷)[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99
[15]郝明工.試論抗戰時期的重慶出版事業[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1995(4):63
[16]蔡罕.《戰時記者》初探[J].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5(2):3
[17]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聞出版志[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68
[18]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三卷) [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