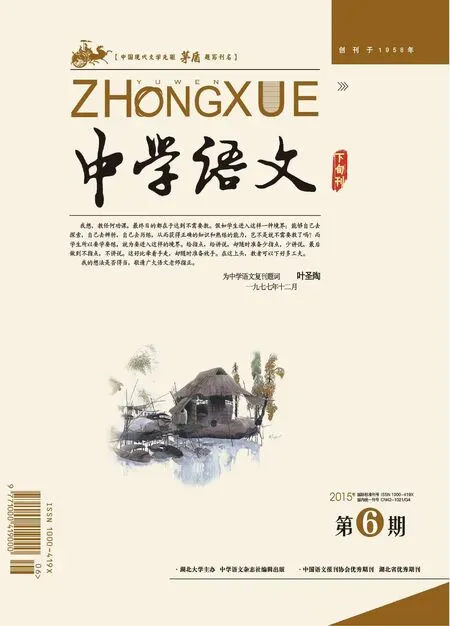愛你在心口難開——談談高中語文選修課
劉 俊
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過,如果想讓教師的勞動給教師帶來一些快樂,那么我們應當從事一些思考和研究。高二上學期我們就已經進入《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的學習階段,就以這本選修課本為觸發點,談談個人的粗淺之見。其中《六國論》《項脊軒志》《阿房宮賦》等以前在必修的課本中都出現過,當前不同版本的教材,有的在選修課本,有的保留在必修課本,人教版教材中統一納入到選修課范圍內并且分屬三個不同的單元。這樣的折騰究竟何用?我們的選修課到底怎么了?是誰動了我們的選修課?
一、誰為選修定“終身”
誰為選修定終身?既然要體現學生的本位,為什么學生只是完全被動的接受,被選擇呢?
人教版選修模塊共有五大類:“詩歌與散文”“小說與戲劇”“新聞與傳記”“語言文字運用”“文化論著研讀”。雖然這五個模塊共有十六本教材,但我們教師都沒有選擇,各地市甚至全省統一選修,這和必修有什么區別呢?一些學校也相應開設了校本課程的選修課,也幾乎都是教師根據自己的喜好或專長確定主題方向后讓學生選擇。這樣,基本上剝奪了學生的自主選擇權。我們完全可以讓學生去選題,教師引導和把關,從學生的選題中確定具有典型性,積極性,對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有益的主題作為我們的選修課程,這才是學生真正感興趣的又能從中獲益的內容,對教師也具有挑戰性。我想可能就會出現“漫畫與人生”“玄幻與現實”“網絡與科技”等一系列新鮮又不失價值的選修課題。只有把選修的權力真正賦予學生,選的才有意義,學的才有價值。正如一位專家所言:學習因選擇而快樂,人生因自主而精彩!
二、必修、選修剪不斷
我們的必修與選修到底該如何區分呢?愚以為,語文學科的工具性應是我們必修內容的學習方向,而人文性是我們選修內容的學習方向。現行人教版選修模塊中“新聞與傳記”“語言文字運用”等模塊很直觀的能體現語文學科的工具性,達到學以致用的目標。現行人教版必修課本中的課文更側重于人文性,其中以詩歌、小說、散文為主。有些單元、課文文藝理論性強,對學生的要求很高,比如《說“木葉”》《談中國詩》等,學生沒有較深厚的文學素養和品鑒能力是無法領悟其中的奧妙的,這類文章應是根據學生的喜好和專長進行粗淺的解讀和品鑒,故而應納入選修課程更好。這類文章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受到的待遇也基本上是一致的——被無視。
三、踏過選修了無痕
選修課程的評價標準對各模塊都有明晰的規定和說明,例如“詩歌與散文”模塊的評價要求中就有這樣兩條:(1)學生的閱讀積累是評價的基礎,要注意考察他們的閱讀興趣和文化視野。(2)以學生的審美能力、藝術趣味和欣賞個性作為評價的重點,如能否拓展想象和聯想,能否通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產生感情的共鳴,能否發現作品的豐富內蘊和深層意義,是否有獨到的感受和對作品的創造性理解等。怎樣的評價機制可以完成對學生的評價?盡管《考試說明》有明確規定不少于百分之十,但事實上有些省份高考試卷中哪些題型是選修內容是比較模糊的,因為這些題目既可以姓“必”(必修)也可以姓“選”(選修)。所以,現實是許多學校并沒有認真完成選修課程的教與學,而這樣的結局也是“預料之中”的。
四、愛你在心口難開
一位課改專家曾說,高中新課改,亮點在選課,難點在選課,突破點也在選課。那些走在新課改前列的地區、學校做了不少有益的嘗試和探索,也有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做法。譬如,在高一階段就開始選修課程的學習,每周固定一課時,實行走班制,學生可任選;另外開設拓展性選修課定位于培養語文特長生。這些都是有益的嘗試和借鑒,這些地方和學校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們的選修課究竟怎么開,恐怕一時也難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我想,我們還是要充分結合本地區、本學校、學生和教師的現實情況,從學生的需要和成長出發,適當給自己和學生松松綁,讓學生從選修中找到受益匪淺的養分,這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在中學階段開設選修課的初衷無疑是好的,教育主管部門制定的相關開設要求、細則、評價等不能說不具體細致,但落實過程中卻徒有其表,原因何在?我們不得不再次審視我們的選修課和必修課、考試與升學的關系。但愿不久的將來,我們的選修課能如春天百花爭艷般綻放在大江南北,我們的選修課堂真正的有學生的精彩和智慧!